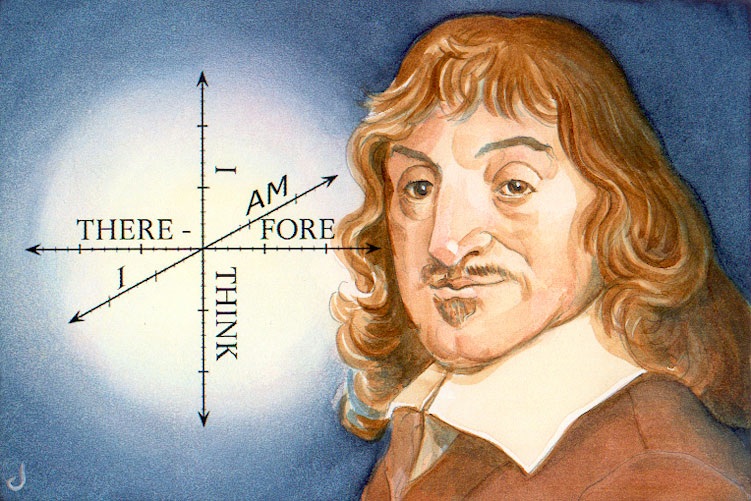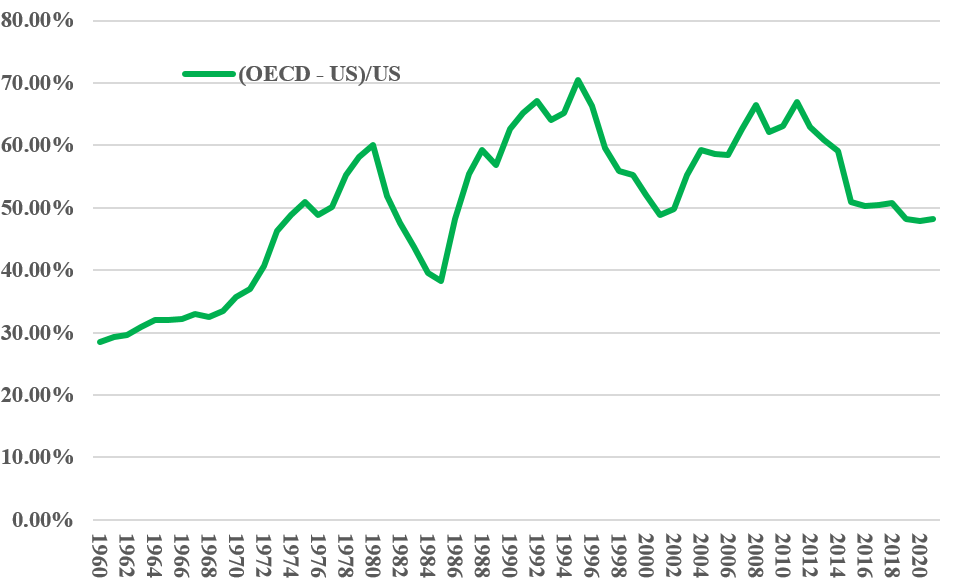過往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知識份子不斷反躬自省的精神傳統。上窮碧落下黃泉,孜孜不倦求探索,為何中華文明在近代落伍的原因。冷戰結束以來,世界上原先存在著兩種對立思潮之間的平衡狀態隨之被徹底打破。西方新保守主義和新古典自由主義被所謂的勝利沖昏了頭,他們的思潮有如現代版的基督教約翰福音,高喊「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在全世界橫行無阻,再無任何保留與顧忌。他們的知識份子和學界益發不能像我們中國人這樣反躬自省,真理的論證過程陷入自說自話的自我迴圈過程,思想日益僵化絕對化,容不得任何不同意見。古希臘人發明的辯論術其規則強調正反雙方意見得到充分表達的基本精神蕩然無存。思想家們一直引以為傲的獨門絕活Critical Thinking(批判思維)而今安在?深陷這個天下學說盡歸楊墨定於一尊的僵局,何以致之?孰令致之?筆者雖一介布衣,遠處江湖,願不揣鄙陋,效法我國古代那位野人獻曝的精神,以大歷史觀,試為近代西方思潮把把脈。
(作者生於台灣,為旅美民間學者)
Read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