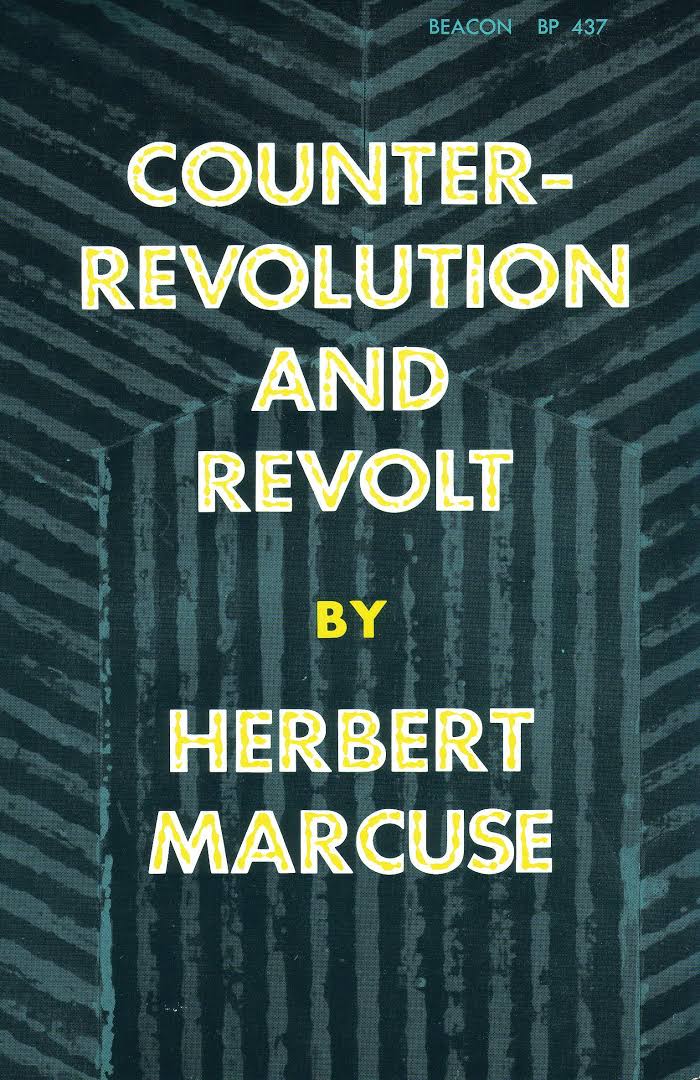【編按】本文為回應武當山〈對不起,我的「含中量」有點高〉一文進一步的延伸,在肯定該文的詰問與批判性之餘,同時從近年「青年反叛運動」,反思人道左派的去政治語言效應,作者為世新大學性別所副教授,感謝作者供稿。
馬庫色於1960年代末期、初來乍到美國從事反叛青年田野時,曾有這樣的嚴厲但深摯的感喟:這群以大學生為主要成員的青年試圖從毛澤東等革命家與當時歐陸的68學潮取得抗爭方向,但從許多反挫的言論與事件顯示出(擬)革命青年無法也不願意脫離形塑西方主體的小布爾喬亞核心家庭舒適思想基礎;他們希冀打倒象徵律法與資本主義的「父」與占有嬰兒慾念所執著的「母」,這樣的套路卻讓周而復始的伊底帕斯情意結永續牢固,亦促使自身毫無罣礙地奔赴至虛無的淵藪。(參見《反革命與反叛》)
促使本文章的激生來自於從去年暑假至今所觀察的一些「青年反叛行動」,最巨大的採樣莫過於「反修例-反送中」群體的表現與修辭。必須先說明,我對於此行動的評價或可稱為節制的不予置評,這個基本態勢與個人層面的情感政治與學術界面的小心翼翼都有關聯。對於黑青的分析,最服膺上述馬庫色的論證之處,在於興高采烈的敵意語言與行動--最明顯者如火焚不贊成此群體的中年男性工人、以磚塊*非刻意*砸死收拾殘敗髒亂場面的年長清潔員,以及使用「我要攬炒」(套用青少年反烏托邦小說《飢餓遊戲》的對白”if we burn, you burn with us)來彰顯微小主體將自身擴大為「我(ego)即世界」、「得不到就悉數毀滅」的嬰幼兒死亡驅力,以及,對於生命網羅(包括但不只於人類)的輕蔑無視。
至於在臺灣島內,從今年二月至今以抗疫新冠肺炎為名目的許多條款,道盡「命」隨時可從無比珍貴到淪為渣滓棄物的完美示範。掌權者或許根本沒聽過阿岡本的「祭物-裸命」理論,卻精彩絕倫地操作了這個論述結構內的每個等式與實踐,尤其以對待「是學生但又是敵對體」的陸生、擁有居留證但並沒有中華民國國籍的「小民」(編註:小明)之酷虐得意手段為後冷戰台式恐異(xenophobia)的最高傑作。
然而,在駁斥此等糟糕手段與顢頇粗暴快感的各種方法論,我認為,訴諸去政治的人道主義(人類中心的永恆自戀)是最無效也最「幫襯」惡質反中反共的不自覺助力。在武當山所寫的文章〈對不起,我的「含中量」有點高〉,作者最後看似提問為立場的「為子孫著想」論點,幾乎是樸素的「為善則有福報,為惡下十八層地獄」的現代性話語。此說法推翻了這篇文章戮力追問的階序暴虐性與國族自戀內核,彷彿只要以普世價值(其實是西方自由派與台式祖先子孫血脈論的混體)的「善」作為方法,就足以抵銷深植於台灣民族主義的「我族」與「瘧畜」之間無可抹除的絕對分界線。
作者沒當成真正提問(也就是視為修辭性問號)的文末結語,反而是我認為值得被視為真實的問題-心態(problematic and mindset)來回應:
是的,很多「我們」恨不得這般的下一代擠滿臺灣,讓血脈(生物與意識形態雙層次)邁向「不中國」的最終境界,打造一個種族甚至物種層面的全新品種。而且,這樣的「下一代」已經大規模地、充滿自主性地竄冒出來。這等情感構造是無可抗拒的絕爽,既是移居殖民主義(settler colonialism)永難擺脫的內在潰瘍,也是維繫「臺灣之光,亞洲民主燈塔」不可或缺的配件。這些「下一代」就是死亡驅力所使役的僭主,以這塊土地之「天命真主」(authentic master of this geographical zone)所自居的自負團塊。
對於當今的執政體系,如此狀態簡直絕佳。在冠狀病毒甚囂塵上、清理地球的此際,這樣的「真台灣下一代」之構築與旺盛生長,不但有效轉移許多無可化解的階級壓迫與主導政權的橫徵暴煉,更是以戳爛歷史筆尖之姿,鞏固了自身的代理者無上權勢。
在肯定本文的詰問與批判性之餘,我想與作者商榷的是,有沒有外於「小孩為大、子孫最高」的思路,來扣問這個以同樣邏輯大量騎劫了年輕世代與人類幼兒的後冷戰臺灣內核?在這個熱血激亢、子彈亂射的惡托邦現狀,意識型態的集體政治效應必須得到說清楚道明白的機會。抗爭的政治經濟學如果不被身處其中的「我們」隨時自我反身質問,背負艱難的不輕易定論,自問不自答,這些義憤填膺的行動不但無法改變沾沾自喜的權力核心,反而造成日後可能的「攬炒」──造就並鞏固了最新型態的歐美帝國主義維穩、單邊的西方話語權,以及無邊綿延的尖酸犬儒島國下一代。
發佈日期:2020/0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