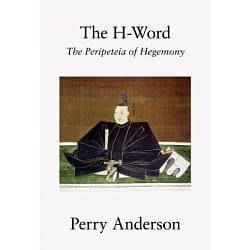◎葉青/編譯,丁雄飛/校
【編按】意大利共產黨創始人安東尼奧‧葛蘭西是一位極具理論原創性的思想家,其「霸權」(hegemony)理論至今仍然受到具有左翼傾向的人們的關注,被人們閱讀、談論、解讀和應用。本文作者Perry Anderson總結了葛蘭西之後四位發展(或挪用)了「霸權」理論的思想家,分別是Stuart Hall、Laclau & Mouffe、Guha、Arrighi。他們來自不同的國家,同時具有不同的理論背景,運用葛蘭西的概念工具研究了不同的問題。比如Stuart Hall關注柴契爾如何獲得英國社會的「同意」,Laclau & Mouffe將霸權改造成populism,Guha則在殖民傳統中思考印度的權力構型,而Arrighi則關注國際的「罷權」是如何運作的。他們為我們提供了解讀葛蘭西理論的不同角度。本文經過作者修改之後,成為The H-word一書的第八章,「Hegemony」一詞於本文譯作「領導權」,本文轉載自2020年7月28日保馬,該譯文原標題為〈誰是佩里‧安德森眼中葛蘭西的繼承人?〉,首刊於「澎湃新聞」!
【原編者按】1960年1月,《大學和左派評論》和《新理性者》合併為《新左評論》(New Left Review)。1962年,佩里·安德森取代斯圖亞特·霍爾,成為《新左評論》的主編,並擔任這個職位達二十年之久。在1976年11月出版的《新左評論》第一百期上,安德森發表了《安東尼奧·葛蘭西的二律背反》(The Antinomies of Antonio Gramsci)。自2000年1月開始,《新左評論》更新換代,重計刊號(見安德森的社論Renewals),到2016年7月,又滿一百期。在這期雜誌上,安德森發表了《葛蘭西的繼承者》(The Heirs of Gramsci),檢討了創造性運用葛蘭西「領導權」(hegemony)概念的四位思想家:牙買加人霍爾、阿根廷人拉克勞、孟加拉人古哈、意大利人阿瑞吉。以下編譯了安德森文章的要點。
今天,沒有哪個意大利思想家享有的盛名能和葛蘭西比肩。不論就學術引用還是網絡查閱而言,葛蘭西都在馬基雅維利之上。1940年代末,葛蘭西的《獄中札記》在意大利經過政治性刪改後面世;1970年代初,英譯本《〈獄中札記〉選》的出版使這些札記在全球被廣泛閱讀。在《獄中札記》的世界性接受中,產生了大規模、大跨度的對葛蘭西概念的挪用,這主要源於葛蘭西思想遺產的兩個特點:
第一,它是多維度的。《獄中札記》涵蓋的主題眾多,左翼理論作品幾乎無出其右。這些筆記針對意大利北部發達資本主義工業和南部前資本主義社會的雙重現實,因而對第一、第三世界的讀者都具有啟發性。
第二,它是碎片化的。在監獄裡,葛蘭西為其無法完成的作品書寫簡短的探索性筆記,這些文字是提示性的而非結論性的。這就促使葛蘭西身後的解釋者將其理論重構為不同的總體性思想。
在意大利,意共基於維護政治路線的目的將葛蘭西的理論工具化,但意大利左翼內部還是有不同的潮流: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一些人把注意力集中在葛蘭西早期《新秩序》寫作中工廠委員會扮演的核心角色,從而把工人自治的觀念和《獄中札記》中黨作為「現代君主」的觀念對立起來。不過,真正對葛蘭西的創造性運用來自意大利之外。八十年代以來,出現了四種主要的對葛蘭西思想的挪用。
驚人的是,這些挪用有許多共同點:它們都來自遠離故鄉的思想家,都出現在八十年代中葉至九十年代中葉的英語文化圈,都圍繞著葛蘭西的領導權概念。
在英國,雷蒙德·威廉斯於七十年代早期肯定並發展了葛蘭西的領導權概念。在威廉斯看來,領導權是一種實踐、意義和價值的中心系統,它比一般意識形態更深地滲透在社會意識當中。領導權包含的複雜結構必需持續更新,以收編另類(alternative)實踐和意義,不過有兩種對抗性的文化能夠逃脫此類收編:新興文化和殘余文化。霍爾發展了威廉斯的觀點,分析了英國政治自1970年代中葉以來發生的巨變,他的研究是對某一特定社會最具洞察力的葛蘭西式診斷 [1]。
1975年,霍爾在《通過儀式抵抗》(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里分析了青年工人階級中的亞文化,指出它們是主流文化內部的潛在反抗區域,而主流文化領導權則保持著一種動態平衡,控制與其抵牾的文化實踐。在《管控危機》(Policing the Crisis)中,霍爾發現在經濟危機的時代,英國社會對青年反抗、黑人移民、工會鬥爭產生了道德恐慌,保守黨已然開始籲請重新施加社會規訓。
終於,撒切爾夫人上台,把貨幣主義的新自由主義和有機主義的托利主義編織在一起,建構了新的社會常識:自由等同於市場,秩序等同於道德傳統。根據霍爾在《通往新生的艱難道路》(The Hard Road to Renewal)裡的分析不難發現,這是一項領導權計劃。而這一領導權的經濟內核(金融去管制化、城市公用事業私有化、中產階級稅收減免等等)其實是葛蘭西意義上的「消極革命」的撒切爾版本,即對某種遲到的現代性的意識形態許諾。
沒有哪種對某個形勢的政治閱讀能夠窮盡一切,霍爾的分析便缺乏國際框架(未曾涉及里根在美國擁有更廣泛基礎的統治),因為它的主要目的是抵抗英國的保守黨政權,提出另一種關於現代性的想像。而霍爾面臨的一大問題是,在英國不存在執行他的分析和策略的工具:英共和工黨都令人失望。此外,對葛蘭西而言,任何完全領導權都需要創造出一種「民族-人民的」(national-popular)意志和文化,但在霍爾那裡,人民的環節幾乎完全抹去了民族的環節。無疑,不列顛從來就不是一個民族,它毋寧是一個早期現代的複合王國,而撒切爾主義鼓吹的帝國認同便是某種應付來自帝國各地移民的多元文化權宜之計。
這也難怪一個擁有牙買加命運意識的人會厭惡纏住「民族的」喉嚨的死結。撒切爾夫人曾驕傲地重申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也曾力促歐洲一體化,但這二者最終成了她給自己設下的套:其時,讓英國走樣的兩股力量——分別來自布魯塞爾和愛丁堡——已然顯現。霍爾的論述卻一點都沒涉及這些,他也幾乎沒有涉及與此相關的撒切爾、布萊爾政權中的暴力因素。他在分析撒切爾獲得社會同意時,過於強調她如何奪取意識形態,而忽略了物質誘因,於是,意識形態彷彿能夠脫離社會錨定似的,在任何政治方向上自由漂移。
1985年,拉克勞和墨菲出版了《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策略》(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2]這本書把後結構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傳統結合起來,雖然在政治上同情歐洲共產主義,但其理論外觀卻完全是後馬克思主義的。兩位作者認為,第二、第三國際仍舊幻想著意識形態與階級的對應,卻無法處理工人階級內部的分化,以及在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以外的階級存在。最早回應這些難題的是列寧,他提出了無產階級領導權的觀念(在無產階級的目標裡帶有農民的訴求),而真正的突破來自葛蘭西:他把領導權的理念改造成某種道德和智識的領導形式,認為領導權的主體並非任何由社會經濟預先構成的階級,而是政治構造的集體意志,這種意誌有能力把各種截然不同的需求綜合為一個民族-人民的統一體。
但葛蘭西的「陣地戰」與「運動戰」的觀點依舊體現出一種本質主義的階級觀念。拉克勞和墨菲認為,不是利益引起了意識形態,而是話語創造了主體位置,於是,今天的目標應當是「激進民主」,社會主義只是其中的一個維度。在後來的《論平民主義理性》(On Populist Reason)中,拉克勞用「平民主義」這個新能指取代了「領導權」,意指各種民主需求被偶然地(contingent)統一為集體意志,束成一股反叛的人民。
如果說霍爾預見了撒切爾主義的興起,拉克勞和墨菲便預言了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應。他們還實現了霍爾無法實現之事:使自己的洞見被擁有大眾支持的政治力量(西班牙我們可以黨)採納。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的理論就那麼有說服力。理論的語言轉嚮導致了某種話語唯心主義,切斷了意義和指涉物的關聯,與社會經濟錨定分離的理念可以被任何政治建構挪用:一切都是偶然性,所有都成了表述。最初,領導權、平民主義被呈現為一種政治類型,繼而,它們變成了一切政治的定義。
在意共傳統中,領導權是一種與地形學無關的策略。同樣在拉克勞那裡,一旦領導權自動變成平民主義的,就無需再精準描述社會圖景了。拉克勞說,平民/民粹主義話語,不論左右,總是不精確的、變動的,這種模糊性恰與異質的社會現實相符。類似馬克思對法國、列寧對俄國、毛澤東對中國、葛蘭西對意大利的細密分析再也沒有必要(或不可能?)了。就像「99%對1%」這樣的口號,領導權話語作為述行話語,與統計學無關。這裡最模糊的是對對立面的描述,拉克勞和墨菲建構的對立面只是抽象的「制度」。於是,在實踐中,領導權變成了被統治者單獨的問題,與被統治者的領導權統一相對的,是匿名的「制度性分化」。
《論平民主義理性》並沒有提供政治經歷作為其觀點的例證,因為政治經歷不光要思考新主體位置的建構,還要思考客觀條件和運行節點。於是,拉克勞便無法解釋,為什麼美國1890年代的平民主義(populism)失敗了,而毛澤東、鐵托、陶里亞蒂這些民族-人民主義者(populist)勝利了。
1970-1971年間,在印度休假的古哈見證了印共兩翼合謀鎮壓孟加拉的納薩爾農民暴動。自此,他決心研究農民抵抗,並在1970年代末召集了一群年輕的印度歷史學家籌備出版一本新刊物——《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3]。這些年輕人同主流共產黨劃清界限,致力於向葛蘭西學習。其時,慣常的關於印度獨立運動的民族主義歷史敘事總是囿於精英政治,古哈號召人們研究庶民階級(工人、農民、非工業城市貧民、下層小資產階級)的鬥爭:印度資產階級無法將他們整合進自己的領導之下。總的來說,《庶民研究》更接近愛德華·湯普森的作品而非伯明翰學派。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份刊物也受到了後結構主義的影響,轉而研究權力的話語建構和文化在意識或行動中扮演的決定性作用。
但古哈本人從來沒有變過。他1983年出版的《殖民時期印度農民暴動的基本方面》(Elementary Aspectsof Peasant Insurgency in Colonial India)展現了農民起義行動和概念的「自主性(sovereignty)、一致性和邏輯性」。借助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不同智識資源,古哈把農民起義視為各種各樣的形式(a repertoire of forms)。不過在重塑印度農民主體地位的過程中,他也絲毫不吝於指出他們的局限性。古哈此後的傑作《沒有領導權的支配》(Dominance without Hegemony)或許是受到葛蘭西啟發的最好著作:古哈的分析模型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葛蘭西寫作中的含混。根據這一模型,在殖民時期印度的權力結構中,包含了一種支配/從屬關係,支配由強制和說服構成,從屬由合作(Collaboration)和抵抗構成:
在任何給定社會的給定的時間裡,權力的有機組成取決於支配和從屬的內部成分的相對權重。領導權作為一種支配狀態,其中說服的權重大於強制。不過,即便面對最具說服力的支配,也總會有抵抗的可能性,並且,也不存在只有說服沒有強制的領導權系統——自由主義所謂沒有強制的國家是荒謬的。
在英國治下,其時印度權力結構中的四個成分皆有特色,每個成分都有殖民和被殖民兩個版本。就強製而言,在殖民國家,強制顯然多於說服,不過當英國著手管製印度時,強制便讓位於「秩序」。而印度傳統的「懲罰」亦成了「秩序」的補充。就說服而言,一方面是「改進」(西式教育、現代基礎設施工程等),另一方面同樣有種姓制度中的道德義務作為本土補充。至於合作,一方面是英國自休謨到早期功利主義的「服從」學說,另一方面是印度「忠誠」的意識形態。而抵抗:英國術語是自然權利傳統中的「正當異議」(Rightful Dissents),印度當地術語是「教法抗議」(DharmicProtest)。
英國統治印度,固然會把強制置於說服之上,形成「沒有領導權的支配」,但為什麼印度的民族解放運動同樣如此呢?民族運動確實激起了大眾的熱情,但印度資產階級領導無法把工農的利益整合進運動,於是這樣或那樣的強制形式便不可避免了。到不合作時期,甘地的規訓系統同樣抑制著人民的平等主義表達。儘管精英謀求領導權,他們卻壓制一切直接鬥爭,唯有訴諸強製手段。不過,當古哈繼續順著這個思路討論印度獨立後國大黨的統治,他高估了其結論的適用範圍。他忽略了國大黨採取的新說服形式得到了後帝國時代的國家和市民社會的支持:普選權、同意機制使該黨擁有了真正的領導權。
上世紀七十年代,古哈在寫作《基本方面》時,曾積極介入印度政治,譴責國大黨濫權,但當《庶民研究》在八十年代出爐時,他卻陷入了政治沉默。這當中存在什麼關聯嗎?或許對孟加拉納薩爾派的鎮壓使他徹底失望了。
在阿瑞吉的著作中,關於領導權思考的兩個脈絡——作為階級間權力關係的領導權和作為國家間權力關係的領導權——第一次綜合了起來。[4]就在霍爾在研究撒切爾主義,拉克勞在研究平民主義,古哈在研究農民暴動之際,阿瑞吉出版了《帝國主義的幾何學》(The Geometry of Imperialism,1977) 。該書沿著英帝國、德帝國、美帝國的序列(以及與之相伴的資本主義轉型),勾勒了帝國主義的連續階段,或曰領導權週期。
此後阿瑞吉去了美國,和沃勒斯坦一起工作,他們相互影響:後者從前者那裡獲得了布羅代爾,前者從後者那裡收穫了葛蘭西。和葛蘭西一樣,阿瑞吉認為,領導權結合了武力和同意,但他的側重點不是意識形態,而是經濟。就國際層面而言,產生領導權的條件是有一個上位的組織、生產、消費模型,這一模型會在各個國家被模仿。如是領導權為國際體系設立了可以預測的規則,給各國的統治集團帶來利益。任何處於領導地位的國家總是聲稱自己是統治者集體權力擴張的驅動力,聲稱其權力的擴張符合一切國家一切主體的普遍利益。通常,這些聲稱能夠變成現實,乃是通過改造既存國家體系,開闢新的資本主義(企業)和領土主義(國家)的結合方式。借助這一分析框架,阿瑞吉在《漫長的二十世紀》(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1994)裡敘述了三個現代領導權:從十七世紀的荷蘭共和國(城邦國家和民族國家的混合)到十九世紀的英國(民族國家)再到二十世紀的美國(大陸國家)。推進這一序列的是資本積累週期:起初,資本主義擴張是物質性的,但隨著競爭壓低利潤,領導國(hegemon)的積累轉向了金融擴張;當對抗加劇、軍事衝突爆發,原有的領導權被打破,系統發生了混亂;最終,新的領導力量出現,在嶄新的基礎上新一輪物質擴張拉開了帷幕。
那我們現在處於歷史的什麼地方呢?阿瑞吉很早之前就認為,戰後美國領導權下的資本主義物質擴張在1960年代末已經式微,並在1970年代為金融擴張周期所取代。但與荷蘭或英國領導權的衰退期不同的是,如今美國的軍事力量仍舊全球領先,儘管就金融權力而言,它淪為了一個債務國,而世界的錢櫃搬到了東亞。但這未必意味著我們又將面臨系統混亂。在阿瑞吉的後期著作《亞當·斯密在北京》(AdamSmith in Beijing, 2007)裡,他開始思考這個世界如何最終擺脫資本的邏輯和領導權週期:既然布羅代爾說資本主義並不等於為市場生產,那麼,斯密設想的市場社會有沒有可能提供一個馬克思描繪的、平等主義的資本替代方案?阿瑞吉最後的希望在於,基於世界諸文化、文明的相互尊重,出現一個以東亞為中心的世界市場社會。
在1970年代阿瑞吉去美國前,「勞工」曾處於他理論綜合的核心位置。但這一概念在《漫長的二十世紀》裡消失了:他坦言,在一個由金融化的動力機制支配的結構中容納勞工太難了。對馬克思來說,工人階級將是資本主義的掘墓人,一方面他們擁有現代工業賦予的集體力量,另一方面資本的逐利邏輯使他們生活淒慘:因為前者他們有能力顛覆資本,因為後者他們不得不然。但歷史弔詭地把這二者分開來了。在勞工力量鼎盛的發達工業社會,工人選擇了伯恩斯坦的改良主義道路;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東方,物質上的慘境為列寧的革命道路創造了主觀條件。自1970年代經濟衰退以來,這兩條道路都陷入了危機:生產外包至南方削弱了西方的工人階級,工業化強化了東方的工人階級。當波蘭誕生了團結工會,韓國、巴西產生了罷工潮,馬克思的預見開始成真。然而,雖然在與西爾弗合著的《現代世界體系的混沌與治理》(Chaos and Governance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1999)裡,阿瑞吉謹慎地預測了新一輪社會衝突的可能性,但在《亞當·斯密在北京》,此類動盪仍處於邊緣位置。
阿瑞吉早期的理論資源對他後來的著作產生了兩方面影響。他1970年代早期在意大利領導的小組屬於工人主義(operaismo)潮流的分支,而工人主義高估了美國勞工運動和羅斯福新政的成就。作為這一傳統的繼承者,阿瑞吉彷彿忘記了支配集團作為普遍利益代表的欺騙性,認為美國能夠向外輸出全球福利模式,這為他後期不再關注勞工埋下了伏筆。無疑,全球國與國之間的不平等遠甚於西方發達國家內部階級與階級之間的不平等。另外,阿瑞吉的小組還把葛蘭西的「工人自治」理論化,從而無暇關注「民族-人民的」主題,這也在他身上留下了印記。在他對葛蘭西遺產的改造中,國際體系的維度遠比民族國家的維度重要,民族內部的領導權結構在他那裡十分薄弱。阿瑞吉經常引用古哈的「沒有領導權的支配」來描述美國的衰弱,但他忽略了一個重要區分:領導權的組成在國際政治中和國內政治中非常不同,就前者而言,強制的比重遠大於說服。
葛蘭西的四位繼承者所做的貢獻是政治和理論結合的產物,他們都經歷了戰後的激進政治高潮:英國新左派,阿根廷民族左翼社會主義黨,印度共產黨,意大利工人主義。在1970年代早期經濟低迷之後的政治低迷中,這四位思想家顯示瞭如何在不利於行動的條件下,繼續在思想前沿領域工作。領導權是四位思想家共同的核心,但他們各自的側重不同:霍爾側重階級統治的意識形態複雜性,拉克勞側重控制策略,古哈側重庶民群體的生活,阿瑞吉側重最先進的生產形式。他們也藉助了馬克思主義之外的思想資源:霍爾借助了巴赫金,拉克勞借助了拉康,古哈借助了列維-施特勞斯,阿瑞吉借助了布羅代爾。可以說,他們每個人都繼承了葛蘭西的一部分,但如果把他們的寫作放在一起,或許產生了一項集體的事業。
譯校者註:
[1] 這是英語界解讀葛蘭西的關鍵,即理論闡釋者根據自己所處語境對葛蘭西理論進行重新闡釋,安德森雖然指出了霍爾的局限,即抹去了葛蘭西的民族的環節,同時只強調撒切爾政權的同意方面,而忽略了其中的暴力方面,由此在強調撒切爾如何獲得意識形態同意時,忽略了其背後的物質誘因。但在霍爾的闡釋中,有兩點仍需要注意:一、葛蘭西的“領導權”只是一個理論工具,一種中性的統治手段,用來分析英國社會,尤其是撒切爾時代的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策略。另一方面,他似乎將領導權看作主流社會的領導權,一種壓制性的權力,絲毫沒有積極意義,他耿耿於懷的是亞文化的反抗,因此撒切爾實行的領導權規劃在他看來當然是壓制性的,正如安德森所言,他的闡釋丟棄掉了葛蘭西“領導權”的核心定義——即民族-人民的集體意志。
[2] 拉克勞和墨菲將葛蘭西的領導權進行了後結構主義的闡釋。他們更關注的是“誰掌握領導權”,換言之,誰是領導權的主體?而這個問題之所以產生,則是由於工人階級內部分化問題,也即是說階級退場,身份政治出場的問題。帶著這樣的後設問題,他們認為列寧的貢獻在於,他不再執著於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區分,而是看到了其他階級的存在,其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包含了農民這個兩大階級之外階級的訴求。列寧正視了階級分化的難題,工人階級領導權的觀念正是對這個難題的解決。而他們認為葛蘭西是對這個難題做出突破性解決的人,即讓領導權變成道德和智識的領導權,文化領導權,由此領導權的主體不再是特定的社會階級,而是通過政治構造出來的集體意志,即各種各樣的意志、話語融合的產物,這自然而然導出了「身份政治」和「激進民主」。有著各種不同身份、族裔、性別的人拼接成一種集體意志。而拉克勞後來所用的「平民主義」(populist),「平民」,是有著各種身份的大眾,這完全不同於葛蘭西有著階級內涵的「人民」。安德森一針見血地指出,這種闡釋受到了理論的語言轉向的影響,很容易陷入話語遊戲,僅僅成為表述,而與社會經濟層面失去聯繫。領導權成為了話語領導權,被統治者用來反抗“抽象的”壓制性話語及製度的工具,因而失去了與現實社會變革的聯繫。
[3] 印度的《庶民研究》以及我們所說的底層研究很出名,古哈受到葛蘭西的影響也在必然,因為葛蘭西的領導權理論中隱含了庶民研究的基本理念,要想獲得大眾的領導權,必須首先承認大眾有一套自己的哲學,一套既有的價值觀和處事方式,也即「自發哲學」,因此研究庶民的「自發哲學」變得十分必要,只有用實踐哲學融彙和改造「自發哲學」,將合理的、積極的、主動的因素吸收進去,將迷信、混亂的部分去除出去,才能形成對大眾的道德和智識領導權,最終形成統一的集體意志。如何將自發的群眾運動導向有領導權的鬥爭也是葛蘭西反复論述的問題。古哈強調農民起義的積極性、一致性和邏輯性,同時也看到其局限性,正是來源於葛蘭西的理論靈感。古哈還在《沒有領導權的支配》中對殖民時期及民族解放運動時期印度的權力結構進行了分析,其運用葛蘭西對領導權的經典定義,即強制與說服的二分法來建立分析模型,看到印度政治中強制總是多於說服,甚至在民族解放運動期間也是如此,資產階級領導根本無法將底層民眾的利益訴求整合進運動中,從而只能通過強制的方式完成。
[4] 阿瑞吉的闡釋更關注國際間的而不是國家內部階級間的領導權問題,阿瑞吉從國際視野和長時段研究視野,關注整個世界的領導權週期。因此,他對葛蘭西的領導權進行了改造再利用,雖然其認為,在葛蘭西那裡,領導權=暴力+同意,但在領導權週期的敘述中,領導權似乎等於資本主義經濟擴張加普世價值,而其更強調前者的作用,他經常用沒有領導權的強制來描述美國領導權的衰落。但阿瑞吉顯然丟掉了葛蘭西領導權具有的更重要的民族國家維度。*葛蘭西領導權的民族國家維度值得思考,現代君主,集體意志,建立民族國家。
發佈日期:2020/1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