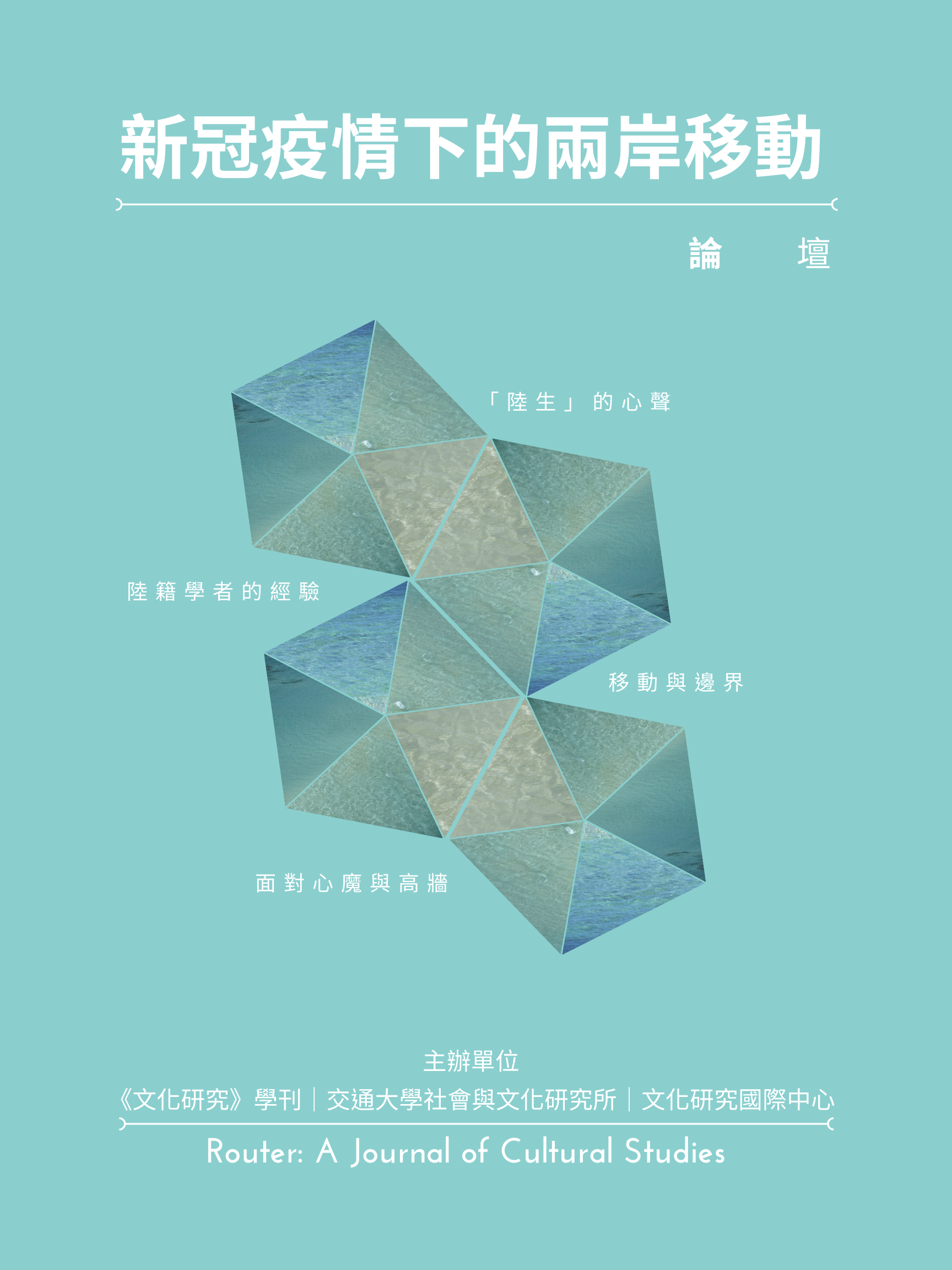【編按】即便中國大陸疫情趨緩,「小明」們仍舊比不上其他國家的外籍配偶,至今無法回台。今年年初新冠病毒發生後,在臺求學與工作的陸港澳學生和博士後研究員,以及過年回鄉省親的大陸配偶立即面臨,因為防疫特殊處置而無法返臺、或被迫滯留第三地的窘境。同時,也有在大陸工作的台商和台商因此無法返回工作崗位,甚至在兩岸對奕的緊張態勢中蒙受不必要的指摘。雖然疫情尚未過去,防疫的邊界管制亦未消除,但相關措施已然對他們造成傷害,也讓兩岸關係的前景蒙上一層陰影。尤其4月9日中國大陸教育部宣佈暫停陸生來台升學就學的試點工作,不僅加劇兩岸關係的惡化,更實質地影響了「陸生」的權益,乃至未來兩岸高教的地景。是故,《文化研究》學刊、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文化研究國際中心舉辦了「新冠肺炎下的兩岸移動」論壇,並希望藉著舉辦一系列的文章,向受到影響的朋友們表示關心和致意,並且展開對「陸生」、「陸配」以及其他兩岸身份的討論。同時,也希望透過不同視角的觀察,思考兩岸移動的未來。本文為該論壇系列文章之一,前一篇為:孫賀︱何以解怨:一個「前陸生」的「後陆生」體悟。本文作者為朱凌毅,現為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博士後研究員,研究跨兩岸的移動。本文原刊於2020年6月11日《文化研究》學刊網頁,感謝《文化研究》學刊與作者朱凌毅授權轉載。
兩岸關係怎麼會無用呢?兩岸題材不正是在這次新冠疫情的挑撥、計算與污名化之中大有用處嗎?與其說無用,或許該說兩岸關係已經來到無法再修補的殘破終點了吧?憤慨和絕望這兩種感受都非常真實,但未必有助於我們拆解兩岸關係的意義。
當前,全世界幾乎所有國家都是封閉起來的,但諷刺的是,台灣此時卻彷若前所未有地更加走進了全世界。自我感覺無比良好,光榮感無比高漲。台灣以防疫模範的角色,獲得世界中的位置,讓世界看見。不僅新聞報導紐西蘭總理借鏡台灣防疫經驗,台灣與美國甚至簽署了防疫合作聲明。有意思的是,當世界的國境邊界愈閉鎖,對台灣來說,彷彿進入世界的邊界愈開敞,只是,我們還人進不了WHA和WHO。
但我們其實都知道,這一切都只是暫時的。這是一場全球災難,緊急事件。沒有人不希望脫離現在的緊急狀態,而且愈快愈好。問題在於,什麼事情會隨著緊急狀態的結束而消逝?又有什麼會留下?有哪些邊界會重新縫合?有哪些邊界將無法再跨越,變成一大塊疙瘩,永遠地糾在那兒。
防疫,國家機器動起來
國家總是不斷利用邊界措施,對我們進行區分和篩選。日前非洲豬瘟流行之際,台灣的機場邊境防疫工作已然升級。邊檢單位區分出豬瘟疫區,凡是從疫區抵台的航班,都要全面接受隨身行李檢查,至於來自非疫區的旅客則可經由「綠色通道」,也就是原本的正常方式通關。到了此次新冠肺炎大流行,台灣亦對不同國家地區發布旅遊警示分級,並且實施不同的檢疫和隔離措施。其中,針對不同身份(陸客、陸生、甚至滯陸台商)的差別待遇,仍是當前爭議所在。
然而,曾幾何時,我們已然習慣了不斷升級的邊界管制?從911事件開始,邊界通關開始變得複雜,從要脫鞋、脫大衣、卸皮帶,逐漸變化,甚至得要被全身360度掃描。我們可能不太記得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在大陸各城市搭乘地鐵紛紛開始需要讓X光機掃描隨身行李;也在不知不覺中,遍地已然裝設攝像頭,透過人臉辨識讓人無所遁形。(但此次疫情,當所有人都載上了口罩,應該對人臉辨識大大不利)。此時此刻,在大陸無論搭乘大眾運輸或投宿旅店,都需要掃健康碼,交待過往的定位和足跡。
所有的安全升級,都需要危機。當危機來了,我們願意被「超前佈署」。這時我們不太有底氣去追問所謂的超前是否「過當」。然而,危機過後,這些佈署未必會就此取消,很有可能它們仍在前面等著我們。於是乎,例外成為常態。既成常態,就不覺得國家機器在動。但我們沒有感覺到國家,不表示它沒有作用。我們之所以沒有感覺,或許是因為它成為了我們「意識型態」的一部份(此謂意識型態國家機器)。但是國家(state)之所以值得研究,並不在於它隱身於意識型態之後,反之,國家其實不斷以透過危機,創造例外的方式展現自身。主權(sovereignty)表現在例行體制的懸置、破壞與超越,主權是在體制之上,而非在其之中。也就是說,國家需要自我破壞體制以展現主權,國家正是透過不斷地自我否定而能夠被我們認識。
防疫,把不是自己人的人趕出去
所謂自己人或共同體,是指可區別於他者的有機相互連結。共同體可以是一種身份或是一種角色。一般而言,所謂身份,通常是指主觀的自我認識,而角色則是客觀的社會期待。社會期待自己所應扮演的角色可能經常變動,並且我們自己可能也需要同時扮演多重角色。角色可以是演出來的,也是可能透過學習得到的。相對地,身份則比較固定、單一、真實、且通常是既定的、學不來的。然而,這樣的區分未必普遍適用,更重要的是,它可能無助於理解共同體如何被形構。
透過邊界視角,我試著重新定義身份/角色:跨越邊界不變的是身份;以邊界加以分類的是角色。也就是說,身份關乎跨越和「移動(mobility)」,而角色則關乎分類的「重疊與多重(multiplicity)」。如果沒有移動的事實和多重類別的重疊,就不需要身份和角色,也就不需要共同體。因此,當我們把共同體想像為穩定的實體,但實際上它卻是因為多重流動而被需要,乃至被想像而產生的。法國思想家儂晞(Jean Luc Nancy 2003)指出,「共同體從來沒有發生過」。他強調,共同體「與其說是被社會破壞的固有的有機關係,不如說是社會建立以後所發生的問題、等待、事件或命令(imperatif)」(27-28)。這表示,共同體同樣是在不斷地自我否定中被認識的。
當我說「無用的兩岸關係」,是在仿擬儂晞的「無用的共同體」。「兩岸關係」作為一種共同體的想像,本來就是用來表達彼此的「一家親」。然而,我們現在熟悉的「兩岸關係」這詞彙原本並不是這麼用的。透過查詢新聞資料庫,可以發現「兩岸關係」一詞在1970年代之前,只出現在美國要處理中國問題時使用。亦即,它原本反映的是美國指涉中國問題的外部視角,並不是用在大陸與台灣相互指涉彼此關係。直到1980年代中期,大陸和台灣才開始愈來愈來頻繁以「兩岸關係」相互指涉。此時,兩岸之間出現愈來愈多諸如走私、探親等課題,需要相互協調。更重要的是,隨著大陸改革開放,中國開始逐漸成為世界資本拓殖的邊疆沃土,而台灣則發現自己作為世界資本進入中國之帶路者的利基。台灣作為中國進入世界、世界進入中國的中介,大陸與台灣都同時需要走出相互對抗,重新找回一家親的角色和身份。唯有如此,「兩岸關係」可以被經驗與想像。
瘟疫中的兩岸關係
“Never waste a good crisis”,是英國政治家丘吉爾的名言。事實上,國家不會放過任何一場危機。此時此刻危機當頭,我們需要對國家如何利用危機保持警覺。在「超前佈署」中,我們需要緊盯著有哪些緊急應變措施成為了剝奪與壓迫的藉口,而被放大並持續?有誰從中獲利?又有什麼新的危機被創造出來,以轉移目前的危機?
另一方面,我們同樣也要對共同體有所警覺。或許不少人的疑問是,當前的兩岸是否已經是殘破的共同體了呢?兩岸是否已經成為無法修補的關係?我認為問題恰不在修補,因為修補的前提在於認定它原本是穩定的實體。兩岸關係正如任何共同體的打造,都是在處理流動的身份與多重的角色,把它想像成實體無助於解決我們的憤慨和絕望。如今,當台灣不再是世界與中國的中介,說不定對於大陸與台灣來說,都會是一個發展更健康關係的機會。問題在於我們要一起做什麼?還有「一起」的意願嗎?我們當前分別面臨哪些問題、在什麼意義上彼此需要?這關係著我們如何可能重新想像、經驗與實踐一個不同的關係空間、一個不同的兩岸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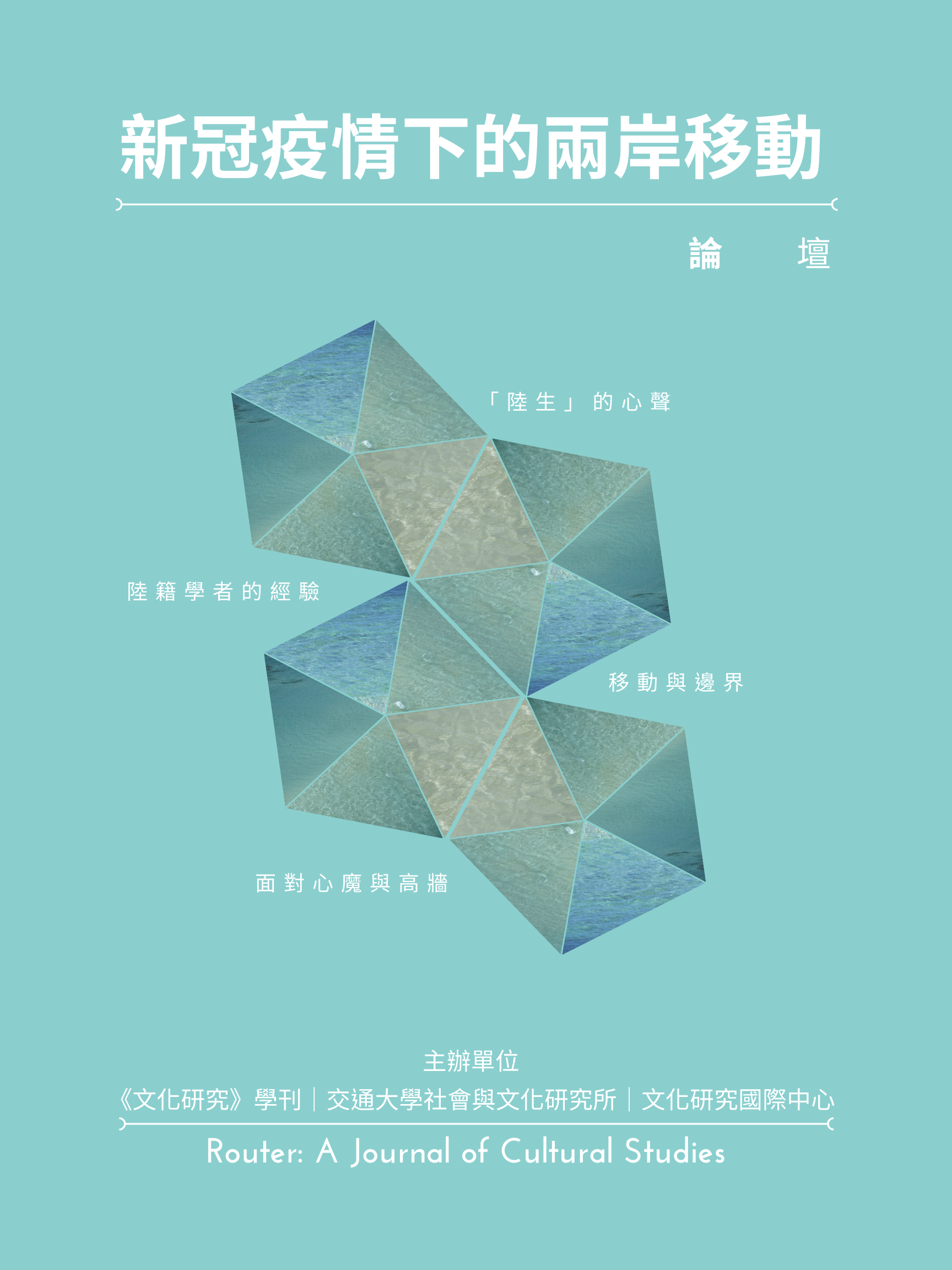
發佈日期:2020/0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