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雜誌》第十六、十七、十八期,連續刊登了三期的〈泛談當前台灣農村經濟問題〉座談記錄(1969年1月17日在台北耕莘文教院舉行),全文共三萬字,討論的方向大致歸納了五點:(一)、雙重經濟下的台灣農村經濟,(二)、農村人口的外移與農業勞動力不足的問題,(三)、保護工業與農業用品價格偏高問題,(四)、發展工業與農工業用地問題,(五)、二十年後台灣農村景象的展望。這份文件至關重要,因為參與座談的成員多數畢業於美國知名的農業經濟學碩、博士(李登輝、許文富、吳同權、史濟增、劉錚錚、賴文輝),另外二位與談者分別是當時是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副研究員文崇一(短暫在哈佛大學就讀)和服務於糧食局的統計室的陳榮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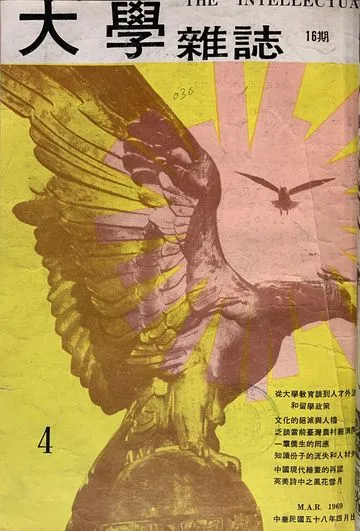
這場座談會記錄了當時他們對台灣農業的建言與政策鋪排,是經濟理性的產物,其觀點幾乎主導了往後的台灣農村、農民和農業的發展。參與座談會的成員關於「雙重經濟」的論點或許有些微的差距,但是基本上是為台灣走上由美國扶持的資本主義軌道出謀獻策,篤定無疑的必須補上資本主義的課。雖然如此,這些戰後第一批留洋的西化派菁英,依然具有《大學雜誌》知識份子的經世濟民的底色,他們也多次強調:台灣農村即使為工業化的原始積累服務的過,也應避免農民巨大的損失,也提出降低農工之間不平衡發展的眾多建言。可惜的是,台灣剛經歷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整肅,具有歷史性的社會主義實踐的農業合作化互助組織或思維,必需隱藏起來,致使「綠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的第三世界後發的資本主義農業生產(農藥化肥、機械化等)的發展路徑幾乎成為不言而喻的共識。這個轉向對於往後近一甲子的台灣農村社會起了重大影響。

回到1969年的台灣,當時耕地面積有九十萬公頃,從事農業人口達六百萬人,佔人口約50%。當時農家耕地面積不到二公頃高達90%,約有農家85萬戶,耕牛約三十萬頭。因此,如何解決遲緩的農業生產力的問題,幾乎成為這個座談會的共識。在這個座談會上,美國Vanderbilt大學經濟學碩士劉錚錚認為「雙重經濟就是進步的資本主義的交換經濟部門,與落後的傳統部門,同時並存於同一個經濟社會內的意思。」他認為台灣農村處於落後是因為市場狹小、分工缺乏、技術落後與商業化程度低。
康乃爾大學農經博士李登輝分析光復初期的台灣,台灣人民的平均國民所得不到美金六十元,作物的單位產量與土地生產力太低,傳統農業若無政府介入金融挹注與技術改善,就無法推進工商業的進步。李登輝擔心台灣的雙重經濟「將要消失」,他舉了日本與非洲的例子,他說日本經濟效率高,但是農業產值還是很低。非洲殖民經濟,白人資本家不提高農業生產力,因為生產力提高,工資所得提高,就有原始積累(capital accumulation),殖民主義不需要資本積累。李登輝提出農業現代化要加快加緊,針對勞動力、所得分配與利潤等生產因素下手。
因此,關於農村的勞動力運用與機械化問題,成為座談會討論的第二個重點。畢業於美國賓州大學農經博士許文富的推斷,根據農家記帳資料分析,台灣農家每戶的勞動供給一年平均798工作天,但是實際需要量為518工作天,主要是農業旺季與淡季的勞動力需求不一。許文富提出農村未充分之勞動力是否可以移出?他給出的答案是不可能,理由是台灣的勞動剩餘並非以個人為計算單位的勞動剩餘,而是由許多家庭成員之零碎勞動所湊合的綜合過剩,隨便移出一個勞動力,生產力肯定降低。許文富認為台灣農村能夠移出的勞動力是20%,而非50%。吳同權也認為農村的勞動力是高估了。怎麼應付農村勞動力的危機?包括劉錚錚、李登輝、賴文輝等人認為耕耘機是可以考慮的方向。
當時全台灣的耕耘機只有一萬台,只能耕作台灣十分之一農地,並且農機太貴、農地不平整不力機械種植。許文富提出一個有意思的方案;讓縣農會成立農耕中心,每個中心準備農耕機幫農民代耕。吳同權呼應機械化的方向但是必須讓土地重劃的政策上軌道。但是問題來了,因為現代農業化所需要的農藥、化肥、機械、抗生素、飼料等有賴工業供給,但是當時這些農業資材昂貴,加上還要負擔水利工程的80%,農戶苦不堪言。往後實施的農地重劃,出現混亂、私相授受、農地損失、共有地拆解等問題。
有趣的是,文崇一問李登輝:「政府是否故意增加財政上的負擔?」李登輝回答:「這個問題就是我要說的了,政府是故意把農民的收入壓下去,使從事農業工作的人轉業到工業去的,但是沒有想到以後的結果是怎麼樣。」文崇一又說了,那不能全搞自由經濟啊!李登輝回說:「還得要保護政策。」文崇一又問,你有辦法嗎? 李登輝說:「最好的辦法是:現在的農產品價格不要管制,讓市場自由去決定……」李登輝認為農產品價格上漲,工資也會漲。李登輝的保護政策,政府應該降低肥料價格、減稅。

關於座談會第四個問題,就是農工業土地的緊張關係。畢業於美國明尼蘇達州農經碩士吳同權擔心工業用地已經在散漫零亂的無計畫狀態下擴展,而且轉移為工業用地多屬優良農地。吳同權分析對於農業土地轉移工業地的問題有土地自由化與管制化兩派的主張;土地自由化的理由是每公頃土地的生產價值工業高於農業達數十倍或數百倍,良田通常位於交通幹道,水電供應方便,勞力來源廣。劣田的工業生產成本較大。自由化派認為損失的農地所生產的農產品,可依靠進口。管制派認為農地要加以限制在於農產品要確保工業、民生、r軍糧的供給。應該利用劣地來發展工業用地,因為農業用地的要求比較高。吳同權非常反對土地自由化發展,理由是忽略社會利益。他認為政府要介入劣地的開發,投資道路與水電的公共投資。隨後,包括劉錚錚、李登輝、、許文富陳榮波等人呼應了吳同權的看法,建議多設工業區與多用海埔新生地。
這個座談會的最後一個提問:「二十年後台灣農村景象的展望?」賴文輝總結出幾個論點:一、全面性農業機械化;二、家庭農場規模每戶五公頃,農戶減為二十萬戶,農村勞動力將至20%;三、改善農民住家環境,家家電氣化、戶戶有汽車。無奈的是,不到二十年的時間,1987年,國民黨政府受制於美國的壓力,要求進口美國水果,衝擊到當時東勢水果農,引發了一系列的全島農民狂飆街頭的行動。
回顧1969年由《大學雜誌》主導的這場三農座談會具有指標性的意義,這群在戰後留美的海歸派的確有不同於民族主義的有限視野,從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座標對當時台灣農業的問題盤整,也在下鄉調查的基礎上診斷三農的未來。可惜的是,農復會依然是當時由美國主導的,台灣農業政策的代理人與決策機構,就遑論農民的代表性了。
FREE MONEY FREE MONEY FREE MONEY FREE MONEY FREE MONEY FREE MONEY FREE MONEY FREE MONEY FREE MONEY FREE MONEY FREE MONEY FREE MONEY FREE MONEY FREE MONEY FREE MONEY FREE MONEY FREE MONEY FREE MONEY FREE MONEY FREE MONEY FREE MONEY FREE MONEY FREE MONEY FREE MONEY FREE MONEY FREE MONEY FREE MONEY FREE MONEY FREE MONEY FREE MONEY FREE MONEY FREE MONEY FREE MONEY FREE MONEY FREE MONEY FREE MONEY FREE MONEY FREE MONEY FREE MONEY FREE MONEY FREE MONEY FREE MONEY FREE MONEY FREE MONEY FREE MONEY FREE MONEY FREE MONEY FREE MONEY FREE MONEY FREE MONEY FREE MONEY HACK TUTORIAL HACK TUTORIAL HACK TUTORIAL HACK TUTORIAL HACK TUTORI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