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按】本文由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政治系助理教授 Inés Valdez所撰。文章探討了2021年國會山莊騷亂與2024年3月凱伊橋倒塌事件之關聯,這兩件事怎樣反映帝國協議失敗與西方民主國家的民粹浪潮。作者指出,西方民主國家的繁榮曾依賴資本與勞工的結盟,這種結盟是以對殖民地人民的剝削為基礎的;到了後殖民時代,這種剝削並未消失,而是演變成新的壓迫形式。
文章提出種族民粹主義的興起,反映了西方社會對後殖民秩序與全球化資本主義利益分配崩解所作出的反應。若要建立真正民主的世界,西方國家必須擺脫帝國主義的思維,挑戰全球和國內的資本主義體制。
本文由孫訥翻譯、盧倩儀校對。
民粹主義在西方民主國家得以興起,跟帝國的協商失敗有莫大的關係——民粹主義就是想復興帝國的一種隱蔽要求。過去富裕民主國家之所以可以日益繁榮,仰賴的是資本與勞工結盟;而這種結盟之所以結得成,本身就是透過帝國對殖民地人民的征服來實現的。後殖民秩序並未消除西方民主國家對帝國主義的癮頭,而只是催生出了一種新的奴役、剝削和壓榨形式。因此種族民粹主義的興起,是對「後殖民秩序」以及「西方大眾藉全球化資本主義分到好處」之安排雙雙崩解的反彈。若要在新自由主義的衰敗之上建立一個真正民主的世界,那麼西方社會就必須擺脫根深蒂固的帝國主義習慣,並挑戰國內和全球的資本主義。
2021年1月6日,一群暴徒襲擊了美國國會大廈,目的是阻止正式宣告拜登在美國總統大選中獲勝。三年後,也就是2024年3月26日,馬里蘭州「凱伊橋」(Francis Scott Key Bridge)被貨櫃船「達利號」撞到後倒塌,船上載著4700個貨櫃箱,上面有來自印度和斯里蘭卡共21名船員。橋上5位來自墨西哥、瓜地馬拉、薩爾瓦多和宏都拉斯、正在修路的道路施工人員不幸罹難,而有多名船員在事故後被困在船上將近三個月。這些事情看似無關,但將它們放在一起思考便能看見政治與資本主義之間的關係;這些關係是當代不滿情緒的核心,也是極右翼政治能吸引富裕世界公民的原因。

1月6日國會山莊騷亂的暴徒是受到川普當天稍早在白宮發表的種族言論所激化。這場創造了至今仍影響深遠的「停止竊取」(Stop the Steal)口號的演講,特別針對亞利桑那州和喬治亞州,指其可能存在選舉舞弊,暗示是拉丁美洲裔以及黑人的組織動員讓拜登贏下這兩個州。然而這種顯而易見的敵意卻跟另一項事實共存,即所有美國人的生命都要仰賴這些群體(就物質條件而言)才得以維生。3月26日凱伊橋倒塌事件讓這事實變得很明顯,當時脆弱的拉丁裔和南亞裔工人在剝削條件下工作,他們的生命悲劇地短暫交錯。雖然當時焦點是放在碼頭工人以及重建橋樑的迫切性,但從另一角度切入就能看到被嚴重剝削的種族化勞動力在維持基礎設施方面扮演的核心角色,讓包裹能送達我們家門口,並確保我們每日通勤順暢。1月6日和3月26兩件事放在一起看就能看出種族化群體同時是政治排斥以及超級剝削的目標。針對那些被徵召來維持我們生活的人們進行詆毀,是一種一邊打擊他們一邊坐享其成的策略。更具體來說,他們在全球北方(作為移民)和全球南方(作為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條件,都是基於兩項彼此交纏的先決條件:公民權被剝奪以及遭受剝削,且沒有前者就不會有何者。這些因素加起來才撐起了全球北方社會。
如我在下文所將闡述,極右翼反移民的歇斯底里大行其道之所以發生在危脆(precarity)蔓延至富裕世界、而衝突與貧窮迫使人們離開後殖民世界之時,並非偶然。雖然殖民主義在20世紀形式上是結束了,但後殖民秩序保留了全球北方自由民主國家「核心」對全球南方新主權國家「邊陲」的剝削性統治。這些種族化的政治奴役、資源汲取以及勞動剝削讓西方民主國家繼續在殖民與後殖民全球秩序下維持繁榮。當富裕世界的工人所享受的相對繁榮開始崩塌,西方民主國家的社會焦慮不是針對那些財富劇增的人,而是針對那些依據後殖民協議,應該繼續屈從的群體。如果我們希望在新自由主義消亡後會出現一個相對公義一些的世界,那麼民主國家就必須反思他們爭取正義的方式,不能再像從殖民時期延續至今一般地要求別人臣服於自己,而要反抗全球範圍內對所有種族化他者的剝削與非人化。

二十世紀西方民主的陰暗面
西方民主其實是20世紀初期到中期,在帝國背景下,透過一步步賦予白人工人階級選舉權而形成的。就像我近日出版的《民主與帝國》(Democracy and Empire)書中所論述的,白人工人階級在放棄了激進的反資本主義要求、並默許跟資本家一起分享帝國贓物後,得到了選舉權。過程中政府扮演了媒介,而工會藉機施壓政府,要其承諾社會福利制度,使福利國家在戰後達到黃金期。要理解這個時期的工運就必須將它放在帝國的語境下分析。例如定居殖民為窮人及失業人口提供了逃生閥,防止大都市發生勞工動亂,並為白人工人在工業化的英國提供了擺脫赤貧、向上流動的機會。向外移民到英國殖民地的工人成為定居者,在當地為自己爭取選舉權,同時也幫來到同一塊土地的非白人外國人爭取土地和工作機會。在這段期間,英帝國官僚針對勞工、流動性與移民問題在裡進行了激烈的辯論,最終,政府管控移民的制度不以限制外國人進入為宗旨,而是將移民融入帝國勞工管制制度。儘管形式上移民制度處理的是外國人事務,但它設立的目的並非為了排斥外國人,而是要建立一個層級制度。移民管制並沒有排斥白人外國人,而是將他們納入到國家體制內,並滿足他們的自治主張,包括限制非白人的華人、南亞人移民至澳洲、南非和加拿大的機會。要是沒有成功阻擋這些族群移入,群眾運動就會努力爭取合法地讓華人、南亞人做到最艱苦的工作,使得剝削他們變得更方便。而美國的辯論也沿著類似的路徑展開。辯論原本聚焦對華人的限制,後來則轉向對墨西哥勞工的依賴,他們的「優勢」據稱是良好的身體耐受性、能耐得住在田裡艱苦地工作,而且用完能很容易遣返或驅逐回墨西哥去。這種以種族分層級的移民制度目的是控制勞工,確保在有需要時隨時能取得廉價可剝削的勞動力,同時也防範多數種族化移民參與政治的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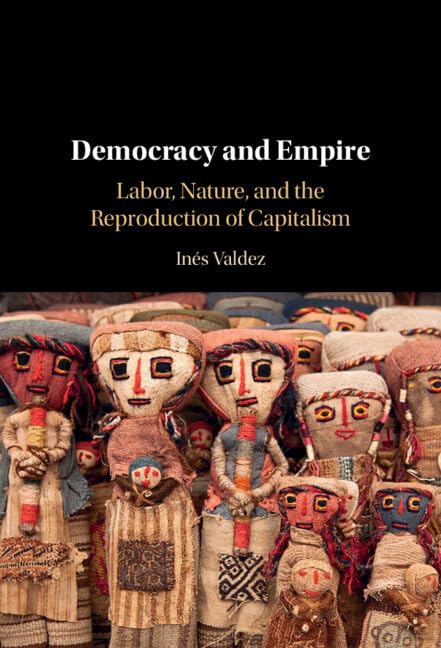
白人與非白人在定居殖民地的分工也能在全球分工裡看到:海外種族化工人的任務是提供食物和原材料,餵飽工業化世界的公民和機器。這種結合移民和全球種族化分工的制度在20世紀有些演進,但對於那些被針對的種族他者群體來說,並沒有實質的改變(相較之下,南歐與東歐人則更容易流動並獲得白人身份)。這在今天仍十分明顯,例如種族化移民在西方的照護、零工、農場與營建產業比例奇高,在當代剝削嚴重的榨取性經濟和出口導向、依賴低薪工人的勞動驅動成長的諸如服裝業和高科技工廠亦然。歷史上,全球南方國家曾打過反殖民戰爭,並反抗強加於它們的反民主發展模式。但最後這些發展模式還是被西方支持的專制政權強加在它們身上,並由被收編的、致力安撫和維穩的本地精英加以落實。而後這些壓迫手段又被「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下的結構改革政策進一步強化,並透過新自由主義或新發展主義的民主政權執行。
因此西方民主的歷史,也是一頁帝國將世界塑造成專為這繁榮之島服務的歷史。這些國家國內工人階級的政治與經濟解放其實依賴了透過武力和壓迫取得的國外資源的挪用及重分配,過程中摧毀了被征服地區的社區,為的就是服務資本積累。因此這些帝國計劃中的民主公民在兩個因素的作用下團結在一起:第一、在佔有感的指引之下,為了攫取資源而專制地幫其他地方的人民設定規則;第二、民主國家彼此之間互惠的政治關係。這兩個因素讓民主國家獲得授權,可以剝削全球南方再將資本主義獲利重新分配,前提就是西方民主國家公民認為自己有權制定與全球南方互動的規則。這種我稱為「自他決」(self-and-other-determination)的帝國式的民主在國外引發強烈抵抗,並透過發動殖民戰爭(如越南)、武裝友好的軍隊、支持政變以防止社會主義者(如瓜地馬拉的阿本斯、智利的阿葉德)掌權等作為製造了許多衝突。這種互動模式助長動盪,因為它將社會衝突軍事化,無論是廣義而言以維護投資「安全」之名用鎮壓方式來對付社會抗議及要求進步的聲音,或是具體而言將毒品的使用和交易這種社會經濟問題當作安全問題來處理。

帝國協議的崩解,也是西方民主的崩解
將時間快轉到現在,將福利國家解體以及阿茲瑪諾瓦(Albena Azmanova)所描述的「危脆的流行」(Epidemic of Precarity)也納入考量。「危脆的大流行」可以理解為「社會對生命而言成為威脅而造成的權力被剝奪之脆弱狀態…使人因為責任與權力不符而感到無力招架。」帝國的協議正在崩解。毫不令人意外,正如馬克思在他有關英國和愛爾蘭勞工的著作裡所預言的,白人工人階級把決定權交給帝國和資本主義的結果只是徒增資本主義傷害工人的力量:資本主義面對危機的方式是開始收回國內「民主協議」。與此同時,我們也目睹了極右派以煽情方式將移民描繪成潛在威脅,而且在許多國家,移民問題日益被轉化為跨政治光譜的安全問題。成功到達英國—歐洲世界的移民其實只是總體移民的很小一部分。世界各地的移民是真實地為了逃離貧窮、暴力衝突,與氣候變遷而出走,他們遠在尚未抵達歐洲或美國邊境前即可能因為各地軍事化的邊境而客死異鄉。換句話說,他們是在逃離資本主義的蹂躪。
這種蹂躪是資本主義和白人工人階級協議的另一面。就像前面提到的,要在全球南方取得足夠資源和可剝削的勞動力,就必須買通願意幫忙管理人民的當地軍事和文職精英,協助帝國榨取勞動力和天然資源。衝突、氣候變遷,以廉價勞動力為基礎的發展模式促使人們向外遷移,而資訊的普及與交通的便利讓移動變得更加容易。眾所周知,大多數流離失所的人都留在本國或鄰國。對於那些冒險前往英美世界的人來說,取得有尊嚴的勞動條件非常困難。相反的,移民管制軍事化為脆弱和剝削創造了理想的條件。這對於成功穿越軍事化障礙的無證移民或尋求庇護者來說特別明顯。近年跨越美墨邊境、沒人陪伴的未成年人淪為童工,使美國童工數量激增,這體現了脆弱狀態與剝削二者間的關係。
因此西方帝國民主兩大支柱(支柱1:資本與勞工一起分享帝國贓物;支柱2:他們對那些為確保資本主義能穩定榨取之被剝削勞動人口的「安撫」或恐嚇)的危機讓帝國民主失衡。就像阿茲瑪諾瓦在其《邊緣上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 on Edge)所言,這自然導致焦慮與威脅感,但我想說的是,這種焦慮與帝國協議的崩解有關,而人們卻在要求恢復那協議。也就是說,西方喧鬧沸騰暴躁易怒的大眾對危脆的反應不是要求重新思考資本主義,也不是調整他們的生活方式使其不再以剝削他人,反而是將自己的不幸歸咎於移民和難民。故意用視覺及煽情的方式處理移民問題是在暗示他們沒留在「他們原來的地方」。易言之,種族化主體犯了罪,他們沒有謹守帝國所規定的勞工移動模式,如官方明文認可的「客工」計劃或海外勞工的剝削。但說是犯罪,又不全然是犯罪。因為現在監控非法人口的作法只不過是將帝國契約奴工及戰後客工制度加以更新而已。新穎之處在它另闢蹊徑創造出新的可供剝削人口(如凱伊橋上的修路工人,他們沒有適當的通訊工具,也沒安全小艇),而且還符合都會及定居工人階級所認可的形式。

甩掉民主的帝國主義癮頭
以上關於帝國民主歷史的敘述顯示,西方政治與解放模式仍沈溺且受困在帝國和資本主義之中。這樣的敘述也挑戰將移民框架成是關於主權國家邊界控制權的意識形態機制。相反的,我將當代移民管制機關視為等同於一種全球種族化勞動控制體系,目前是由民主的民族國家在管理。
這樣一個描述民主和移民管制的架構允許我們從歷史視角,更完整地評估當代極右政治以及左翼的反應,而非繼續依賴去歷史化的當代評論,把移民看成是某種「發生」在社會身上的一件事。比如說最近一篇反思歐洲轉向民粹主義的文章就指出:「無論這種恐慌的感覺多麼不理性,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包括美國,在面對這種被大規模移民(合法或非法)所激發起的恐慌時能愉快地把問題處理好,歐洲人也不例外。」在學界,移民被視為是市場驅動的全球化所帶來的又一種新的「流動」,並引起專制或右翼民粹主義的反彈。但這樣的論點反而引出另一個問題:為何對全球化的反彈都帶有專制、極右翼的色彩?只有以上所提出的對帝國民主的歷史敘述才能正面回答這個問題。簡單來說,移民是危機的核心所在,因為移民的增加是全球南方衝突和危機擴散的症狀。這些危機本身就是資本主義榨取系統因過度剝削社區和天然資源而不再穩定的指標。這個事實,加上資本主義精英就算是面對本國同胞也日益自私傲慢的事實,顯示西方民主國家內部資本和勞工之間的帝國協議正逐漸崩解,並滋長了某種懷舊需求——過去比較「有秩序」、良好被隔離(因此必須種族化)的福利樣態。很重要的是,現在與過去這種面對非白人移民時的種族主義反應,皆助長了愈來愈多以暴力方式落實移民管制制度與監控手段,從而將種族化的敵意和暴力轉化為勞工控制以及資本積累的手段。
換句話說,反移民是帝國—種族—資本主義的大逆襲,它依賴種族敵意來創造更多資本累積的機會,只不過這一次(很大程度上)它拒絕給予西方工人階級社會福利議程。此外,本文提供的診斷也凸顯了左派政黨可能會再度回到20世紀初期帝國社會主義的危險。值得注意的是,在拜登宣佈給予無證配偶假釋的措施前,他頒布了一項跟川普的政策雷同的行政命令,允許邊境人員在某些條件下暫停提供移民庇護。另一方面,新上任的英國首相施凱爾(Keir Starmer)將「非法移民」列為政府的首要任務,並承諾「不會再有更多移民」,而他的方法是使用「反恐式的策略」來打擊提供移民橫渡英吉利海峽管道的「幫派」。而法國左派新人民陣線(New Popular Front)則拿出了令人欣慰的對比,他們的立法契約建議修訂歐洲和法國的庇護政策、成立救援機構、擴大申請庇護者的工作權及公民權。然而除非在賦予工作權以外,也拿出正視全球資本累積過程(而非僅求保護國內民眾不受資本主義之苦)的更果斷反資本主義計劃來伴隨(令人欣慰的)人道主義措施並進,那些措施本身是不夠的。因此西方左派在當前危機時刻面臨的挑戰是,怎麼回歸到他們最初反資本主義的綱要並將其全球化,而不是只盯著越縮越小的公共預算在國內的分配是否公平,卻對暴力的全球秩序以及資本主義的破壞袖手旁觀。袖手旁觀在目前的左派裡面已是算好的了,最壞的情況則是像現在西方國家的許多左翼政府,繼續利用政治籌碼和軍事力量來維持和擴大企業的影響力,唯一結果就是更加強化企業行為者而非一般人民。

左翼可以走的另外一條路是致力普世勞工正義,方法是讓西方公民不必將自己獲得利益這件事建立在全球南方的移民和工人付出代價的基礎上,而是藉由直接打擊企業及富有精英的權力。像「工作保障」、17美元基本工資以及「每周四天工作制」這樣的計劃都是旨在保障工人福祉的良好案例。但這些提案應該要是全球性的,就像2%富人稅提案一樣。這個提案如果不是全球性的,就會只是個不痛不癢的提案。衝突以及機會的缺乏助長了移民問題,因此要面對這個問題就有必要了解:全球南方缺乏機會是(資本主義)設計出來的結果。這正是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學者所點出的,也是出口導向、廉價且不受保護的勞工導向的成長所持續展現出的事實。依賴理論學者和其他批評資本主義的評論家帶給我們的另一教訓是——資本主義是個全球體系。假如是這樣的話,那麼一個不挑戰全球勞動分工的左翼反資本主義計劃,就沒在挑戰資本主義。只著眼國內的左翼計劃不碰觸資本主義全球影響力(或甚至透過國際組織和外交政策助長資本主義)的結果是讓自己陷入危險。因為以國內為中心的反資本主義在兩種意義上並不只是中立而已:第一,它允許資本在國外不受羈絆地累積,這就強化了資本主義精英在國內的力量;第二,它保護自己的選民/工人的方式是允許並且收割對種族他者的持續剝削。因此左翼政黨擁抱反移民措施真正的危險不僅在於讓自己走上與極右一樣的移民限制和軍事化之路,也在於這種左翼根本無法真正挑戰資本主義。短期而言,藉著邊境軍事化以及收買過境國家來壓制移民或許比較便宜,但只要移民輸出國和接收國的條件沒有同時獲得顯著改善,移民就會繼續,而資本主義無論是在全球或是國內層次都只會愈發強大。
近日,一些評論家已察覺到了這個現實,但他們並沒有將全球驚人的薪資不平等歸咎於財富從邊陲國家向核心國家移轉的歷史事實,反而認為這「創造了地球上最大的套利機會」,套利方法就是透過「安全數位身分」來管理臨時客工計劃,並對那些將臨時移工用在超出這法律框架範圍的企業祭出罰則。的確,以暴力方式來落實創造不平等的全球勞動分工,再結合軍事化的邊界與種族敵意,確實創造了套利機會!透過「限時勞動力流動」提供低工資勞動力機會來解決西方的人口危機,同時利用數位科技和懲罰來確保帝國利益得到保護,這正是傷口撒鹽的真義。此外,這其實根本不構成一個新「解決方案」,而是當前非正規、受高度監控的移民勞工體系結構的一部份。
總而言之,極右翼運動在歐洲和美國日益流行,透露了公民希望消除非白人主體,或將他們排擠到社會更邊緣的地方的願望。這是重蹈覆轍:富裕國家的民主國家人民對資本主義密集剝削種族化勞工視若無睹,只希望從帝國的利益中分到更大一杯羹。這種衝動對於左派來說並不陌生,左派的解放取向往往太過狹隘地只關心國內工人,他們的怨憤被假定為與資本主義在國外製造的全球弊病無關。然而這是錯的。若不重新把資本主義挑戰定位為全球挑戰,左派就沒有出路。在本文寫成之際,我們看到了歐洲與美國極右翼崛起。我們必須了解,1月6日國會山莊的暴動、三年後凱伊橋倒塌事件,這些都是西方民主國家持續存在的帝國主義取向的症狀顯現。我們必須深入探討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作用如何讓拉丁裔修路工人和南亞裔船員交錯在巴爾的摩一個撞擊力強大的撞船事件中——這次事件曝露了種族化、被剝削勞工如何以地下的方式撐起西方民主國家。1月6日的暴動中對種族化群體的種族仇恨透露了一些有關我們所處的民主政體的一些重要訊息。藉著拉高那些所謂「受到種族化政治進程威脅」的白人公民,我們的民主延續了白人公民加入資本主義計劃作為次要合夥人的傳統,卻讓國內和全球的種族化勞工繼續為了服務資本積累而處於脆弱與被剝削的位置。當我們面對這種仇恨的重新崛起,我們的挑戰是如何消除整體結構,而非跟著搖旗吶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