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劉健芝老師和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是多年的好友,劉老師於2005年和許兆麟老師合作編譯《庶民研究》一書。2021年7月13日,晚上22:00,「南南論壇」邀請了《庶民能發聲嗎?》(Can the subaltern speak?)著名文本的作者、印度思想家佳亞特里.C.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講座,「南南論壇」發起人、嶺南大學教授劉健芝應《澎湃新聞.思想市場》之邀撰寫本文,梳理斯皮瓦克的思想脈絡。本文轉載自全球大學Global U,首發於澎湃思想市場,感謝劉健芝老師授權轉載。
邂逅在港大
跟佳亞特里.C.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第一次見面,是在2002年6月香港大學的會議室。當時,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主辦「公共批判與視覺文化」暑期研討會,邀請斯皮瓦克主講。我的本科、碩士、博士學位都是在香港大學修讀的,碩士、博士論文導師是全球布萊希特學會的會長安冬尼.泰特婁教授(Anthony Tatlow),也在學校裡聽了很多老師談後結構主義、新左理論的課,其中包括阿克巴.亞巴斯(Ackbar Abbas)等,都是我非常敬佩的有深厚人文關懷的君子。2002年,我已在嶺南大學任教15年,作為亞洲學者交流中心(Asian Regional Exchange for NewAlternatives, ARENA)的主席也有9年了。亞巴斯老師跟我說,斯皮瓦克指定要跟我來一場對話,談理論與實踐的互動關係。這次對話,開啟了我和斯皮瓦克的友誼。對話後,斯皮瓦克建議,我們倆應更深入交流,合寫一本書,中、英文同時出版。於是,接下來的半年,我們多次見面討論、聊天。不幸的是,2003年的非典疫情,打斷了她來香港的安排,也中斷了我們的面對面交流,當年沒有像現在那麼便捷的互聯網溝通方式,不知不覺中,出對談集的計劃延宕了。

在研討會上對話
從1996年開始,我們嶺南大學翻譯系(後來轉去文化研究系)的幾位同事,分工編譯自己最感興趣的題目,集結成「另類視野:文化/社會研究譯叢」,繁體字版由牛津大學出版社推出,出版三集後,我們和汪暉、戴錦華、孫歌等內地學者合作編纂,由中央編譯出版社推出簡體版。汪暉和許寶強合編《發展的幻象》、戴錦華和陳順馨合編《婦女、民族與女性主義》等,我對另類歷史觀感興趣,把相關的書籍找來看,雄心壯志想編幾本書,介紹Allen Ginsberg、Michel de Certeau、Walter Benjamin等大師的理論。要編一本選集,必須讀大量文章再從中挑選,於我而言是很好的學習機會。自1996年開始,連續多年,我每年幾趟去印度的喀拉拉邦,探索民眾科學運動和邦政府推出的人民計劃運動的理論和實踐,對印度歷史產生很大興趣,搬回來一大摞書,其中有「庶民研究小組」(Subaltern Studies Group)領頭人古哈(Ranajit Guha)、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等歷史學家編輯的系列,叢書從1982年到2005年,總共出版了12本。因此,我在「文化/社會研究譯叢」的第一本(後來沒繼續出版,所以是唯一一本),就是與許兆麟合作編譯的《庶民研究》。我們毫不吝嗇時間的投入,有一次,在嶺南的課室裡,我們幾位編輯用了三小時討論一個名詞如何翻譯,最後決定,加腳註也沒法傳達名詞的複雜內涵及其社會文化背景,所以要在每一本書的後面加上關鍵詞解說。在當時的學術界,出版中文書籍不被重視,對評職稱完全沒好處,但是,對我們來說,那種不計較名利、只為知性研習推介新思潮的日子,是那麼的快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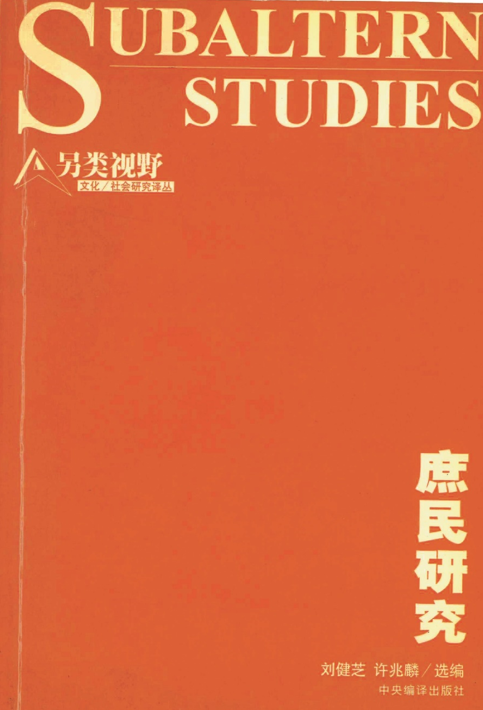
編纂《庶民研究》時,我們收入斯皮瓦克一篇題為「庶民研究──解構歷史編纂」的文章。嚴格來說,斯皮瓦克不屬於「庶民研究小組」這個集體。據她說,1981年構思、其後發表題為「庶民能發聲嗎?」(Can the subaltern speak?)的文章時,沒聽說「庶民研究小組」;後來接觸了,跟古哈合編了《庶民研究精選集》。斯皮瓦克的論述補充了婦女問題是結構性的問題,不是邊緣的問題──「庶民研究小組」成員大多數是男性,談工人、農民,談封建關係、殖民霸權,卻忽略了性別在維持權力結構中的關鍵作用。經過一段時間合作後,因為「庶民研究小組」只談印度、不接受斯皮瓦克對南非問題的討論,因此停止了合作。
我編譯《庶民研究》時,還沒認識斯皮瓦克;在香港大學相識後,一見如故,聊理論,也聊身邊事,特別是身為女人的處境。斯皮瓦克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第一位被聘為「大學教授」(即講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僅授予少數十來位傑出教授的名銜)的有色女性教授,至今只有兩人,有色人種女性在精英白人父權社會所受的壓力,可想而知。我們認識時,我與江西貧困山區農村婦女們的交往已有8年,斯皮瓦克在印度偏遠農村為賤民婦女辦學比我更早8年,我們有共同話題、共同感受。斯皮瓦克說,她在兩種極端之間的講學,是那麼惹人熱議──她的學生,一邊是美國精英學府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生,另一邊是印度山區小學的賤民婦女。她讓自己泡在兩個極端的環境裡。她最討厭人們恭維她在農村辦學,她說,「要恭維就恭維我做得棒的理論工作」,然後會補充上一句,「沒幾個人這樣恭維我!」
「庶民能發聲嗎?」
斯皮瓦克自1968年開始翻譯、最終於1976年出版雅克.德里達的《論文字學》(Of Grammatology)的英譯本,寫了洋洋數万字的譯者導言,嶄露頭角。德里達是阿爾及利亞法裔猶太人,出生在二戰前,從內部遭遇西方哲學,批判西方哲學中的歐洲中心主義。斯皮瓦克的導言,闡釋發揚德里達的解構理論。
《斯皮瓦克讀本》編者如此概括斯皮瓦克的知識軌跡:「在過去十五年,她的學術生涯循著一條複雜的知識軌跡發展,有對解構理論的深刻的女性主義視角考察,有對資本和國際勞動分工的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有對帝國主義和殖民話語的批判,有對與民族性、族裔性、移民工身份相關的種族問題的批判,也有對新殖民世界之下的後殖民國家和文化的批判。這樣的知識軌跡為斯皮瓦克贏得了紛紜多樣的國際讀者。」
斯皮瓦克在後殖民理論、文學批評、女性主義、教育理論等方面,均有突出建樹。可是與她的名字不可分的,是她的文章「庶民能發聲嗎?」 兩個關鍵詞有多個中文翻譯版本,subaltern有如下翻譯:庶民、底層人、被殖民者、次元、屬下、屬下階層、從屬者,至於speak,則有發聲、言說、說話、發言…… 由於這篇文章在後殖民理論中佔據經典地位,後來者紛紛以此為題發揮,寫了諸如Can the subaltern vote?(庶民能投票嗎?)、Can the subaltern be felt?(庶民能被感知嗎?)、Can the subaltern securitize?(庶民能自衛安全嗎?)……
我選擇翻譯為「庶民」。其實,重要的不是名字的選取,而是概念的緣起、使用、語境、文化社會背景,特別是能帶來怎麼樣的批判思考。Subaltern一詞,出於意大利共產黨人葛蘭西(Antonio Gramsci)關於社會霸權問題的討論。「庶民」原來是軍隊用語,下級、從屬者的意思,通過紀律訓練必須接受上級指令、服從上級制定的規則標準。葛蘭西被囚禁在監獄,所有書信被當局審查,沒法直接用上「無產階級」等政治用語,因此,他筆下的「庶民」,有時候被視為「無產階級」的代名詞,也可被視為標示沒有權勢的社群。有別於馬克思主義的經濟主義,葛蘭西提出霸權的說法,是要探討霸權關係在文化領域的作用,即數量上是少數的統治集團如何使為其一己謀取利益的價值、標準、世界觀,成為多數人認同接受的東西。要理解這個狀況便要探討庶民的歷史。
斯皮瓦克和「庶民研究小組」筆下的「庶民」,不簡單是「無產階級」的擴大或引伸。斯皮瓦克經常強調,沒有人可以說「我是庶民」。聽起來比較抽象,但是,在她的理論發展軌跡中,「庶民」的界定不在於身份認同的層面,而是指涉排除在任何社會流動的可能性之外的狀況。「狀況」不是人,不是階級,但處於這種狀況的群體,一般是社會邊緣群體,因此這些群體可用來標示「庶民性」,猶如風帆之於帆船。在書寫庶民歷史方面,借助斯皮瓦克的理解,我們可以說「庶民」指的是關係,「庶民」一詞總是相對於「精英」(elite)而言的,即「庶民」不是指「現實」中的「實體」,「庶民」沒有內在的本質。「庶民」標示的是主導社會的不平等關係,是弱勢相對於強勢的位置。「庶民」更多是一種視角,從弱勢的位置來看支配關係,藉此拆解支配關係所依靠的霸權論述。
作為一種視角,借助尼采的詮釋,是批判西方哲學傳統沿用的關於知識的過於簡單的概念,拆解所謂不偏不倚的純知識的神話,突出知識總是在特定的時空、特定的互動關係和張力中形成的,就是說,知識有其歷史,求知者在其所置身的世界有欲求、有恐懼,承載著種種印記的身體存活在特定的時空,在我們的「世界」中,因我們有所求、有所拒、有所取向,知識才成為可能。視角是我們認知能力的起點,讓我們了解身處的世界所形成的強勢的習俗和典章制度,如何在我們身上烙刻痛楚和折磨,如何塑造我們的感情和取向,如何塑造我們的混亂和矛盾,也如何賦與我們和這一切角力的能力。知識生產與其說不偏不倚,不如說是建基在推動知識建構的取向、慾望和與權力的勾結。
如何研究庶民歷史?
如果說「庶民」是處在歷史邊緣的群體,研究庶民歷史就不在於增加、豐富「人類」的知識庫,不在於補充主流學術權威所認許的歷史的遺漏,而在於在過去看似不可能活動的處境中看到可能活動的空間。主流的歷史敘述,把一切明確和不明確的東西在因果分明的邏輯關係中賦予位置並組織起來,追求嚴謹科學性理路清晰的敘述。主流歷史敘述的權威,依賴的是「理性-非理性」的二元框架,讓人們接受其重「理性」、輕「非理性」的傾向。在這種二元框架中,事實和虛構的分辨不但是「真」和「假」的分辨,同時還是「客觀知識」和「主觀想像」的分辨,意味著「知識」必須絕對客觀,不受任何個人的情感左右。於是,「知識」不可能是一般的經驗,因為一般的經驗不可能沒有情感的作用。於是,守衛和生產「知識」的「知識分子」不可能是一般的人,因為他們必須能夠超越一般經驗。換句話說,知識分子要通過接受學術、科學的訓練,才能有超越「一般人」的成就,即成為「精英」。簡言之,科學關於真實與幻象的分辨,跟「精英」和「一般人」在社會上的劃分是同構的。和事實與虛構(真/假)緊扣一起的劃分,有理性/非理性、正確/不正確、科學/迷信、現代/傳統、客觀/主觀等的劃分,這是學科的權威依賴的好/壞標準,「好」的能成為權威的一部份,進而鞏固維繫權威的機制,「壞」的只能被排斥到邊緣位置。
主流歷史以其權威成為普遍被接受的歷史,我們研究庶民歷史,就是要尋找被忽視和屏蔽的,在我們自身的經歷中,看到總是說不清楚、曖昧、不能確定、偶發的感情,如何左右我們的思想行徑,進而質疑現代社會的等級關係被合理化的運作邏輯。現代社會科學各門知識不但和種種社會控制的技術關係緊密,其建立更有賴於維繫、生產、繁衍權力關係的機制的運作,即社會科學在社會制度、生活組織、以至每個人的「自我」的打造,都有關鍵的規範作用。福柯在這方面有精闢的論述,我們編纂的第一本「另類視野:文化/社會研究譯叢」,題目就是《學科、知識、權力》。
我們提出了精英-庶民的相對關係,那麼該如何看待這個相對關係呢?是否通過否定「他者」來確立自己,以「庶民歷史」取代「精英歷史」?在精英歷史書寫中,被置於邊緣、不被重視的角色,甚或只能在暗處窺見其影子的角色,或只能在落後、非理性、叛亂等指責中佔一席位的角色,是否現在反過來成為敘述的中心、成為歷史書寫的「英雄」,而在精英歷史書寫中的「英雄」現在則成了「丑角」?
我們要看到,精英和庶民的相對關係是充滿矛盾和張力的關係,但不是兩個獨立實體的對立關係。所謂「精英」或「庶民」是對相對關係中的不同位置的命名,而這些位置又是由多重不平等的支配關係交錯折疊而構造的。不平等的支配關係可概稱為政治、文化、經濟、社會、性別關係等。「精英」和「庶民」的相對關係是對相對固定的不平等關係的一種說法。可以說,這樣的關係是不同作用(本身也是交錯複雜的權力關係網絡)交錯下形成的「果」。因此,「精英」和「庶民」指的是在權力關係中相對固定下來的不同位置,不平等的權力關係才是其存在的條件,而不是什麼出於自身的本質,也不是假設了本質上對立的二分法。
如帕拉卡殊(Prakash)在「後殖民評論和印度史學」一文中所說,「庶民」在維持支配關係的論述中被置於邊緣隱形的位置,「庶民」被看成沒有什麼價值和重要性的,能從支配者/精英的位置上說話的論述中留下痕跡也是很勉強的事情。因此,要從刻滿了一層又一層支配者/精英的言辭說法的哈哈鏡零散的碎片裡,重整「庶民」完整的面貌是不可能的。造成庶民歷史不可能的哈哈鏡碎片,不僅僅是殖民統治精英的問題,也是為獨立事業奔走的民族主義精英的問題,殖民統治訓練出來的民族主義精英也讓造就帝國擴張和殖民統治的現代理性和人文主義銘刻他們的靈魂。
因此,探究庶民歷史,與其說是窺探哈哈鏡裡零散的碎片,不如說,是從哈哈鏡的反照中,質問「知識分子」的作用。洛特(David Lloyd)指出,為現代化論述收編的知識分子,在現代/傳統等二分法的規範下,只能陷於國家主義貧乏的形式主義中,沒有能力認識人民的「同時代性」的創造力,只昧於尋求把人民改進為有現代精神的現代國民。知識分子這種置身於領導者之位置發言的理所當然的想像,正是現代「中心」對「他者」的控制,而控制的一個重要手段是「同一化」。
「現代理性」的權威,其實是通過制度確立的封閉的「自我中心」,把「他者」看待為「中心」不能容納的顛覆的威脅,是封閉的果,亦是製造、鞏固封閉的實踐。因此,庶民歷史研究不是為了補充權威史學確認的歷史──精英歷史──的不足,更不是要取代精英歷史,而是跟踪精英歷史施行刪改、壓抑、排擠「他者」的痕跡,從中動搖其封閉的二分法確立的價值觀以及由此產生的表意和敘述的封閉。要根本動搖主導的邏輯,便不能走重複這樣的邏輯的路,所以庶民歷史研究不是要尋找、還原庶民的「聲音」,讓其「聲音」在主流歷史中佔一席位。古哈稱眾多的「他者」為眾多的微弱雜音。即是說,庶民不是一種聲音、一種說法;庶民歷史研究是要聆聽眾多微弱的雜音、殘留歷史的回音。聆聽紛杳餘音、細察零碎殘影,是要讓「微弱的」、「紛亂的」釋放出動搖支配邏輯的偶合力量,讓不同的故事、不同的視野、不同的關係得以繁衍。
「新庶民」
在2008年的一次演講中,斯皮瓦克回顧了她的庶民理論的軌跡,明確地說,庶民所指的,不是特定的人,而是指「subalternity」,可翻譯為庶民性、庶民處境、庶民環境,即斷絕了邊緣群體有社會上升流動可能性的社會關係與權力結構。問題不在於庶民能不能發聲,而在於庶民不被聽到、不被認可,因為由精英主導的主流社會根本不會注意他們、聆聽他們,或者視他們為社會整體的一部分。提出庶民性的思考,是她作為教育者,省思自己的角色,一方面努力進行漫長持久的教育,著眼學生的主體性構造,期望他們在非強迫性的條件下有慾望的轉移,打開視野。同時針對庶民在全球主導文化的孤立狀況,她通過潤物細無聲的教育工作,打開庶民的想像,突破孤立經驗的樊籠,思考庶民作為國家的一部分,面對主流精英的邊緣化壓制時,能從其現實中抽離,思考國民與國家的關係,思考參與公共領域的民主實踐。
如果說「舊庶民」談的是邊緣群體被撂到邊上、拋棄在現代「公民/人民」社會的整體之外的話,斯皮瓦克提出,庶民現在面對新的狀況,即全球化主導文化的滲透,這反映在庶民(例如原住民)的語言結合了主導文化片言只語,但反過來原住民的文化卻不能無條件地與殖民者文化交流,因為在科學的名義下,本地知識/原住民知識,被奪取剽竊,被轉化為數據,成為強權的私有財產,成為知識專利產權(例如,跨國藥業去亞馬遜叢林蒐集草藥然後申請專利),這是當今不可忽視的狀況。主體性塑造的教育,一方面要讓全球北方的學生突破科學的邏輯和世界觀,看到原住民知識體系的本身價值,同時協助原住民在融入數據洪流之時,能堅持傳統知識和經驗的完整性。指稱「新庶民」,是為了突顯邊緣群體被自上而下、從中心到邊緣的力量所滲透,但滲透力量的流動是單向的。斯皮瓦克強調,資本主義現代社會這幾十年的演變,進入數碼年代,庶民身處的社會關係,只是以不同形式延續精英社會的自我繁衍。
說到底,斯皮瓦克讓自己泡在兩種極端環境的教學工作裡,更好地體會社會的不公、排斥、分化如何延續,而教育者不斷要自我警醒的,是顛覆封閉性,轉化為開放性。知識分子的「認知失誤」(cognitive failure),既是認知的不可能,也是認知的可能性條件。
發佈日期:2021/07/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