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篇遲來的電影觀後感。二〇一九年首映、由徐漢強執導的《返校》賦有特殊意義。這是從影藝史的宏觀角度而言。它包涵某段特定時空的時代韻律;其特色之顯著,讓人辨認出電影所屬的製造背景。這一時期的影視作品具備共同的特徵,它們此起彼落,共譜枯燥乏味的樂曲。概言之,這些影視作品預設同一框架,製作人擠進各式文本,繼而擬仿出調子相彷的現實,形塑特定的世界觀。以上論點的前提,是電影不能再現現實,它們只能擬仿現實,卻可呈現一定程度的「真實」。我們不妨把觀影體驗及其後的分析視作思辨的過程;若然如此,所謂真實則不是別的,即驚險的思辨旅程結束後,幫助我們起步的踏腳石如實呈現其錯誤之時。銀幕(或電腦屏幕和音效配置)向我們呈現的、由聲畫交錯綜合而成的影像經驗,便是旅程的起點。據此,我們會發現電影展現的世界觀是有所缺陷,但缺陷的世界觀卻是製造該齣電影的前提,作者和其他人(製作人員、目標觀眾,以及他們身處的社會)自覺或不自覺地浸淫其中。戈達爾曾說,「鏡頭的擺設已是一種虛構」,也是表達類似的道理。因為導演選擇了哪些事物需要呈現,哪些不用呈現;決定他所決擇的,便是預設了的世界觀、用作展示素材的文本框架。故此,當我們從《返校》的改編電影入手,或許能診斷出某一特定時空下的「時代精神」。本文聚焦《返校》的電影版,原版遊戲擱置不論。
話在前頭,《返校》改編電影是一場失敗的驅靈儀式。這齣電影的風格是如此獨特,編導竟毫不猶豫、露骨地把如鬼魅般糾纏我們的過去記憶——即白色恐怖戒嚴時期的記憶——直接表達出來,宛如雕刻師販賣未經雕琢的石像。記憶是驅不散的幽靈,不確定性是它們的鮮明特徵,就像潛伏家居角落的鬼魂,似有還無,介乎生死之間。普遍意義的「過去」,對於人們來說,是虛無縹緲、無法觸摸的「存在」。這是奧古斯丁式的時間迷思(當然,還涉及「自我意識」的統一問題,還有先天綜合的困惑,實在龐雜,不贅述),我們意識到的,永遠是純屬當下的「現在」,沒法直觀「過去」與「未來」,還有時態變易的分界線。未知是萬幸或不幸,人類大腦也不如電腦晶片,沒有紀錄一切的記憶能力。有時候,我們視昔日往事為異己之物,譬如讓人尷尬的醉後亂話或遙遠的童年時光;有時候,人們會將似是而非、道聽塗說的事當作親身經歷。朦朧的記憶,亦包括了集體的記憶。史書沒有記載的——未有合適的名相,暫稱作——遺史,以夾雜神話的秘卷經文,或是民族歌謠的形式,代代相傳,一直纏繞人們的思緒。據此,人們不難發現當代的對應物。都市傳說和網絡傳言等事例,證明了各種幽靈般的記憶貫徹始終,與時俱進,持續在人類社群擴散,築起屬於集體的記憶。由此,我們須懂得區分「記憶中的幽靈」與「幽靈般的記憶」;前者純屬靈異的玄學範疇,後者卻泛指記憶獨有的虛幻特徵。兩者容易混淆,以至出現二合一的情況。在佛教的葬禮儀式上,比丘們要求家屬一起頌經,其目的是雙重的。既超渡逝者,又超渡親友的心;消除在世的人對死者的執念,好讓亡者的中陰(antarābhava,bardo)安然往生。撇開怪力亂神,佛家的方法,可能是處理往昔的幽靈之最佳手段。人們的記憶和思念,隨葬禮的終結化作虛無。
台灣戒嚴時期,國民黨飽受內戰挫敗,失據至台島的他們,為了維繫其脆弱的統治權,黨國機器的齒輪便急速轉動起來。除了移植過去在大陸施行的間諜系統,祕密警察和已被招安的黑道潛伏各地,還作嚴厲的高壓管治,當中包括黨禁和新聞審查。黨政府的一切舉動,僅想剿滅他們眼中的敵人,即國民黨自覺的唯一威脅,在叢林中鬼影幢幢的共產黨員。當時的資訊傳遞不如今天,獨靠紙媒和收音機,這些媒介較受時空及經濟條件所限;此外,除了少量非法流通的黨外刊物,黨國機器牢牢掌握傳媒話語權。種種一切,造成社區資訊難以傳播,訊息的空缺可被想像填充;各城各市的非官方消息,市民遭受黨政府殘酷對待的事件,通通以口傳耳授的形式散播,漸成困擾人們的集體記憶,宛若鬼魅般的存在。
與其說,《返校》講述戒嚴時期的蒙難者冤魂不散的故事,不如說電影將那段特殊的遺史與無主孤魂劃等;這不是象徵或比喻,而是一種簡白得有點過分的表態;編導僅將記憶的幽靈特性如實呈現,彷彿透露了不想再被記憶糾纏、欲見冤魂安息的簡單願望。從此意義看,整齣電影是萬人參與的驅靈儀式,好讓參與者告別被怨魂纏繞的生活。哪怕各地宗教習俗有多差異,在鬼魂這個話題上,人類彷彿早已達成共識。鬧鬼是人們不能直視、或不敢直視;既是無法看透、又不可理解的現象。面對靈異現象,人們只能用空洞的儀式咒語驅鬼。之所以說《返校》的編導是「彷彿」想記憶獲得安息,因為在驅魔儀式背後,有一項決定性因素,反映出製作人的真實動機。
西谷啟治在《宗教是甚麼》(宗教とは何か,Religion and Nothingness)一書,借鑑其師海德格之存在論,嘗試剖析宗教信仰得以確立的根基。儘管作者沒明確作出以下分類,讀者尚可遵循整套論述的思路,把西谷先生列舉的例子——日本神道教、基督教和佛教——劃分為「原始宗教」及「現代宗教」。神道教(包括薩滿教色彩濃厚的各地民間習俗)歸作原始宗教;基督教和佛教則為現代宗教。箇中差別,在於現代宗教經過歷史的推演,信仰經過知性的理論化,信徒自覺地處理「自我」與存在論之關係,亦即我思主體或其他現代的主體觀之問題。是故,若用絕對觀念論的術語,稱之為「自在的宗教」與「自為的宗教」也不為過。無論如何,不管諸般宗教之差異多大,西谷啟治認為它們有特殊的啟示作用,不論是死亡/虛無、上帝的無我心、根本惡或業力等,都是一個契機,幫助人們脫離科學——我思主體式的思維框架,尋找真正的實在(reality)的根源。根源則包攬一切生命,它是構成我思主體、由我思出發建立的諸般對象的根基。這個純粹的眾生根基,西谷啟治應該從黑格爾的邏輯學獲取靈感,稱之為「絕對無——絕對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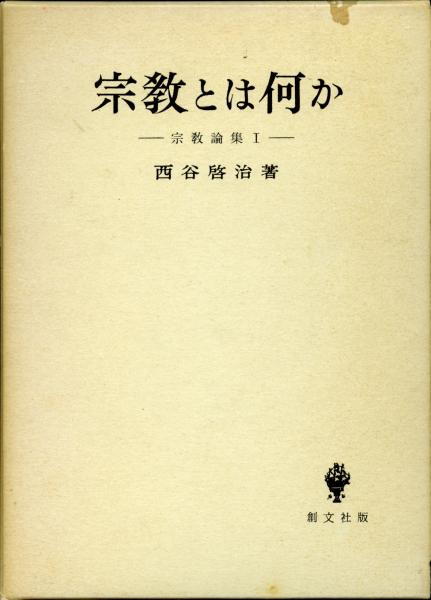
我們引鑑德希達對海德格的批評。西谷啟治犯上了老師海德格一樣的毛病;借用德希達的話,「西谷先生(原話是海德格)是最後一位形上學家」(此話源自海德格對尼采的評鑑,指他是最後一位形上學家。也許,對現代每一位哲學家來說,他們的前輩或啟發者都是「最後的形上學家」)。他們身陷在場(presence)的形上學之局限:當諸般百樣的形上學殘餘經解構詮釋過濾後,「在場」是那最後一根蘆葦。絕對者的在場,依舊是西谷啟治的預設。它脫下了上帝、神靈等名相外衣,化為包涉萬有——包括虛妄的我思主體與一切生靈——的顯在,亦即「絕對無——絕對有」,按照因果律則坐在第一因的寶座上。據此,我們應該「顛倒」它,進行一次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撕破其形上學的迷彩外衣;這個絕對的顯在,不是暗藏主體內的神秘源泉,它實質源自外部,是人與自然、社會關係的一切總和。然而,古人未有自覺,隨時間的推演此一存在論預設漸漸退化成抽象的顯在,往後補上絕對者、上帝和各種神明。
綜觀而言,西谷啟治忽略了中國民間信仰,它是一項重要的關鏈,幫助我們理解「驅靈」的問題。古往今來,人類的宗教都包含某種交易性質。這種認知已成常識:古人透過奉祀,向假託的絕對者進行交涉,試圖化解天災異象。在此,交易兩方的關係明顯是不對等的。然則,世上沒有宗教比——儒、釋、道的混合物——中國信仰習俗更具經濟特性。基本上,中國人把俗世的經濟系統,幾乎劃進神鬼境界中去。孔子說「敬鬼神而遠之」,按照中國民間傳統的解讀,此處之「敬」不同基督教義上對神之畏;毋寧說,是指「施予好處」,即俗話說的「給甜頭」。縱然在信仰中,神、鬼、精、怪與人仍有存在論意義上的等級差別,但平民卻可燒冥鈔——一種被設想成陰間流通的貨幣——來收賣神心(或鬼心)。某程度上,這映射出黎民百姓面對官宦的態度。面對人際困難時,他們往往用錢賄賂上流階級的官人達要。且外,根據中國的傳統禮節,每逢重陽和清明節,人們會帶備祭祀用的美食和冥錢,前往先人墓頭拜祭。關於以上現象,我們不必先簡單地歸因於儒學的倫理價值:孝(filial piety);祭祖有其經濟維度,後人掃墓的出發點,是盼望善待先人和祖先後,獲得對方的祝福和保佑,頗具交易上的契約精神。也許,我們不能說中國人祭祖的心態市儈、勢利,應該說中國文化有強烈的入世感,導致信仰習俗傾向世俗化;他們不追求西方柏拉圖式的形上價值,對虛空的抽象名相毫不在乎。整套扣連生命的價值觀,貼近孔子的另一名句:「未知生,焉知死。」,這句話如同中國傳統的存在論之地基。於是,孝道是建基於物質之上(補充:一切儒家追求的價值皆是),故人們以物質享受(祭祀用的美食、冥錢)來報答先人,解除記憶的執念。話說回來,多虧冥錢這項中介,生者與神鬼交易時,彷彿彼此形成了對等的關係,彷如商人進行買賣。更甚者,生者可藉此控制神靈鬼怪,獲得一定的好處。換言之,這是一種幽靈的經濟學。
由此,我們真正地瞭解《返校》的製作動機。表面上看,電影是設法驅除幽靈的嘗試,但實際上是一場招魂儀式。「自由、民主」與泰戈爾的詩,便是招魂的法術咒語。編導就像清明重陽的祭祀,希望駕馭這些鬼魅;《返校》變成一齣嚴格意義上的「改編」電影,因為要改寫歷史。但由於製作人員(包括電影的目標受眾)沒有勇氣如實觀照這段歷史、一切流於草草了事,那個時期的陰霾——未被理解為歷史的「記憶」——沒法被成功操縱,只會繼續糾纏下去。這種招魂戲法在現今相流行,人們妄想把不瞑目的幽靈充當扯線木偶,結果讓鬼魅般的記憶徘徊人間,揮之不去。
如何處理鬼魅般的記憶與歷史的關係呢?難道要將朦朧的記憶納入正史,讓幽靈化為實存(即變成「歷史——語言中心主義」認可,真實存在過的人與事)?或許,讀者從本文各處可見端倪,我們是採納反福柯主義的立場。德希達在〈我思與瘋狂史〉對福柯的批評,已是標準的教科文本。發揚惻隱之心的福柯,當他發掘被歷史掩埋的非理性聲音,嘗試譜寫一部屬於瘋狂的史書時,他身陷悖論的囹圄卻不自知。恰如德希達所言,熱心的考掘學家罔顧了語言的本質。理性的語言是消融諸般差異的熔爐,它的基本原則實為同一性,故福柯沒法藉此道出語言外域之物。事實上,按照系譜學的概念,美國現正雷厲風行的「政治正確」風潮,是福柯主義孕育出來的畸胎。上至拜登政府,下至荷里活如法炮製的「平權」電影,概言之,都是美式民主派的「語言修正」運動,目標是將表達「多元」的字詞編列主流話語之內。結果,他們重蹈福柯的覆轍,誤以為修定詞彙可如實般呈現差異,繼而達致平等,撫平社會矛盾。無奈歌舞聲平背後的蕭條持續,現實中的政治衝突依然。理由顯然易見,美式民主高舉的「包容」,不過是語言同一性的專橫;他們著重修言令措的表面功夫,漠視語言中心以外的真實社會紛爭。福柯主義者的故事教訓我們,不要浪費時間修正語言。是故,我們應以開放的態度,坦誠接納歷史與史料以外的一切蹤跡。所謂蹤跡,是顯露言外之音的印跡;並非明確的言述,而是語言自我消解、言者無法直道的否定狀態。
近年來,台灣當局陸續解禁戒嚴時期的官方資料,學界也持續搜索各地史料和總結新的史觀。史記的更迭,不僅是認識新出土史料和證據的機會,更重要是論者提供新的觀察角度,好讓我們爬櫛諸般多樣的史料;發現箇中不能消解的足跡,面對無法消腿的記憶幽靈,超渡在世者的執念。若《返校》的製作人能跳出「陰魂不散」的角度,不以招魂的手法改編歷史,轉用其他手法「擬仿」這段往事(重申:電影不能再現現實),或能鼓勵我們一改過去「不敢直視」、把昔日舊史視為恐怖冤鬼的態度,啟發人們勇敢地審視台灣戒嚴時期的歷史。
(感謝作者供稿)
發佈日期:2021/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