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美國總統大選結果即將揭曉,臺灣社會也相當關注,雖然美國的東亞與國際佈局方向不會有重大的差異,但是策略的差異仍會牽動臺灣作為棋子的角色與東亞未來的和平發展,而部分臺灣社會民眾(包括一些自認進步的人士)之所以表態支持川普,主因是川普口頭上明顯的反中策略呼應了其對中的政治情感,而非川普代表的政治價值,相對地不支持川普與美國者,往往就被簡化為對立面,被扣上了「不愛臺灣」、「膠」等等標籤。臺灣社會因其歷史與地緣因素而有的親美反中政治情感及意識型態,很大地影響了自身如何理解美國的國際角色,並將此投射在美國的政治人物上。然而,當代國際體係正處於深刻的演變過程之中,而臺灣的角色也深刻受到牽動,臺灣是否有有別於依附美國的冷戰式理解呢?又如何理解國際體系轉變下,美國的霸權將迎來什麼樣的命運?大國之間的協調體係是否可能?各國發生針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抗是否可以除舊立新?本文透過理解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思想,重新探索這些問題。本文發表於《國外理論動態》2019年第12期,本文轉載自6月27日保馬。
當代國際體係正處於深刻的演變過程之中。在全球各地都有許多人以焦慮的目光注視著國際舞台的風雲變幻。三個問題成為討論的焦點:美國霸權將迎來什麼樣的命運?一種大國之間的協調體係是否可能?諸多國家發生的針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抗是否具有創造新秩序的可能性?
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對這些問題有著自己獨到的見解。安德森長期從事歷史社會學與思想史研究,其著作《絕對主義國家的譜系》一直以來被廣泛承認為歷史社會學領域的學術經典。近年,安德森將研究的重點轉向了國際體系,出版了《新的舊世界》(The New Old World,2009)、《美國外交政策及其智囊》(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Its Thinkers,2014)、《原霸:霸權的逆變》(The H-Word: The Peripeteia of Hegemony,2017)這三部重磅作品[1],並長期堅持在《倫敦書評》(London Review of Books)上撰寫國際觀察。2016年10月,他曾經訪問北京大學,其演講和相關訪談也集結為《大國協調及其反抗者》一書於2018年出版。[2]在這些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國際秩序的總體判斷:美國霸權正在衰落之中,然而在主要大國之間很難建立一種新的「大國協調」機制,以填補權力真空;新自由主義仍在全球範圍內居於強勢,針對新自由主義壓迫的反抗力量總體上仍居於弱勢地位,但歐洲目前是新自由主義世界體系的薄弱環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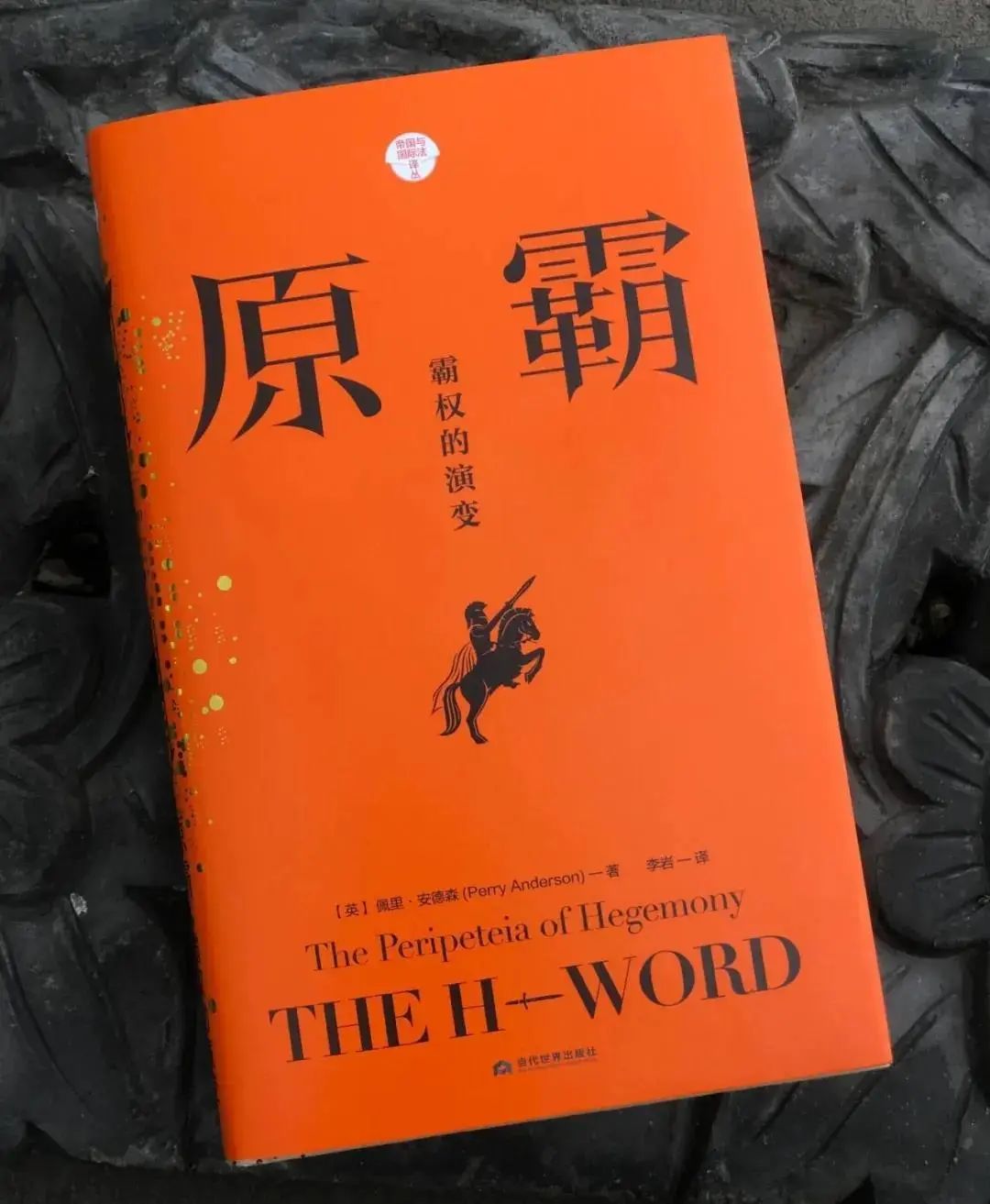
不過,安德森提供的遠不僅是判斷。所有這些看法都有著深入的歷史研究和當代研究作為支撐。長期以來,他一直深入分析當代資本主義的壓迫性結構,並思考不同類型的反抗運動突破這一結構的薄弱環節的可能性。近年來,他的思考延續了其一貫的理論原理和風格,不僅在空間上覆蓋更多的國家與傳統,在原理上,也深化了安東尼.葛蘭西(Antonio Gramsci)以來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對於「霸權」的思考。為了更為立體地呈現安德森的思考,本文將從安德森對於「霸權」的原理性思考開始,進而探討其對原理的運用。
一、「霸權」/「領導權」思想的源流
與歐美國際關係學界的主流學者相比,長期從事思想史研究的安德森對於學者們所使用的概念工具本身俱有更加深刻的反思意識。在《原霸:霸權的逆變》一書中,安德森聚焦於「霸權」/「領導權」 (hegemony)一詞,探討來自不同時代和不同政治共同體的作者如何出於不同的目的在使用該詞。正如其指出的那樣:「從一開始,在該概念的各種潛在含義之間便存在著張力。聯盟中的領導地位是政治上的,還是軍事上的?被領導的是臣民,還是盟友?其關係是自願的,還是被迫的?’霸權’隨後披上的每一件外衣都籠罩著這樣的模棱兩可性,儘管其使用者常常——並非總是——試圖將其消除。」[3]基於對這些問題的探討,安德森描繪出一個豐富多彩的理論光譜。對於今天在寫作中使用到「hegemony」一詞的各國學者而言,該書不僅提供了有史以來最全的關於「hegemony」的理論類型總結,更包含了安德森對於這些不同理論的回應。
安德森將「hegemony」的源頭追溯到希羅多德在其《歷史》中使用的「hēgemonia」這個抽象名詞,後者用來指代為了某個共同軍事目標而結成的城邦國家聯盟的領導權。希羅多德將斯巴達視為反對波斯的聯盟中的「hēgemonia」的承擔者。因此,「hēgemonia」在誕生之時指稱的是一種「邦際」或「國家間」 (inter-state)的權力關係。這一詞語與古希臘語中的「帝國」 (arche)概念經常能夠互換——安德森強調這一點,因為後續有許多理論家致力於對「霸權」與「帝國」進行語義上的區分。
「hēgemonia」這一詞語在古希臘之後長期處於休眠狀態,直至19世紀中葉才在德意志地區首度出現於非古籍的語境中。當時,醉心於古代希臘史的德意志歷史學家們將普魯士王國視為德意志聯盟之中「hēgemonia」的承擔者,期待普魯士領導聯盟完成德意志統一大業。這一用法與古希臘的用法大體上保持一致,都是在「國家間」這一層面展開。但在19、20世紀之交沙俄革命運動內部的辯論之中,俄國的革命思想者們用「gegemonia」來界定國家之內的政治關係,用其來指稱俄國工人階級在反對沙皇的鬥爭中對所有受壓迫階級所實施的領導權。由於軟弱的俄國資產階級無力領導完成反對沙皇絕對主義的革命,工人階級承擔起反對沙皇絕對主義的階級聯盟的領導地位,推動著一場從本質上屬於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從古希臘到19世紀的德意志再到世紀之交的俄國,無論是在國家間還是國內層面,「霸權」或「領導權」都基於某種聯盟關係,領導者通過共同的事業來凝聚聯盟成員,並獲取他們對於領導地位的同意。
但西歐不同於俄國,歷史上並不是工人階級領導各階級推翻絕對主義統治,強大的資產階級領導了反對絕對主義的革命,並在革命成功後對工人階級和其他階級實施統治。針對這樣的歷史語境,葛蘭西的《獄中札記》極大地豐富了「霸權」/「領導權」的理論傳統。與俄國革命者的用法類似,葛蘭西的用法也側重於國內政治關係,但所指的並不是工人階級在一個共同事業中對其他同盟階級的領導,而是任何社會階級的穩定統治——這種統治結合了強制(coercion)和同意(consent或者persuasion) ,使得被統治者臣服於對自己不利的某種秩序。葛蘭西使用這一術語來分析加富爾領導的皮埃蒙特溫和黨(Moderati per il Piemonte)在19世紀的意大利統一進程中所發揮的領導作用以及這一政治集團的後繼者對意大利所實施的統治。與俄國的用法不同的是,葛蘭西強調了「霸權」/「領導權」的「強制」的維度;但為了理解工人階級革命的任務,他重點分析了資本集團如何對大眾進行意識形態控制,使後者從形式上「自願」地接受前者的統治。而這意味著,革命者必須在掌權之前就與這種意識形態控製作鬥爭,贏得大眾的支持;在掌權之後,同樣需要實施對於大眾的「領導權」。
但安德森指出,葛蘭西對於「霸權」的用法經常表現出不穩定。在討論意大利國內的階級關係時,葛蘭西經常不經意地抹去了其強制的維度,而聚焦於其同意的維度。安德森在1976年發表的〈安東尼.葛蘭西的二律背反〉(“The Antinomies of Antonio Gramsci”)一文中對這種不穩定性做過初步剖析,該文後來修訂成書,在2017年出版。[4]在葛蘭西之後,德國法學家海因里希.特里佩爾(Heinrich Triepel)在1938年出版的《霸權:論領導型國家》(Die Hegemonie: Ein Buch von führenden Staaten)一書中也表現出了類似的不穩定跡象。在特里佩爾看來,霸權即「一種格外強大的影響力」;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介於「支配」(Herrschaft)與「影響」(Einfluss)之間的一種權力,它同時在國家間和國內政治關係中存在。特里佩爾寫作此書,意在為「霸權」概念洗刷掉動用強制的嫌疑,從而為德國的擴張進行正當性論證。但在討論德國歷史的時候,特里佩爾又不得不承認霸權與支配之間的界限有時的確是模糊的,從而將強制引回到其霸權概念的用法之中。安德森指出,特里佩爾主要討論的是國家之間的關係,而在這個層面,「強制」與「同意」的結合實現起來就要困難得多。而在真實的歷史過程中,從普法戰爭到《凡爾賽和約》,歐洲各國不斷使用一個以「強制」為核心的「霸權」概念來討論德國所帶來的威脅。在一戰打敗德國之後,協約國無意將業已帶上強烈「強制」意涵的「霸權」用到自己頭上,儘管有人論證,英美行使了一種主要基於「同意」而非「強制」的「霸權」。
接下來的討論主題是二戰之後「霸權」/「領導權」概念的發展。安德森探討了路德維希.德約(Ludwig Dehio)與魯道夫.施塔德爾曼(Rudolf Stadelmann)對於歐洲均勢與霸權關係的辯論,兩位理論家對於海上強權和陸上強權中何者可以被稱為霸權有著不同的看法,但最終都呼籲美國與歐洲聯手遏制蘇聯共產主義。漢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與雷蒙.阿隆(Raymond Aron)這兩位重要的國際秩序理論家也站在美國一方,「霸權」一詞在其文字中並不佔據中心地位,其意義也可以根據具體目標而不斷調整。
1973年左右,美國面臨的衰落危險使得「霸權」在美國的政治與理論爭論中再次成為關鍵詞,而跨國(trans-national)這一層面在「霸權」的討論中出現。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Keohane)和約瑟夫.奈(Joseph Nye)等新生代理論家倡導擺脫以國家為中心的範式,轉而關注各種非政府組織及關係的互動,而這引起了其他理論家的批評。在美國理論界內部進行辯論的時候,葛蘭西的思想遺產繼續在全世界傳播。但意大利共產黨急功近利地利用葛蘭西的思想來服務於不斷變化的各種目標,極大地損耗了這筆思想遺產在意大利本土的活力。反而是英國的左翼知識分子運用葛蘭西的理論對本國的社會及政治態勢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分析,從而激發了葛蘭西思想遺產的活力,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斯圖爾特.霍爾(Stuart Hall)與湯姆.奈恩(Tom Nairn)是這些左翼知識分子中的傑出代表。
葛蘭西也影響了來自阿根廷的厄尼斯特.拉克勞(Ernesto Laclau)與來自比利時的尚塔爾.墨菲(Chantal Mouffe)。兩位作者拋棄了葛蘭西關於無產階級是「根本階級」的觀點,認為當下的目標不應是社會主義,而應該是「激進的民主」,社會主義不過是「激進民主」的一個方面。拉克勞的《論民粹主義理性》(On Populist Reason)設想的是這樣的反抗:不同群體的民眾通過一系列共同符號以及對某位領袖的共同情感凝聚起來,打出「人民」的旗號,與壓迫他們的「精英」對峙。由於無產階級不再被視為「根本階級」,反抗者及其對立面的範圍都具有了很大的偶然性,取決於政治動員的具體過程。拉克勞與墨菲對「激進民主」和「民粹主義」的推崇已經影響了當代世界的諸多民粹主義運動。比如說,打出「99% vs.1%」旗號的「佔領華爾街」運動就是符合兩位作者設想的「激進民主」或「民粹主義」的運動。然而,安德森批評說,民粹主義運動最大的缺陷就在於,它無法,也不願意講清楚「人民」以及與之對立的「精英」的具體構成,它使用的核心概念必然是模糊的,因為如果一旦太確切地或現實地分析對立陣營的具體構成,就會暴露出「99% vs.1%」這一夸張的百分比實際上是一種虛構。
印度底層研究(Subaltern Studies)創始人拉納吉特.古哈(Ranajit Guha)則將葛蘭西的理論與對印度的分析結合起來。《無霸權的支配》(Dominance without Hegemony)將「領導權」/「霸權」界定為「說服」份量超過「強制」份量的支配形式。古哈指出,在英國對印度的統治中,「強制」相對於「說服」具有壓倒性的地位,因而是一種「無霸權的支配」;但反抗這種權力的民族主義運動同樣也處於「霸權赤字」的狀態——這反映出古哈對於國大黨尖銳的批判態度。安德森積極評價古哈的分析,但同時也指出其低估了印度選舉政治對於建構被統治者的「同意」的意義。喬瓦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讀過古哈的作品並加以引用。阿瑞吉將霸權的國家間維度和國內維度融合到單一框架之內。和葛蘭西一樣,阿瑞吉也認為霸權兼具強制和同意。但與同時代人不同的是,阿瑞吉認為霸權獲取同意的關鍵不在於意識形態,而在於提供更高級的組織、生產和消費模式,為國際體系製定遊戲規則,消除對該體系的共同威脅,給各國統治集團帶來利益。換句話說,霸權需要提供「公共產品」,促使自己領導的這一國際體系釋放出比上個國際體系更大的生產力水平,如此,霸權的理念和價值觀才有可能獲得普遍的支持與順從。然而,安德森批判道,阿瑞吉將葛蘭西的分析運用到國家間層面,沒有看到在這個層面,強制始終是更突出的一面。阿瑞吉看到美國在國際上越來越頻繁地訴諸武力,於是將這一現象視為美國霸權消退的信號,但縱觀美國的霸權史,這其實不過是一種常規操作,並沒有特別新奇之處。[5]
而更晚近的加拿大人羅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與來自英國的理查德.索爾(Richard Saull)繼續從「跨國」的層面探討了全球性霸權的構成,並探討美國霸權的未來走向。但安德森批評說, 「跨國」維度的霸權分析往往會導致另兩個維度(國內與國家間)的輪廓顯得含混不清,就彷佛是「跨國」維度將「國內」與「國家間」都包含在內,使得後兩個層面的強制性權力特徵變得模糊不清。安德森認為,汪暉的「去政治化的政治」論述同時涉及三個層面的聯動,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上述學者的問題。但對汪暉在論述霸權的「跨國」維度的結構時重點突出消費領域,安德森持保留意見,認為更應該關註生產領域。[6]
最後,安德森梳理了美國霸權的辯護者們對霸權的論述。一些美國理論家避免使用「霸權」一詞,稱美國為居於領導地位的國家;另外一些理論家認為,美國是「友善的」、為「國際社會」所需的霸權,並將「霸權」與「帝國主義」相區分;還有一些理論家從正面定義「帝國」,稱美國為「帝國」,同時避免使用「霸權」一詞。關於「霸權」的討論也在歐洲一體化的語境下出現,核心的問題是德國是否可以被界定為歐盟中的霸權力量。這些討論呈現出「霸權」概念如何從「聯邦中基於共識的領導地位」滑向「居於其他勢力之上的強制性支配地位」,最後歸於「帝國的天然兄弟」,三種界定方式之間存在著強烈的連續性。安德森最後又回到了美國的理論家,引用了現實主義理論家對於美國過度擴張帶來的災難性後果的警示。
東亞的讀者有可能對該書第九章中關於中日兩國「霸」、「霸道」、「霸權」的思想的探討表現出濃厚興趣。安德森認為,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對「強制」與「說服」的區分比西方更早、更敏銳,也更系統。只不過由於古代中國的強大,「王」「霸」之分主要被用於中國內部的政治關係,要等到近代帝國主義入侵之後,才被系統地用於描述國家間的關係。相比之下,日本江戶時期天后與幕府之間的二元結構使得日本儒家對於「王」「霸」之分的使用呈現出了比中國更為豐富的形態。明治維新之後,「王道」在日本的最終意識形態樣式是跟日本的「亞洲主義」關聯在一起的:以領導亞洲各國反抗白人帝國主義的名義,服務於日本在亞洲的擴張。
這一系列述評終結於若干概括性的結論: (1)在經典意義上,「霸權」/「領導權」永遠暗示著比純粹強制更多的某物;(2)「霸權」/「領導權」在「國家間」這一層面通常更強調「強制」而非「同意」;而在國內政治層面,有可能出現其「強制」與「說服」之間的某種平衡,而在跨國層面, 「說服」的特徵更為突出;(3)迄今為止,霸權在「跨國」層面所呈現的特徵仍然是被探討最少的,「跨國」層面與另外兩個層面聯繫的方式仍存在諸多晦暗不明之處;(4)隨著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推進,三個層面之間的聯繫越發緊密。[7]
二、美國霸權與「大國協調」
安德森對「霸權」語義的溯源式研究與其對美國霸權的探討相互支持。在《美國外交政策及其智囊》以及若干其他評論中,安德森探討了美國霸權的興起與演變過程,尤其探討了這樣一種可能性:在21世紀,美國霸權是否有可能轉化為一種通過「大國協調」機制來實施的霸權?
冷戰結束後,美國確立了單極霸權地位。1991年美國經濟的衰退將民主黨人克林頓送入白宮。克林頓以美國的單極霸權地位為依托,致力於推動全球自由貿易體系的建設,促成了《北美自由貿易協議》的簽訂,將關貿總協定發展為世界貿易組織(WTO)。安德森指出,這其實是一種新的霸權實踐。在冷戰「鐵幕」落下後的20多年裡,美國為了回應社會主義陣營的挑戰,並不限制資本主義陣營中其他國家發展經濟的方式;1970年代美國在冷戰格局中處於守勢,當經合組織內部其他國家的經濟威脅到美國經濟優勢的時候,美國有可能會作出反擊,但仍然不會要求對方採取美國製定的經濟發展方式;但是,冷戰之後,美國羽翼豐滿,開始向全球輸出美國的經濟信條,推廣新自由主義的貿易與投資規則。與此同時,克林頓政府繼續推進北約東擴,將其推進到俄羅斯的家門口。而通過介入南聯盟戰爭,美國霸權在兩個方面推進了創新:一是促使聯合國安理會將軍事行動外包給北約;二是以「人權高於主權」的名義,將對南聯盟的空襲宣佈為「人道主義干涉」。1999年對伊拉克的空襲增添了「未經宣布的常規戰爭」這一霸權武器。小布什在克林頓之後當政八年。在9.11事件後,小布什宣稱美國有權發動先發製人的戰爭,進而發動了阿富汗戰爭與伊拉克戰爭。小布什看起來比其前任更具有侵略性,但在大多數方面,他不過是在延續其前任的政策。[8]
2009年,一位非洲裔民主黨總統入主白宮,曾經引發許多人的幻想。但奧巴馬並沒有改變美利堅的帝國政策。戰爭仍然繼續進行,只是在話語上作了一些調整,如將「反恐戰爭」重新命名為「海外緊急行動」,將對利比亞的導彈襲擊包裝為「有活力的軍事行動」,並且加強了保密工作。奧巴馬與小布什一樣,都認為美國有權發動「先發製人」的戰爭。「阿拉伯之春」在中東的爆發並沒有削弱美帝國在該區域的地位,而只是削弱了一系列世俗共和國,加強了該地區那些與美國結盟的君主專制國家的力量。歐盟在「阿拉伯之春」中也表現出與奧巴馬政府的合作態度。奧巴馬在第二個任期比之前更重視貿易問題,白宮試圖與歐盟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打造一個「經濟北約」;針對日本,奧巴馬政府將不馴服的日本民主黨的鳩山政府趕下台,並試圖通過《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談判,獲得更大的對日經濟優勢。奧巴馬政府宣布「回歸亞洲」,試圖用一系列美國盟友和軍事設施包圍中國,迫使中國對美國表示順從。奧巴馬進一步擴大了總統的權力,與小布什相比,更工於成本算計,會在軍事與外交中盡可能爭取值得信賴的盟國的參與,並儘可能減少美軍的傷亡。[9]
迄今為止,一切看起來盡在掌握之中。然而,美國大力推進的自由資本主義秩序已經開始背離其設計師的意圖。全球性的放鬆管制給美國資本帶來了巨額利潤,但也給美國帶來了許多消極後果,美國貿易赤字不斷增長,為了彌補財政赤字需要的借貸不斷增長,中國逐步崛起,成為美國最大的債權國。美國的理想當然是將自身的霸權地位與資本的普遍利益結合在一起,然而,資本的流動脫離了美國的控制,實際上有助於國際體系中的其他國家縮小與美國的力量差距,從而削弱美國的支配地位。美國在後冷戰時期大張旗鼓宣傳的普遍性理想已經成為美國「不可承擔之重」。[10]
在安德森看來,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美帝國的理論家們已經減少了對「輸出民主」的熱情,致力於捍衛美國的帝國基業,尤其是消除中國與俄國等國家對美國的潛在挑戰。一種可能的替代方案就是建構一個「大國協調」(concert of great powers)體系,將世界上的重要大國拉入一個俱樂部,共同承擔維護新自由主義體系的責任,並保持美國在這個俱樂部中的霸權地位。這種可能性會變成現實嗎2016年10月安德森在北京大學的系列演講中系統討論了這種可能性,給出了否定的答案。
為了說明何謂「大國協調」,安德森從19世紀的大國協調機制開始說起。大國協調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大國均勢(balance of powers)。事實上,實現客觀的均勢經常需要一個國家對其他國家發動「先發製人」的戰爭,但協調則包含了避免戰爭的主觀努力。1815年歐洲君主聯盟打敗拿破崙之後,為了保衛其成果,通過維也納和會形成了五大君主國俄、普、奧、英、法所組成的「五霸共治」 (Pentarchy)的國際體系。五霸各自的社會和政治結構不盡相同,地位也不平等,英俄處於歐洲的兩端,分別扮演著海上霸權與陸上霸權的角色。「大國協調」之所以可能,首先得益於君主們對共同威脅的明確共識:他們擔心再出現一次法國大革命或一個拿破崙,因此需要通過相互之間的協調,將各自國家的革命苗頭消滅在萌芽狀態,同時通過國家間協調來控制彼此的衝突規模,防止這種衝突給潛在的革命帶來可乘之機。為了實現這一目的,奧、普、英、俄四霸與戰敗國法國和解,將其納入「五霸共治」結構。
在克里米亞戰爭爆發之前,該協調體系成功地抑制了意大利南部、希臘、西班牙、比利時爆發的革命,以及影響整個歐洲的1848年革命。在鎮壓革命的同時,大國協調機制使得歐洲內部直到一戰之前都沒有發生大規模、長時段的戰爭,這一時期有時也被稱為「百年和平」時期。然而,這一體係為何會走向崩潰呢?安德森指出兩點:第一,地跨歐亞的奧斯曼帝國被協調體系排除在外,在奧斯曼帝國衰落後,歐洲列強紛紛進入這一地區以填補權力真空,形成激烈的爭奪之勢,這一邊緣地帶成為歐洲協調體系的缺口;第二,1871年普魯士統一德國,此後,乘著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東風,德國迅速崛起為歐洲第一大工業國,這就破壞了歐洲內部的均衡格局,英、法、俄逐步走到一起,以牽制德國,五霸分裂成兩個對立的陣營。最終,一戰的爆發使得維也納體系的大國協調走向徹底失敗。[11]
那麼,21世紀的大國協調有可能嗎?從表面上看,這樣的期待或許不無道理,如今的世界既有各大國之間的定期會議、有聯合國以及形形色色的國際組織,在意識形態上, 「人權」話語已經替代了19世紀的「文明標準」成為大國干涉他國內政的藉口。美國、歐盟、俄羅斯、印度和中國五個政治體,是最有可能組成新的「五霸共治」的人選。但五霸有可能出於何種目的進行協調呢?安德森分析指出,目前具有全球性影響的議題有兩個,一個是團結起來抵禦經濟失調,防范金融危機;另一個是生態環境災難。這些都有可能為「大國協調」提供基礎。如果說在維也納體系中英、俄「共霸」,那麼冷戰後美國是名副其實的唯一霸主。基於所有這些條件,新世紀的「大國協調」看起來就像是水到渠成了。
然而,安德森指出,美國卻恰恰成為實現21世紀「五霸共治」 的最大障礙,原因如下。第一,美國不能像維也納會議四強對待法國一樣寬待冷戰的失敗者俄羅斯,相反,美國夥同它的盟友不斷欺騙、羞辱和傷害俄羅斯,從而使得兩國之間的矛盾積重難返。安德森在2016年發表的這一評論在接下來的三年裡不斷獲得新的證據的支持:特朗普試圖改善與俄國的關係、從而分化中俄兩國的努力,卻遭到了美國建制派勢力發動的「通俄門」的嚇阻,目前,我們看不到美俄關係發生實質性改變的跡象。第二,美國從未放棄過「演變」和顛覆中國政治社會體制的努力,而且中國始終非常清楚這一點,這就使得中美兩國之間的協調變得非常困難。這一點在接下來的三年之中也繼續得到新的證據的支持。在中美貿易談判中,即便特朗普首要關心的並不是中國的政治結構,美方提出的一些過分的要求仍然具有改變中國政治社會體制的潛在可能性。既然美國與中、俄兩國的協調都缺乏基礎,新世紀全球性的「大國協調」就很難成為現實。我們可以看到,2019年6月,中俄兩國結成了「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這可以說是對美國愈演愈烈的單邊主義的一種反應。在短期之內,我們看不到建立一種全球性的「大國協調」機制的可能性。
不過,這對安德森來說並不是壞事。如果一種美國領導之下的「大國協調」機制真正成型,那也就意味著新自由主義秩序更加鞏固,更加難以撼動。[12]如果說19世紀王朝國家之間的協調壓抑了工人運動與民族獨立運動,21世紀大國協調難以形成,恰恰給反對新自由主義的力量提供了尋求替代秩序的機會。
三、反抗者的坐標和處境
在分析當代世界的支配結構之後,我們可以將視線轉向針對這一支配結構的反抗勢力。安德森密切追踪著對新自由主義形成衝擊的歐美民粹主義運動與相應的政黨。但從總體上看,他對這些民粹主義勢力創造新的秩序的可能性並不抱樂觀態度。
安德森在2016年10月訪問北京和上海期間,系統地討論了針對新自由主義的民粹主義反抗。[13]他指出,當下的民粹主義反對的是新自由主義這一特定的資本主義類型,並不是從根本上反對資本主義。民粹主義在話語上建構出一個籠統的「人民」與建制派「精英」的對立,概念上具有極大的模糊性,無論左右都可以通過「人民」話語對中下層民眾進行政治動員。在美國,右翼民粹主義有茶黨和特朗普主義,左翼民粹主義有「佔領華爾街」運動——它打出了「我們是99%」的旗幟,要對付1%既得利益者,後又有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競選攻勢。在歐洲,右翼民粹勢力有法國的國民陣線、德國的選擇黨(AfD)、英國的獨立黨、意大利的北方聯盟黨;左翼民粹勢力有西班牙的「我們能」黨(Podemos)、愛爾蘭的新芬黨、希臘的激進左翼聯盟黨,等等。左翼與右翼的主張還可能會出現某些混合,比如意大利的「五星運動」既有右翼的一面,也有左翼的一面,但安德森認為,其左的一面占主導地位。總體而言,在歐洲各國,右翼民粹運動的勢頭蓋過左翼民粹勢力。移民問題是刺激右翼民粹主義興起的因素之一,但相比於經濟問題,它仍舊是一個次要的問題。更普遍的擔心是既有的經濟全球化路徑使得民眾對於自己的生活失去控制,境況日益惡化。
安德森不主張對民粹主義運動持完全消極否定的態度,因為它可以對新自由主義起到一種衝擊作用,從而為更有生命力的政治主張開路。然而,民粹主義的弱點是明顯的。它用一個模糊的「人民」的概念將訴求不同的群體聯合起來,但它甚至無法清晰地描繪出要打擊的敵人的面目。民粹主義只談「人民」,因為害怕談「階級」會導致分裂。上文介紹的安德森的著作《原霸:霸權的逆變》在評論拉克勞時,就已經批評後者放棄了對於具體的經濟社會條件的細緻分析和對不同社會集團和人群的考察,而只是強調主觀的動員過程起到的作用。在2016年的訪華講演中,安德森進一步指出:民粹主義話語不是馬克思主義話語,是不可能做出類似於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的社會分析的。[14]
因為民粹主義的這種先天不足,它只是反抗的開始,但不能真正提供對於新自由主義的替代方案。安德森指出,新自由主義與民粹主義確實是在對峙,但二者的地位並不對等:新自由主義攻城略地,處於支配地位,而民粹主義只是一種從屬性的針對它的反叛。在今天的全球體系中,力量對比仍然有利於新自由主義。比如說,歐盟與美國的大部分人都厭惡現狀,但卻又通過選舉一次又一次接受和承認了現狀,原因在於既有的經濟秩序綁架了大多數人,人們恐懼如果政府採取非新自由主義的路線,經濟就有可能崩盤,給多數人帶來直接的損害。
在2016年底特朗普贏得美國大選之後,安德森迅速作出研判:這是右翼民粹主義的勝利,對於既有的新自由主義秩序有一定的衝擊。特朗普在競選時期批評北約、攻擊歐盟、指責世貿組織、主張與俄羅斯修好、譴責美國在中東的戰爭、譴責中國「操縱貨幣」,等等,幾乎是在美國掀起一場「外交革命」。然而,安德森指出,一旦特朗普上台,就會遭遇華盛頓建制派的馴化,回歸到經營美帝國的老路上去。不出所料,特朗普上台後,迅速譴責俄羅斯、稱頌北約,在敘利亞、阿富汗扔炸彈,威脅進攻朝鮮,回歸了奧巴馬與小布什的老路,只是「更加不按常理出牌,更加感情用事罷了」[15]。安德森預測,特朗普與前任們最大的差異會出現在貿易政策方面,他試圖迫使中國在貿易上作出讓步,討好美國國內關心失業議題甚於一切外交議題的大眾選民。[16]
特朗普的當選表明,美帝國的基礎在本土正在弱化。美國的少數統治精英享受了美帝國的紅利,然而大量中下層民眾並沒有獲得好處,甚至不斷為美帝國付出代價。由此造成的巨大社會不滿將特朗普送入了白宮。不過,時至今日,美國全球霸主的地位仍舊無法被任何外部勢力所撼動。這裡仍舊有一座堅固的新自由主義堡壘,這座堡壘只有從內部才能被攻破。1970年代美國民眾對於越戰的抗議就是堡壘從內部攻破的事件。類似的條件正在形成之中。
而在美國的後院拉丁美洲,21世紀初掀起的左翼政治浪潮正在消退,新自由主義的勢力是增強而不是減弱了。相比之下,在歐洲,新自由主義的支配結構要弱得多。在安德森眼中,歐盟曾經代表著比新自由主義更為進步的一種可能性,但是,今日的歐盟不斷從社會民主與經濟民主的主張退卻,甚至在一些領域表現出了比美國更大的新自由主義傾向。歐盟已經不再是一項進步的事業。但由於歐盟在政治結構上的脆弱性,當民粹主義力量起來攻擊這座堡壘的時候,它們有可能獲得比在美國更大的成果。因此,安德森認為:「歐洲相對而言仍是新自由主義秩序最薄弱的環節。」[17]然而,如果歐美的民粹主義力量要提供一種真正具有替代性的新政治秩序,就需要超越民粹主義在「人民」與「精英」之間的模糊二分,進行更為細緻和具體的政治經濟學與政治社會學分析。否則,我們可能會繼續看到連綿不絕的政治運動,但看不到一種更為進步的秩序安排。
四、餘論
在當代國際體系加速演變的背景之下,安德森對霸權與國際體系的論述可以給中國的思想者帶來極大的啟發性。他在研究霸權時,區分了「國內」、「國家間」與「跨國」三個層次,為研究當代世界的政治支配結構提供了一個全面的理論框架,而他對一系列「霸權」理論的評論,可以幫助國內學者更好地消化、吸收這些理論。比如說,阿瑞吉的理論近年來頗受國內重視,但安德森直言不諱地指出,阿瑞吉對於「國家間」這一層面的霸權的分析過度強調了這一層面的「同意」的因素,而實際上在這一層面,「強制」始終是佔據主導地位的。[18]這意味著,我們不能被種種關於「軟實力」的話語所遮蔽,輕率地將美國越來越多的單邊主義行為簡單地視為美國霸權衰落的標誌。在「國家間」這一層面,安德森更關注的是,美國施加的強制力量是否受到了真正的限制。
安德森對於「大國協調」的論述近三年來已經在國內產生了顯著影響。這一論述反思了一種想當然的「從帝國到民族國家」的單線歷史敘事,揭示出19世紀西方列強的民族國家建設與殖民帝國建設是一個同步推進的過程,殖民帝國之間的協調與鬥爭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命運。由此,它可以啟發一系列新的研究議題,比如,「大國協調」如何塑造包括八國聯軍侵華、辛亥革命在內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國近代文化—政治精英如何理解維也納體系中的「大國協調」的走向,並對其作出回應?「大國協調」的破裂為中國的自我解放提供了何種機遇和條件?而從中國的近代命運與「大國協調」之間的關係出發,又有可能為反思卡爾.施米特等歐洲中心主義色彩濃厚的理論家的國際秩序論述提供有效的切入點。[19]
最後,安德森對於「民粹主義」的思考亦深具啟發性。「民粹主義」是國內理論界近兩年來非常關注的議題,安德森的論述告訴我們,究竟是從新自由主義立場,還是從批判新自由主義的立場來看待「民粹主義」,結果是非常不同的。新自由主義將「民粹主義」視為一種擾亂秩序、必須加以抑制的力量;但如果新自由主義秩序本身並不具備進步意義,「民粹主義」對新自由主義的衝擊可以在堅固的城牆上打開一個缺口。只是,「民粹主義」在「人民」與「精英」之間的二分過於模糊,缺乏精準的社會集團分析。它必須增加政治與社會分析的精確度,才有可能帶來一種更為進步的政治秩序。因此,「民粹主義」的情懷有可能將一部分民眾聚集到進步政治的旗幟下,但進步政治要繼續前進,離不開超越「民粹主義」的理論武器。而這就凸顯出了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政治經濟分析方法的重要性。
發佈日期:2020/11/04
註腳:
[1] Perry Anderson, The New Old World, London: Verso, 2009。其中譯本為佩里.安德森《新的舊世界》,高福進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Perry Anders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Its Thinkers, London: Verso, 2014。其中譯本為佩里.安德森《美國外交政策及其智囊》,李岩譯,金城出版社2017年版;Perry Anderson, The H-Word: The Peripeteia of Hegemony, London: Verso, 2017。本書中譯本至今尚未出版,本文對相關引文的翻譯參照了李岩先生的譯文,在此說明並表示感謝。
[2] 章永樂、魏磊傑主編《大國協調及其反抗者:佩里.安德森訪華講演錄》,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
[3] Perry Anderson, The H-Word: The Peripeteia of Hegemony, p.180.
[4] Perry Anderson, “The Antinomies of Antonio Gramsci,” New Left Review, No.100,1976; Perry Anderson, The Antinomies of Antonio Gramsci, London: Verso, 2017.
[5] Perry Anderson, The H-Word:The Peripeteia of Hegemony, pp.115-116.
[6] Ibid., pp.150-152.
[7] Ibid.,pp.180-183.
[8] 佩里.安德森《美國外交政策及其智囊》,第93-108頁。
[9] 同上書,第109-123頁。
[10] 同上書,第124-125頁。
[11] 章永樂、魏磊傑主編:《大國協調及其反抗者:佩里·安德森訪華講演錄》,第1-20頁。
[12] 同上書,第44-45頁。
[13] 同上書,第107-113,166-173頁。
[14] 同上書,第108頁。
[15] 同上書,第188-189頁。
[16] 同上。
[17] 同上書,第190-191頁。
[18] Perry Anderson, The H-Word: The Peripeteia of Hegemony, pp. 115-116.
[19] 近三年國內探討「大國協調」的代表性論述有章永樂《萬國競爭:康有為與維也納體系的衰變》,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章永樂《「大國協調」與「大妥協」:條約網絡、銀行團與辛亥革命的路徑》,載《學術月刊》2018年第10期;章永樂《卡爾.施米特論國際聯盟與歐洲秩序的敗壞》,載《開放時代》2019年第3期;孫璐璐、章永樂《從波蘭問題反思卡爾.施米特的歐洲國際秩序論述》,載《歐洲研究》2019年第2期,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