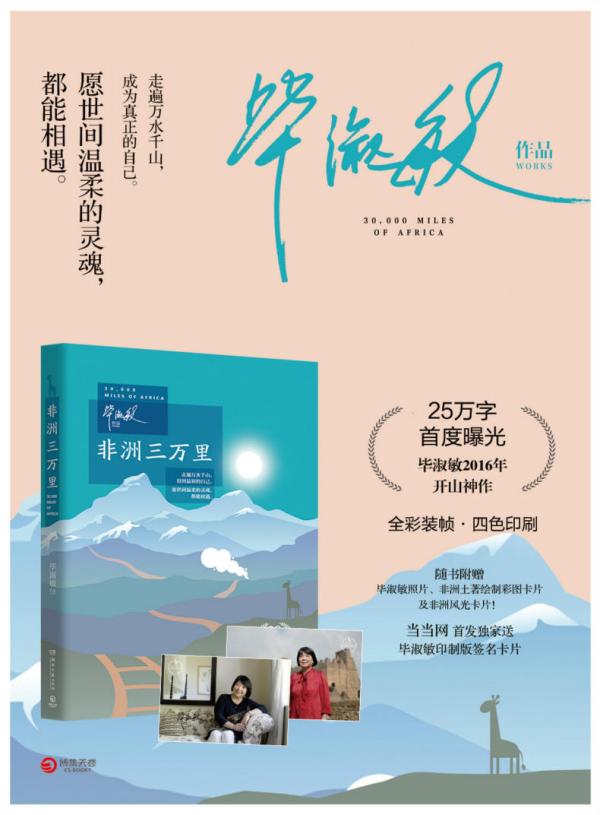今日中國的非洲:初步觀察(下)
◎王智明(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本文原載於《人間思想》第十期「思想第三世界」專號與《熱風學術網刊》2019年冬季號,感謝作者授權,圖為《新國際》編輯所加,分(上)(下)轉載,上篇請點選:今日中國的非洲:初步觀察(上))
從發現到孤獨:中國旅行書寫裡的非洲
早先我一想到非洲,腦海中涌出的畫面大致有這麼幾幅。黑如漆墨的當地人、荒蕪的草原,無盡的沙漠,還有驚慌蹦跑的羚羊和懶散偉岸的雄獅⋯⋯哦,說不定你也是這樣想的。我們都是《動物世界》的擁趸。骨瘦如柴的百姓、鐵皮房頂的城市、愛滋病的泛濫和埃博拉的高死亡率、赤裸上身的原始部落居民和政變⋯⋯哦,你是個關心世界風雲的人,每晚都會看《新聞聯播》。
──畢淑敏,《非洲三萬里》,7
每天晚上,等在首都機場準備前往非洲的人滿坑滿谷。他們穿著自己最好的衣服,却掩蓋不了去出賣體力的事實。非洲急需建設,中國工人作為基建大軍,大量擁入非洲。然後,就像一滴水落在干涸的沙地上,飛快地沒了。
──蘆淼,《孤獨的時候,我們去非洲》,6
當然,這些高曝光度的影視產品並不代表「中國的非洲」之全貌。以上的討論也不只是為了批評中國傳媒的非洲再現陷於東方主義的框架。相反的,這僅僅構成了一個考察的起點,要求我們思考中國對於非洲的知識與想像究竟來自哪裡,又如何受到主體意識的中介?中國的非洲故事又如何反映中非關係以及中國人腦子裡的非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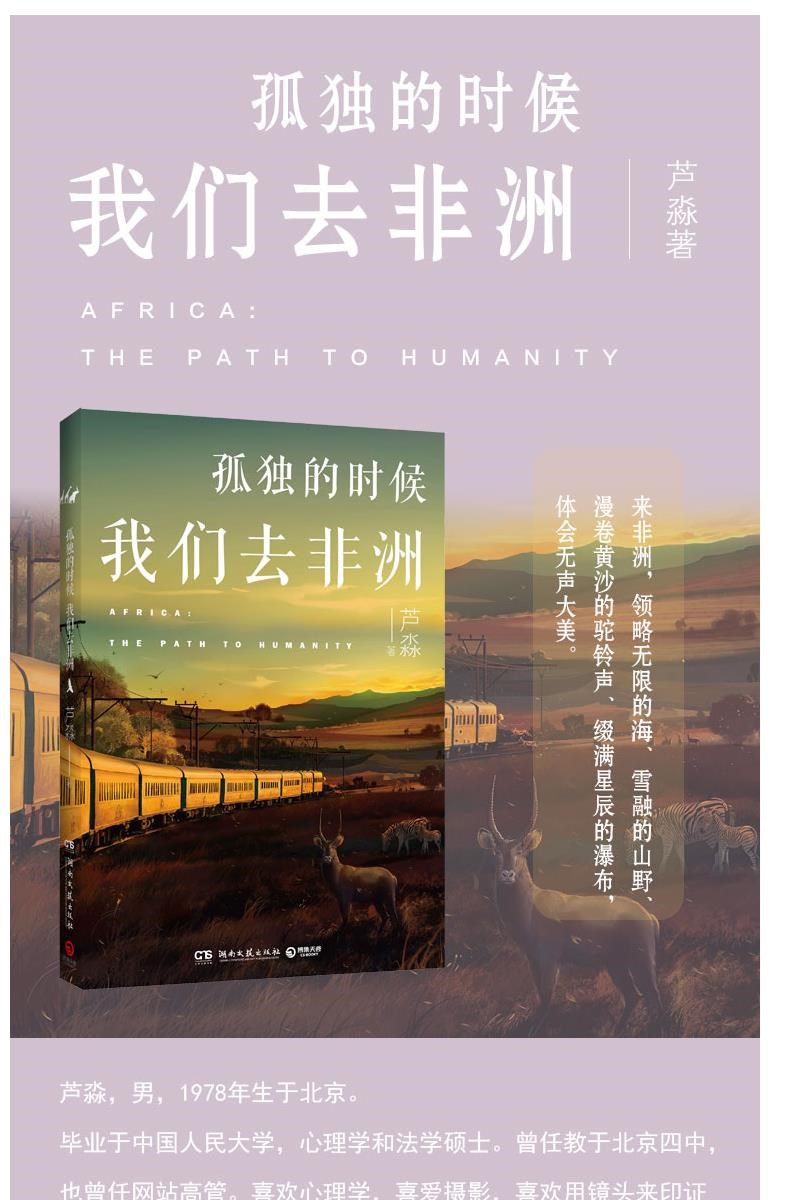
在中國崛起的數十年前,華人世界即對非洲及其他第三世界地區投以關注的眼神。台灣的三毛可能是華人世界第一個描寫非洲生活與文化,並廣受兩岸讀者歡迎的作家,儘管她的作品向來被放在「流浪文學」、「旅行文學」或「流行文學」的框架中理解。[i]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雨季不再來》、《稻草人手記》、《哭泣的駱駝》、《溫柔的夜》等書描寫的就是她在1970年代在北非西班牙屬地(西撒哈拉與加納利群島)生活的故事。[ii]雖然三毛在故事裡也寫到了北非的貧窮與戰亂,但是她筆下的非洲人物鮮少有刻板的龍套角色,而多是活生生、有思想與主張的個體,為華人世界的非洲想像提供了有溫度與深度的思想資源。然而,儘管三毛去世後並沒有被華人讀者遺忘,[iii]但我們絕少從中非關係的歷史視野中去看待她的作品,也往往忽略她在非洲寫作的1970年代,所謂的中非關係仍是一個三角關係,兩岸透過各項援助計畫正在非洲競逐國際支持。[iv]簡言之,即令三毛的作品稱不上「非洲研究」,但她浪漫行旅的非洲采風與國際背景仍然構成了當前中非關係的史前史,值得進一步的考掘。
近年來,部份由於中國崛起以及中非關係大幅進展,部份由於中國主體意識在變動中的世界裡更為增強,非洲之於中國不再是黑暗的大陸,而是遙遠的他方;非洲的意義也逐漸從政治經濟領域滲透進文化領域。近兩年陸續出現的非洲遊記或可為證。畢淑敏是中國的「一級作家」,其西藏書寫受到相當歡迎。她在2016年出版了《非洲三萬里》(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記述她在非洲行旅的經驗。她兒子蘆淼與之同行,也於同年出版了《孤獨的時候我們去非洲》(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著名的海外作家嚴歌苓也在2016年出版了《非洲手記》(北京:人民出版社),記述她陪美國外交官丈夫派駐非洲的經驗與觀察。曾在非洲的中國國企工作的八O後作家黃河清則在2017年的一月出版了《非洲歸來不必遠方》(廈門:鷺江出版社)。幾個月後,曾在尼日利亞從事農業與技術支援工作的渤文也出版一本《我在非洲的一千零一夜》(北京:團結出版社)。雖然可能有更多的作品尚未面世,我也可能錯過了一些稍早的作品,但是僅在這一兩年內的中國旅遊書寫就出現了五本關於非洲的遊記,這件事本身或許就值得思考。也許這意味著中國對非洲相關的知識有更大的興趣與渴望──至少,讀者渴望看到更多關於非洲的故事與圖片。事實上,《非洲歸來不必遠方》是這五本當中,唯一除了封面以外沒有任何圖片的一本,而在其他四本裡,圖片的重要性不亞於文字敘述本身。這些遊記的內容各有視角、觀察與體會,但是儘管經驗不同,這些作品卻意外一致地呈現了兩大主題:發現與孤獨。
「發現」這個主題不難理解,即令它本身意義複雜。如同這些作者注意到的,中國人對非洲的第一印象大都來自「發現頻道」(Discovery Channel)上的「動物世界」節目,在這裡頭非洲被呈現為一個景緻壯麗的野性大陸:睡獅、奔鹿、漫步的象群,當然還有捶胸頓足的猩猩。非洲的「發現」因而必須從超越「發現頻道」開始。然而,誠如畢淑敏的《非洲三萬里》所示,克服非洲刻板印象的第一步很快地就與非洲的現實捆綁在一起──貧窮、髒亂,甚至是混亂。事實上,對任何有意去非洲的人來說,進入非洲前要出示黃色的疫苗接種證明這件事本身,就不斷提醒自己非洲是疾病的大陸,而不要靠近貧民區、小心劫匪與個人安全等的各式警告,也在強化非洲並不安全的印象。換句話說,在「發現頻道」背後的真實非洲或許並不美麗,而且更為「野性」,因此希望超越刻板印象的企圖很快地被更為流行的刻板印象所置換。
在畢淑敏和蘆淼的作品里,「發現」同時意味著收集故事──從名為「露西」的第一個人類骨骸、南非貧民窟、火車「非洲之傲」的風情,到非洲殖民者與西方銀行家西塞爾‧羅德斯(Cecil Rhodes)的故事、波耳戰爭、曼德拉的修行與氣度,乃至一般人的故事──這些故事企圖展現一個不同於「發現頻道」的非洲,以揭示非洲社會的種族與階級動態,並且凝聚一種同情,而不是團結的觀點;非洲不只是一片廣袤無邊的大陸,而是不同個人──從殖民探險家、非洲部落到中國工人與商人──故事的集合。畢淑敏如此總結她的非洲之旅,「旅行就是聽故事。聽不同的故事,聽沒有聽到過的故事,聽他人的故事」(368);她強調,「旅行本身就是不斷踫撞記憶的過程。沒有回憶的旅程,不能算作優質的旅行」(256)。換言之,旅行一方面是收集故事(一如收集各類紀念品)的活動,同時也是製造記憶的行動──將他人的故事變成自己的記憶,在畢淑敏看來,恰恰是旅行的本質,或是說優質旅行的必要條件。隨著她所收集的故事與製造的記憶,讀者們也成為故事與記憶的收藏家;他們不只見證與發現,同時也感受,反思與記憶非洲。但是中國讀者們究竟記得非洲的什麼,他們的反思又反映了些什麼?
由於畢淑敏與蘆淼一同旅行,所以他倆的遊記分享了共同的行程,由南非入境,搭乘火車「非洲之傲」一路向北,以走上坦贊鐵路為敘事的高潮,並在坦桑尼亞的德累斯莎朗姆結束旅程。畢淑敏的記述較為細膩,對當地的風土民情、文史地理有較多的考察與介紹,並在非洲的故事當中提煉人生的智慧。相較之下,蘆淼的記述較為零碎,文字略為滑頭,書中不斷出現,用來分段的引文有時也顯得多餘而做作。儘管兩人筆下多是非洲的景物與旅途的人事,但非洲景物中的中國身影──「非洲之傲」的「綠皮火車」內核,坦贊鐵路的鐵軌與枕木,乃至中國工人和移民等──仍然是他們心頭揮之不去的念想。換句話說,這兩部遊記裡的另一個重要「發現」,其實是在非洲大陸上的「中國」。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製〉這一章裡,畢淑敏帶著讀者坐上坦贊鐵路,那是1970年代中國人民餓著肚子為贊比亞的非洲兄弟蓋的一條鐵路。藉著描述坦贊鐵路今日的狀況,畢淑敏帶讀者走進時光隧道,回憶她自己的1970年代,以及當時中國建造這條鐵路的原因。坦贊鐵路是「屬於我們那個年代的紀念」(251),畢淑敏回憶道:當時中國非常貧窮,窮到她在西藏的同志們樂於在離開部隊前割盲腸,因為割掉盲腸,每個人可以獲得兩百塊人民幣的補償。儘管窮困至斯,寧可割肉換錢,中國卻毅然決然地要為非洲兄弟蓋鐵路,只因為他們向世界銀行貸款遭拒、向蘇聯求援被否,極需要一條鐵路來推進自身經濟的發展。這是中國人民願意勒緊褲帶,全心全意幫助非洲人民的時代。但是新禧年到來後,坦贊鐵路很快地失去了昔日的光采,因為贊比亞不再需要它來運送銅礦到國外,而中非友誼的願景也慢慢在記憶中淡去。坦贊鐵路的故事是畢淑敏珍惜的回憶,因為那正是今日中國所失去的,即令它也是中非關係中一再被提及的橋段,包括2018春晚小品「同喜同樂」亦以之為背景。
同樣的,蘆淼也為坦贊鐵路寫了一段,但是他的理解卻有更多想像與虛飾的成份。他坦誠:坦贊鐵路「這詞離我實在太遠太遠。無論是從歷史還是地理上來說,都如此。我會和其他人說坦贊鐵路如何如何,這就像七月驕陽下的高中地理考試,滿嘴名詞彷彿地球就是自家後院,自己就是無所不知的秘書長,但實際上,貧瘠的大腦裡浮現的只是一行行枯燥的印刷體」(128)。即令如此,也不妨礙蘆淼對之大發思古幽情:「那種似曾相識的感覺,來自那些沈睡在此地已經40年的鐵軌、道釘和枕木。它們似乎還帶著當初修建鐵路時中國人的喘息和汗水,帶著當時的塵土和海水的味道」(131);「歷經風吹雨打,車廂已被風化腐蝕出一個個锈跡斑斑的大洞。雖然沒有漢字,但我仍然固執地認為,這些車皮,就是當年中國援助坦贊鐵路時的車皮。這個車站給我的感覺就像一個沈默的墓地,讓人壓抑」(134)。墓地的比喻具體而微地解釋了坦贊鐵路的興衰,也暗示了中非友好時代的落幕,如今非洲更為形象的中國商品已不是鐵路,而是大量傾銷的日用商品、手機,以及機場、體育館等大型硬體建設。因此,如何評價坦贊鐵路遺產的問題,就成為如何理解中非關係深層歷史的線索。然而,儘管坦贊鐵路構築了中非關係歷史上的基石,它同時也成為了一套修辭,或是用以導正中非關係發展的道路,或是用以遮掩中非關係中的實質剝削。顯然,在「發現頻道」之外,非洲的發現意味著重新發現在中非關係的發展與體驗中的中國主體性。
然而,這個主體性是如何構造的?它與非洲的關係,如果不是以友誼和連帶為基礎的話,又是如何表述的?蘆淼在〈龍在非洲〉這章的記述值得觀察與申論。他在開頭就寫道:「在這個世界上最善於背井離鄉然後落地生根的,我覺得不是猶太人,而是中國人」(220)。以他的非洲簽證反覆被找麻煩為起點,蘆淼指出,非洲國家之所以不給中國人發放落地簽證,是因為「他們怕根本控制不住中國人流入國內」;中國不只有基建大軍進駐非洲,更在非洲各個角落留下了許多的足跡與印記,成為「隱隱能夠影響民間局勢的一股力量」(223)。然而,這批來自中國的新移民「所做的不過是賣苦力」、「掙非洲錢的洋民工」(224)。他寫道:
我真不希望,我的同胞們向非洲輸出的,幾十年來永遠是這些體力勞動。非洲人自己不願意做、懶得做或者不屑於去做的工作,我們去做。西方人做不了、做不來、覺得做了虧本的工作,我們去做。這樣多傻。我真不希望,我們的同胞去做那些本來就應該是當地人做的工作。而且做了之後,還無法得到感激。他們會在口頭上說,呀,謝謝你們無私的援助,我們永遠是好朋友呢。但然後呢?然後就是全世界人都可以去自己的家裡坐坐,唯有好朋友不行。因為好朋友太能幹了,他如果來了,就可能會讓自己家人沒事可幹,儘管這些活兒可能擺在那裡,如果好朋友不來永遠也沒人幹。(228)
姑且不論蘆淼的這番表述是否符合現實,他此番感受其實來自兩個特定的歷史構造:一方面是中國積弱不振的百年陰影,衷心希望自己的同胞能夠擺脫勞苦奮鬥,為人刀俎的命運;另一方面則是對種族主義壓迫的反抗,不願自己的同胞受到歧視與不公平的對待。問題是,在反抗積弱與歧視的同時,蘆淼或許沒有考慮的是,「因為自己太能幹而使得朋友沒事可幹」這樣的比喻本身可能也是一種種族主義;它非但沒有注意到非洲朋友敞開大門的期待與需要是什麼,也沒有考慮到援助與移民,一如探險與殖民,本不該是同義反覆,而是兩種不同的行動;前者的正當未必得以證明後者的必要,而對後者的警惕也不必然意味著對前者的否定。重點或許不在於中國人能幹與否,勤儉無雙,而在於移動與交往當中的文化衝突往往反映了主體性的問題以及對待他者的態度問題。同樣的心情也在畢淑敏那兒有所反映。對非洲同胞想憑英語到中國賺錢的想法,她頗感不以為然,即令她自己是不說英語的:「非洲普通黑人的英語常常是有口音的,還有些不合正統語法的口語。有時發音模糊,難以聽懂。他們把到中國教授英語當成新的致富之路,我個人覺得有點過於樂觀了。中國人求賢若渴不錯,但也不會孬好不分」(152-3)。雖然寫的含蓄,這段話的言外之意倒也無處隱藏。
認為非洲英語不夠「正統」或是非洲人不肯「吃苦」、不夠「勤勞」,當然都反映了中國人直觀的感受,但這些評價的背後,其實有一套根深蒂固的種族階序。非洲同胞雖然是我們的第三世界兄弟,但是在文化與文明,乃至於發展的程度上,他們仍是被援助的對象,而不是平等交往的主體。依此邏輯,中國移民與資本進入非洲當然是文明開化之舉,只能是無私的援助,而非有意的侵佔;非洲是中國躍上世界的舞台,是聰明的中國人在中國之外追求發展的機會之地。不諳非洲語言,不會影響中國人到非洲發財,但是想到中國發展的非洲人,還是該乖乖到孔子學院學好漢語的。無怪乎,在維多利亞瀑布的山水秘境之前,蘆淼會發出如下的感嘆:「如果沒有利文斯通,非洲大陸的秘密或許要到很多年之後才能被人發現。有沒有可能,要等到衛星上天,才能找到非洲大陸內陸的那些巨大的湖泊和河流?」(103)。作為豐饒之地,似乎非洲的美好只能被外人發現,而非洲的機會仍然不屬於非洲。[v]
有趣的是,這個沿著中非關係發展與體驗中出現的中國主體性,卻往往以「孤獨」的修辭來表述自己。年輕一代的作家尤其如此。蘆淼的《孤獨的時候我們去非洲》可謂其中代表。蘆淼不只在書名上將孤獨的感受與非洲掛勾,更在內文裡表述了一個詩意、自省的自我,將他與母親同行的非洲之旅表述為一趟靈魂探索的旅程。於是,儘管蘆淼的遊記與畢淑敏的《非洲三萬裡》在內容與視角上有諸多雷同之處──都是故事的收集──蘆淼的敘事更傾向於建立一種主體性,一種排斥各種事先計畫,只聽從內心的主體表現。在附錄〈走進非洲之前〉裡,蘆淼寫到旅行就像職業生涯規劃那樣,各人雖有不同,但高下可見。有些人走的是安穩的路線,以攢簽證章為目的,另一種則「劍走偏鋒,什麼地方有挑戰什麼地方難去,就專揀這些地方去[……]這類人就有點兒像職業生涯裡的自我創業者。不願意受別人的規則的約束,寧願自己冒風險去打拼,是這類旅行者的特點」(19)。像其他旅遊書一樣,蘆淼也以「老司機」的姿態提供讀者行前規劃的「實用資訊」(簽證手續、貨幣策略、行程規劃等),但是以上的表述卻突出了一種行旅主體的姿態,強調一種自我創業者的孤傲、不受規束,而非洲正是這類旅行者的心之所向。在這個意義上,孤獨來自於想要走一條沒人走過的路的想像,以及自我探索的期待,而非洲在旅行上所提供的挑戰恰恰最適合這些創業家類型的旅人。在此,旅行安排與生涯規劃被巧妙地與中非關係勾連了起來,非洲被投射為一個挑戰之域,一個挑戰、完成自我的新天新地。當然,這些投射沒有對錯可言,但孤獨修辭卻有效傳遞了種族潛意識裡的感受;這種感受與《戰狼II》與《紅海行動》沒有太大的差別。
無獨有偶地,黃河清的《非洲歸來不必遠方》也在書末收錄了一篇實用資訊的章節,名為〈關於非洲工作生活的Q&A〉,但其目的並不是要告訴讀者如何規劃行程、辦理簽證,而是透過一連串的問題來協助讀者自剖與考慮是否要到非洲工作和生活。這一方面顯現到非洲工作已然成為當前中國公民的就業選項之一,另一方面也突出既有的非洲想像對有意前往非洲者的制約。但是,在眾多的考慮中,黃河清強調,核心的問題不是非洲安不安全、文化適應是否困難,而是「我的孤獨值多少錢?」(279)。這是一個有趣、深刻,甚至帶點哲學意味的問題。但它也暗示了到非洲工作本身就是一種「犧牲」,而這樣的犧牲只能以薪資所得來計數與衡量,因為在非洲的工作經驗是無法被轉移到其他的工作上;在非洲工作的風險也確實比其他地方來得高;最重要的,孤獨本身就是最大的挑戰,連科技的進展也難以彌補和改善。而這本書的內容恰恰就是關於在非洲工作的中國國企員工如何面對日以繼夜的孤獨。蘆淼將非洲視為挑戰之域,黃河清則將之加碼為生命的賭注。在半殖民場景裡的這個賭注,其目的不外是為了更快地謀求中產階級的薪資與生活;去非洲的目的不是為了體驗非洲或孤獨,而是為了從非洲歸來,不再遠方。在這個意義上,所謂「孤獨」不只是一種清冷寂寥的感受,而是一種主體的裝置;這個主體與當下的環境陌生而疏離,但他又需要這樣的陌生與疏離來證實自己的存在。正如黃河清說的,「即便有的老非讓我見面就想退避三舍,而有的老非又給我提供了極端舒適的生活。老非終歸是老非,我終歸是我」(34)。其實,主體並不真的孤獨,只是需要孤獨的襯托。

「民族誌瞬間」
命運就是這麼有意思,把我這麼一個人發配到了大洋彼岸那些個荒蠻未開化之地,讓我想不旅游都不行。我在這樣的世界裡竟然有了些審問自己、凝視星空的時間。
──黃河清,《非洲歸來不必遠方》,4
相較於蘆淼與畢淑敏的遊記,黃河清這本書更接近於民族誌書寫,不過它記錄的對象不是非洲及其人民,而是在非洲的國企員工。如果說遊記是一種主觀化的採風,是作者對他者與地景的凝視,那麼民族誌,在1980年代的反身性轉向之前,[vi]是自許為客觀的再現模式,是將自我從其凝視中拔除的一種他者書寫。文化人類學家詹姆士‧克里佛(James Clifford)就指出,「只要民族誌的任務是將陌生的文化變得可以理解,那麼它永遠不能被限定為一種科學的描述」(101);相反的,克里佛強調,我們必須認識到民族誌的文本性與寓言性,亦即它是一種描述與再現他者的「故事」,本身就糅雜了客觀的現實與主觀的認識。[vii]另一位人類學家瑪麗琳‧史崔珊(Marilyn Strathern)則主張,民族誌書寫包含兩個田野,一個是作為研究對象的田野,另一個是作為書寫現場的田野,這兩個田野之間的互動構築了她所謂的「民族誌瞬間」(ethnographic moment)。換言之,作為一種知識的形式,民族誌並非純然客觀而科學,而是一種經過轉化的洞見。也因此,民族誌的意義不在於他者知識的積累,而在於反思的瞬間,在那既「沈浸於內,又游移於外的關係之中」(6)。[viii]所以,當我試圖從民族誌的角度來理解黃河清的遊記時,我想強調的是一種糅雜的閱讀策略:一方面將書寫者本人置於書寫的場景裡,作為民族誌再現的一部分(例如作者與當地人的互動),另一方面注重作者自身的主體存在,亦即他對當地風土與當下事件的描述、感受與反思。不同於畢淑敏與蘆淼對收集故事的強調,彷彿自身只是外在於故事的收集者,在黃河清的作品裡,重要的不是故事,而是見證──不只是非洲的風土民情,更是中國國企及其員工在非洲的存在,以及他們為非洲帶來的影響。在這個意義上,「審問自己、凝視星空」的孤獨既是主體的裝置,也是中非關係的寓言。
對黃河清來說,孤獨的構成是多重的:一方面是空間上的隔離,這包括了非洲與中國的空間阻隔以及國企員工與非洲人民生活空間的隔離;前者可能造成妻離子散的家庭悲劇,後者則會導致國企員工與非洲人民的緊張和矛盾;同時,感情與文化生活仰賴祖國的補給亦會強化人在異鄉的孤寂。另一方面,中國國企與非洲政經緊密而複雜的關係,以及幾乎是根深蒂固的種族心態,更使得派駐非洲的國企員工形成一個極小的社交圈,若不與同事相濡以沫,彼此安慰,就只能相忘江湖,自度傷悲。如此隔離的體制性安排製造與強化了中國人特別「吃苦耐勞」的意識型態,乃至形成一種「集體的禁欲主義」。李靜君(Ching Kwan Lee)的研究就顯示:在非洲的中國工人普遍居住在當地人稱之為「中國屋」的集體住宅裡,如此隔離的居住狀態使得中國工人都是囚犯的流言,在當地甚囂塵上,而這樣的道德批判,在海外的中國移工眼裡,則強化了中國人被外國人羞辱與歧視的感受,使得他們更以「吃苦」作為民族身份與道德邊界的識別標誌(157)。於是,隔離本身就成為中國在非洲的寓言。黃河清以極為淺白的文字寫道:
中國在非洲的投資與其說是援非,不如說是救己。[……]一方面,近期內中國對非洲的援助完全通過中國進出口銀行直接撥款給相關企業,也就是說錢完全不經過老非們的手,而是直接從中國銀行轉到中國企業的手裡。因此當地的深度腐敗對此基本沒有影響。另一方面,中國企業在收到錢後,基本又全部投回了國內。項目設備的進口以及人員的僱佣,基本上還是以國內的廠家和中國人為絕對的主導。因此錢轉了一圈又回到了中國人自己的手裡,所以流到外人田裡的肥水,只是極小一部份。(28-29)
如果說資本的跨國流動,以援助之名,繞了一圈,還是在中國人的手裡,那麼在非洲設立公司與工廠、進行基建的中國企業總要與非洲人民有所互動吧。對此,黃河清則有以下的表述:
在這一點上,我們公司探取的方針政策一直都是「中國人的項目當然應該由中國人來建!老非出出體力就可以了!」因此一般的工程全都是由中國人負責管理層,高層僱佣老非更是絕對不可能的,不管來的人多優秀,總會有點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感覺。即便和少數的老非合作,也是一種以黑治黑的心態,依靠那些老非的能量來對抗當地許多不合理的現象。(219)
易言之,國企員工在非洲感到的孤獨,很大程度上,是資本運作與種族主義的結果。儘管來到非洲,中國國企仍然是以中國的方式運作,不僅資金與人力來自中國,連心態也沒有因為時空轉換而有所改變。「以夷制夷」仍是百年不變的對外策略,「肥水不落外人田」的老祖宗智慧也仍然主導著援外的思路。[ix]也因此,在行文上,黃河清對自身的種族潛意識直言不諱,不但直指非洲髒與窮,連非洲人的體味也毫不客氣地批評。他將非洲人民分為五等,最下等者,他直言,是無法交流的,因為「當我們用憐憫的眼神看著他們在微不足道的小事面前瑟瑟發抖時,他們也會用憐憫的眼神看著我們為著虛幻的未來東奔西走」,而那些「整天無所事事閑逛的,在你車前敲打著玻璃要錢的,把握一切機會對你進行勒索的」則是稍上一等的老非,因為「他們既沒有步入現代化的機會,也失去了安貧樂道的平常心」;再上一等者是從西方與中國留學歸國的非洲知識青年,他們儘管對環境憤恨不平,卻無力改變大局;最上兩等的則是皇親國戚與各方權貴(30-3)。
雖然作者的焦點是國企員工在海外面對孤獨的心路歷程,非洲種種只是花絮,但這反倒賦予了這部作品「見證」的意味,從而促成了「審問自己」的可能。在〈老板發威整拆遷〉這一章裡,作者描述中國國企在非洲發展的一個重要現場。作者受命要與剛果當地村落的一個非洲靈媒接觸,以說服村落百姓搬遷,讓國企進駐開發,架設電塔,因為當地百姓相信,地有祖靈,不能隨意拆遷,而這位靈媒或可與祖靈溝通,打通門路。在這個過程中,不僅作者發現這個靈媒曾經留學中國,獲得北京清華水利工程的博士學位,他也明白了村民的抗爭並不是為了討價還價、索求賠償而演出的戲碼。可是就在他說服了靈媒前往現場的當下,他赫然發現老板早已聯繫好剛果軍方,強行拆遷。眼見靈媒因為村落拆遷而瘋顛,他明白了自己所為不過是公司的備案,也因此自己成為強行拆遷的同謀──不管靈媒靈或不靈,拆遷都是必然。帶著一點同情與更多的世故,他寫道:
「趙總!都拆完啦!」遠遠傳來一聲呼喊,聽聲音是趙總下屬管工程的王經理,這聲音標志著他沒有因為胡拆這裡褻瀆神靈慘遭不測,也標誌著這次搬遷工程的結束。不久之後,這邊便會被剛果河的水所淹沒,不管是否真的有靈,都已不會再有,靈是否真會哭號,也不再被人聽見。不管世界有多少種解釋,勝者永為王侯,敗者終生為流寇,所謂自由之靈,自此湮消雲散。(256)
黃河清的描述,在這裡,遠遠逸出了「遊記」的範疇,而展現了某種的「民族誌瞬間」,讓我們看到發展的代價如此沈痛,以及作者見證苦難之後的人生體悟。然而,作者不只是個旁觀者與記錄者,他更是這個事件的參與者。他無力扭轉事情的發展,也無意為村民的命運做出更多的努力,但他畢竟為那些不可知的祖靈留下了一點悲憫的「見證」,並對「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大道理予以嘲諷;他讓我們看到,即令發展的步調無法停止,發展造成的「不安」仍然值得我們關注與思考。因此,我們不能不在他的悲憫與世故之間把握分寸。作為讀者,我們或許同樣無力抵擋發展與拆遷的巨輪,甚至羞於承認在其中獲得的好處,但我們或許都該捫心自問:在悲憫與世故之間如何把握自己,如何與時代共進,又保持距離。儘管作者未必有任何反思的企圖,也未曾深入檢視自身的種族意識,只是單純地分享自己的見聞與體會;然而,恰恰是這樣一個含括自身在內的視角,提供了一種感性的見證,迫使讀者思考「中國在非洲」的意義,以及它與「中國的非洲」之間的關聯。
結語:「世界中的中國」與其不安
「向南看」(Looking South)政策是成功還是失敗,就取決於它
是支持非洲大陸的自主發展計畫,抑或深化其與世界經濟的融合。
──莫約、耶羅斯、傑哈,〈帝國主義與原始積累〉,133[x]
2018年10月15日,《紐約時報》報導了一則消息,在國際社會引起嘩然。[xi]一名在奈洛比郊區的中國機車工廠擔任銷售員的肯亞員工,歐強先生(Orchieng)指稱,與他年紀相仿的中國上司叫他「猴子」,令他感到歧視與難堪。事情是這樣的:在一趟公務旅行中,歐強與上司看到一群猴子在路邊,上司就叫道:「你的兄弟」,要他分一些香蕉給牠們。類似的狀況一再發生,於是歐強錄下了一段他與上司的對話放在網上。在這段對話中,上司不斷強調黑人如猴子一般,並且以西方曾經殖民肯亞為理由,拒絕承認肯亞的黑人應該被平等對待。毫無意外地,這樣的言論立即在網路上引發熱議,而這位上司也於隔天被遣送離境。雖然遣送的處置可謂果斷,但歧視的印記卻不容易消除。最令人不安的是他毫無遮掩的種族潛意識,強調黑人髒、窮、笨、又有體味,一如黃河清在書裡的描述,而這位中國上司之所以敢於如此放肆,是因為「他不在乎,也不屬於這裡」。[xii]
這個事件讓我們明白,黃河清的記述不只代表了他自己,也一定程度地表述了部分在非中國工人的心聲,而這恰恰是中國在非洲最為人詬病的地方。傅好文(Howard W. French)在《中國的第二個大陸》中最核心的批評也在這裡:在非洲「中國並沒有與西方的家長作風分道揚鑣,而是如一般所批評的,取而代之。非洲人並不真的是兄弟。一點也不。在友好的面具下,中國官員把非洲人當成小孩,認為他們只能夠緩步行走,得用糖和幼稚的語言誘使前進」(221)。劉曉鵬的系列研究也顯示,早在1960年代,當台灣仍與中國在非洲競爭外交支持的時候,「台灣也在非洲建立了台灣版的『殖民論述』,認定自己所代表的中國足以領導『落後的』非洲」(2012: 143);雖然表面上,台灣對非洲的農業技術援助是以孫中山的「扶助弱小民族」為指歸,但實際上,從當時的新聞局長到非洲各國的公使,都對非洲人投以歧視的眼光,認為他們「自大、倨傲、混亂、骯髒而沒有責任感」(2012: 146-147);連當時的台灣媒體也提出移民非洲,協助開墾的呼聲,以解決非洲國家缺糧的問題,相信台灣可以派出「大量青年像漢代的張騫班超一樣,前往非洲宣揚我文化並幫助他們」(2012: 154)。當然,1960年代的台灣與當前的中國無法相提並論,但在對非洲社會的認識以及推動雙邊交往的論述卻是如此的相似,以致我們不能不承認某種種族潛意識確實在兩岸社會中作用著,形塑著漢人對黑人的感覺與認知結構。姑且不論中國在非洲是否真如西方媒體所說形成了新的殖民主義,或是如李靜君描述的只是「國家資本」在獲取最大利益與執行國家政策之間所表現出的矛盾行為,我們大概都無法否認這些資本與國家行為也受到種族潛意識的左右,而且國家資本的理性要求還不斷地透過體制性的安排──包括居住空間、勞動與僱佣的種族性區別、乃至於資本流動與資源交換的契約行為──強化了種族潛意識,儘管表面上的官方論述恰恰相反。如果我們不能對自身的種族潛意識進行反省和警惕,再多的援助承諾與美好願景都無法改變非洲社會與西方媒體對中國的質疑和警誡,中國深入世界的過程只會更為崎嶇而扭曲,即令我們仍願意相信前途是光明的。
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在非洲不僅如李靜君所言,是資本主義發展史上的一次事件,它也是中國走向世界,重返榮耀的里程碑。李靜君強調,「中國國家資本的向外流動只是全球中國的一個例子」,在經貿投資外,「中國的全球性存在以多元的形式在不同的場域中展現:人口移動,全球的傳媒網絡、高等教育、科學研究、多邊的區域與全球信用機構以及中國非政府組織在海外的拓展等等」(165-166)。這意味著我們對於中國的研究與理解不能再侷限於中國境內,而要從國際互動的具體脈絡中重新理解中國。換言之,「世界中的中國」(global China)將成為一個新的命題與學術領域,這也意味我們必須嚴肅面對「中國在非洲」與「中國的非洲」之間的關聯,從外部出發打開內部的秘密。對處於中國內外夾縫中的台灣學者來說,這意味著既不放棄介入改造中國的責任,也不忽視自身既內且外的曖昧處境;此外,更應該如陳光興所建議的,「善用綁在我們身上、甩不開的身分認同,從內部發言,讓自身所屬的群體能夠積極面對問題」(2006: 436)。
作為一個知識與政治的命題,「中國的非洲」最終追問的仍是中國的問題;它是一個鍛鍊跨文化、跨種族感性的挑戰,是在政治與經濟之外對「世界中的中國」的另一種要求。這或許正是思想第三世界在當前局勢中的意義:一方面對我們據以認識世界的媒介保持警醒,另一方面不斷追問與自省我們和世界的關係。或許面對「世界中的中國」及其不安,探其根源、溯其變異,正是我們現在出發必須首先正視的起點。
(完)
【銘謝】
本文最初以英文發表於杭州中國美術學院亞非拉文化藝術研究院在2018年6月1-2日所舉辦的「思想第三世界:藝術、翻譯與媒體」國際工作坊。感謝與會朋友們的討論與分享,尤其是高士明副院長對工作坊的支持,以及唐曉琳博士、曹梅清、姚雨辰、李佳霖、彭婉昕的協助。之後,又以「華人穿非衫:今日中國的非洲之初步觀察」為題,於2018年6月22日在金華的浙江師範大學非洲研究院發表。特別感謝雷雯老師的邀請,以及浙師大朋友們──張勇、徐薇、章亮瑩、黃金寬等──的批評與討論。謝力登(Derek Sherida)與賀照田老師對本文初稿提出的諸多建議與批評,筆者亦受益匪淺,特此致謝。最後,感謝陳光興多年來的啟發、鼓勵與支持。沒有他的敦促與推動,這篇文章是不會出現的。
注釋
[i] 比方說,在台灣出版的六本碩士論文,儘管主題不一,都是從旅行書寫、流浪文學與流行文學等角度出發研究三毛的作品。在華藝線上圖書館可以搜尋到的相關期刊論文,多數也持類似的觀點。
[ii] 三毛當時生活的地方是西撒哈拉。1886年,這塊地方被劃為西班牙的保護領地,並在1958年成為海外省。1975年,西班牙和摩洛哥、茅利塔尼亞簽訂馬德里協議,準備離開。1976年,西班牙撤出西屬撒哈拉,其後大部分領土被鄰國摩洛哥佔領,三毛也因此搬到西屬加納利群島居住,直到1981年回台灣定居。
[iii] 2000年,三毛遺物被收入後來的台灣國家文學館中典藏;原來出版三毛作品的皇冠也在2010年以「三毛典藏」重新出版她的著作,並授權北京出版集團的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於2017年出版三毛全集,共14冊。
[iv] 見劉曉鵬,〈回顧一九六O年代中華民國農技外交〉,《問題與研究》44.2 (2005),頁131-145;以及〈一種刻板印象,兩種不同政策:比較兩岸在非洲的「神農」們〉,《中國大陸研究》59.2 (2016),頁1-35。
[v] 雖然這裡的分析以畢淑敏和蘆淼的遊記為對象,但這類種族主義心態不是中國公民的專利,而是華人社會中普遍的態度。劉曉鵬在討論台灣在非洲的農技援助時就曾指出當時的種族主義心態;見〈農技援助之外:小中國對非洲的大想像〉,《臺灣史研究》19.2 (2012),頁141-171。陳光興在《去帝國》(台北:行人,2006)中則使用「漢人種族歧視」(424)一詞,一方面強調「漢人」為中國主導性人口,以及中華文化的傳承與流佈主要是以漢人為基礎的事實,另一方面也使之與境外的海外華人與境內的少數民族有所區辨,畢竟這兩者的處境不同,也往往處於漢人種族與文明階序的下方和外緣。陳光興企圖回到中華帝國與漢人世界觀的脈絡中,梳理種族歧視的問題,並強調這樣的種族文化主體形構與帝國歷史的關聯。同樣的,本文對種族主義的批評無意針對中國大陸公民,而是著眼於台灣及其他海外華人社群也分享和承繼的漢人文化種族潛意識。關於這點,我會在結語一節再做申論。
[vi] 1980年代,在後結構主義思潮的影響下,北美的人類學家開始反思民族誌的文本性格,強調人類學家對異文化知識的再現並非純然客觀,而有高度主觀的介入。一般認為,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E. Marcus, ed.,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是推動民族誌反思的重要哩程碑。
[vii] James Clifford, “On Ethnographic Allegory,” In James Clifford and Geroge E. Marcus, eds.,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99-121。
[viii] Marily Strathern, Property, Substance and Effect: Anthropological Essays on Persons and Things (London: Athlone Press, 1999) 。
[ix] 這也是國際媒體對中國在非洲常見的批評,亦即中國的援助是一種變相的交換與剝削,以及中國的投資並沒有進行技術移轉,也沒有為非洲帶來更多的工作機會。
[x] 薩姆‧莫約(Sam Moyo)、帕里斯‧耶羅斯(Paris Yeros)、普拉文‧傑哈(Praveen Jha)著,陳耀宗譯,〈帝國主義與原始積累:關於新非洲爭奪戰的筆記〉,《人間思想》(繁體版)第11期(2015),頁117-136。
[xi] Joseph Goldstein, “Kenyans Say Chinese Investment Brings Racism and Discrimination,”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5,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10/15/world/africa/kenya-china-racism.html?emc=edit_mbau_20181015&nl=morning-briefing-australia&nlid=6210613320181015&te=1&fbclid=IwAR2EDGzCS1f_LPBoXqayt_8iCS58RWDKLnkoCVXkodRjmouFTPQDy-HzYwE。
[xii] 同上,見文中崁入的視頻。
發佈日期:2020/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