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今年7月,趙剛教授出版了《主體狀態——雜文散論於歷史、文學與社會理論之間》一書,書中彙集了他多年來的學術與思想歷程,反映了他從西方新左翼立場逐漸轉向中國和第三世界歷史文明的主體性思考。此外,該書亦透露出他對傳統學術分工的反抗,並批判了過度依賴西方理論的學術趨勢。作者強調社會學應與歷史和文學結合,以應對變革中的社會現實。書籍出版歷經波折,原本應為社會學教科書,但因種種原因,最終轉變為隨筆集。隨著對魯迅和陳映真的深入研究,作者重新審視台灣與中國的關係,並強調反帝反殖的重要性。趙剛認為:真正的「普世性」應在多方文明對話中誕生,而非西方霸權的產物。書中探討了中國崛起背景下的知識責任,以及如何重新認識中國和第三世界,為學術與政治上的反思提供了深刻的見解。
本文為該書的序章,獲趙剛教授授權轉載。有興趣者可到唐山書店網頁購買。
這本集子走過不少坎坷路。一切都得從二十多年前他人的一個善意以及自己的一個「輕諾」說起。2002年某天,是春是秋都記不得了,一位任職於台北的一家知名出版社的黃姓編輯,敲開了我研究室的門,請我為他的東家寫一本社會學教科書。當下我毫不思索立即禮貌拒絕,因為腦際從未閃過這一念頭,直覺是小伙子亂槍打鳥。那時正值壯年,對這個提議心裡多少還有些抵觸呢。但這位社會學碩士出身的青年編輯還真是「有備而來」,不但努力說明好的教科書的社會意義、「很多大師也寫教科書,好比季登斯」,而且呢,還表現出對我的寫作的足夠熟悉。說實在,這有點管用。但更要命的是他的「鍥而不舍」,在「前高鐵」年代,多次專程南下拜訪。地非南陽,何需三顧?終而我點了頭,不只是因為小伙子的誠意弄得我有些不好意思了,也是因為他對我提出的「刁難」竟都一一答應:無截止日期、「老師你愛怎麼寫就怎麼寫」。而且,還預付了一筆稿費。
之後,我也的確為「社會學教科書」建立資料檔,分門別類、見縫插針地蒐集起資料來。但是,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始終沒能定下來密集而持續地寫作。這主要是由於我性格上的一個缺點:一旦必須做某件工作,它就經常會退變為一塊「責任」沙地,熱情快速流失,而同時總是有更想做更想寫的東西冒出來向我眨眼。這個毛病適用於成語「見異思遷」嗎?此外,又由於我術業無專精,總是逐時局而論,好比不免一直被「社會運動」、「民族主義」、「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多元文化」、「紅衫軍」,或「太陽花」……這些時潮熱點所勾動,作起「批判」來。時也,命也,我就是歧路上的一隻羊。回想起這大半生,不是完全沒有一點點遺憾,但想一想也就沒啥好「當初如果……」的了,因為,無論是就天分、師承,或是用功之勤,我老早就已免於什麼「建樹」奢望了;無論是學術的深耕有得,或是思想的一點突破。但幸好,大約始自2008年,我開始有了長期而聚焦的投入,密集地耕耘起陳映真的文學與思想來,沉吟至今。這總算是在隨時流轉多年之後,於桑榆之際,發現了一口我所樂於深掘的井,讓我重新認識台灣、重新認識中國,重新認識二者之一體。說陳映真「給了我一個祖國」,並不誇張。由陳映真入魯迅,那又連接上一片崎嶇深刻、明暗之間的思想風景,認識到現代中國的悲哀與偉大……。不敏如我,當然是不敢上比於魯陳,但總也不敢自棄於下學上達,何況,偶然也對他們倆向來沒有要成就什麼華麗殿堂,甘於孤獨,甚至偶現一抹奇異荒廢的精神光澤,而感到某種稍帶虛榮的親近。讀者很容易在這本集子裡的多篇文章中看到他們二位對我的影響。我相信一種中國的也是第三世界的「社會學」,是繞不過他們的。它必然是成長於歷史、文學,與廣義社會理論之間的那塊豐饒的土壤,而非專業學術高牆之內的盆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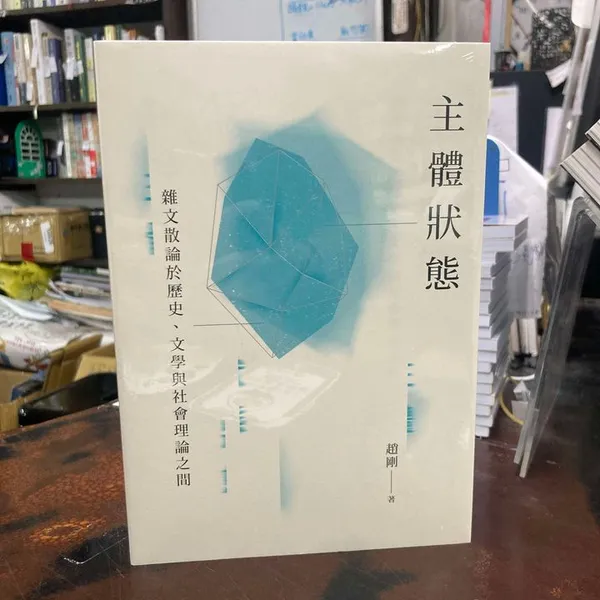
自從答應書約後,五年十年,十五二十年過去了。其間,不是沒有下過決心一償文字債,例如2006年秋「紅衫軍」喧囂而始、戛然以終後不久,若有所失的我就曾打算定下心來閉門寫教科書,而的確也寫完了一篇五六萬字的長文〈社會學思考〉,交代了我當時所以為的「社會學」,但這篇文章因為太長而且體例也與現在的集子不搭,就從現在這本集子裡割出,但它的一些比較核心的內容還是可以在〈社會學的用處、限制、濫用與未來〉那篇演講稿中見到。2006年的這個寫作,見證了我雖開始企圖出離美西方社會學,但終究不過還只是拿中國例子注西方概念罷了。但無論如何,總算是邁出了艱難一小步。寫完這篇沒多久,我又「旁騖」了,就是我方才說的──讀上了陳映真,以及魯迅。之後的光陰並沒有不似箭,倏乎抵於退休之年。在這些年間,當初約稿的黃編輯早已離職,不知江湖何處,接續他的編輯後來也換了好幾位。她們總是很客氣,逢年過節會發郵件問好順道詢問進度,後來進度也不問了,只問好。起初我有些羞愧,後來竟也習慣了。其實我很不想老欠著,但是寫作又嚴重落後。一度我曾致函提議取消約定、退預付款,並負擔利息,但對方顯然並不認為那是好點子,一笑置之,繼續對我勗之勉之。
2017年左右,因為正開著「魯迅入門」一課,對魯迅的獨特雜文書寫頗有感動,於是對出版社提出了以「社會學隨筆集」取代教科書的構想:不循教科書的制式議題與組織,意之所至寫一些「社會學的」「隨筆」。「甲方」同意了。當年夏天,我就以「隨筆」的心情,盡量少掉書袋,環繞著我當時頗感興趣的現代性與「天」的問題開始寫,但沒想到寫得還是太長。隨著筆走那麼長,那不就是漂流筆了嗎?自己走一趟,才知道為何魯迅的雜文是絕唱,見首不見尾,但又言之有物,而又意義多層,且餘味無窮。現在,我為了這本書,將長文「精簡」為〈想像一種“有法有天”的人間秩序〉。那之後,我又故態復萌,把隨筆集的寫作又給收進抽屜,因為我又承接了一個難以拒絕而且更有挑戰性的任務──編兩本陳映真文集並做導言。因為工作量遠超出我的預期,直到2021年九月新冠尚在蔓延時,才把稿子交了。之後,我才又重新開始「隨筆」至今。這期間,上課之餘擠時間寫,寫得還算順利,因為多年下來累積了不少課程講義、會議或講座的未完稿,雛形略備等待完善,例如〈哭笑不得的現代性〉、〈你不可在迪士尼樂園裡奔跑〉,以及〈歷史編寫與社會控制〉,就都是2005年應北京清華大學高研院之邀訪學時開的「文化研究」課程的講義略做改寫而成的;讀者應可從中看到我早期的「新左」痕跡吧。2005年的北京行,雖然當時惘然,但事後看來應是人生的一個節點,從長期面向西方的知識習性「轉向」中國。話說我之前如果有休假或開會,還都是往美國奔,而2000年之後我就再也沒去過美國了。可能是先有這個轉向,而後陳映真,以及魯迅,才對我展開吧!
改寫了一些講義、手稿與會議發言大綱之外,也選了一些先前發表的文章,最後再加上我的一篇關於關於社會學的用處與害處的演講逐字稿,這樣,我終於在退休前編好集子交了稿。不久,出版社來函表示他們無法出版,而原因除了二十年來整個出版市場變化巨大與不景氣之外,也是因為這個集子與他們對社會學的期待之間落差過大。他們的意思大概是:雖然我們不是對陳映真或左翼有什麼意見,但此書觀點明顯太偏,沒有平衡表述多方學派觀點。
我能理解。
台灣這邊不出就大陸出吧。我問過大陸的熟識出版編輯人,都是好朋友,但也都誠懇而委婉地表達了困難。原因不止一端,包括篇幅太長、市場考量等,但也都特別強調了「在兩岸目前的這個狀況下,要出這本集子啊……」。同樣,我能理解,但有點難過──對兩岸走成這樣。有一位朋友好心地建議我將「文學的」與「社會學的」分成兩本出。我感謝朋友們的建議,但我還是想以現在的形式出,因為它是,好或壞,我對「社會學」的看法的真實體現。在非西方地區,或第三世界,社會學本就不得不與歷史、與某種文學書寫難分難解,因為共同關注的對象都是變革中的人與社會,而且它們都是在過去、現在與未來的辯證中操作。這是我的看法,我並不欲望引人從己,但我希望留下記錄。於是,這就是讀者您所看到的現今這本在「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出版社」出版的集子。多年以來,「台社」(《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是我在這個島嶼上唯一外延的知識連結。曾經,台社編委會同仁最顯目的知識特徵即是質疑學術分工並同時輕看學門認同;不少人都是各自學科的異數邊緣,例如于治中、卡維波、何春蕤、夏鑄九、陳光興、瞿宛文……。類似的交往模式也表現在我與對岸學者的關係上;與我文會者,率多文史哲乃至搞藝術的,至於社會學圈嘛,大概只有半個吧,呵呵。這也是有歷史的。2005年我寫的一篇對龍應台女士的批評,以及2010年我對大陸一位學界朋友的支持,先後捲進了當年「新左」與「自由派」的鬥爭,接連造成了島嶼內外曾經朋友的「割席」效應。對這些效應,尤其是來自大陸社會學圈後來被視為屬於「公共知識分子」的朋友,我的反應頗遲鈍,常常很久之後才啊一聲悟過來。我或許應該更冰冷地相信學術與政治從未真正分離過,但因為總還看到有那麼二三子能做到盡量懸置立場只在乎論證,我就總還是在矛盾中。
收在這本集子裡的文章都有一共同「學術」特徵:抗拒那以「專業分工」之名將學術思想碎裂為互無關連的學科,進而在各學科內部進行「領域再分化」的趨勢。在這個無限分裂中,學術與整體現實越來越疏隔,更加著迷於研究問題的小巧、方法與方法論的削尖、西方理論或概念的依賴,以及──與「實證科學」標準的綁定。結果是:現而今,誰還在讀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著作呢?有,研究生與他們的老師。少數人在小小行話圈裡相濡以沫的趨勢越來越嚴重。但這似乎也不能完全責怪於學者,因為學者既是共謀者也是受害者;你不如此寫就沒法發表、沒法升等(評職稱)。學術評鑑體制正是隔絕學院與民眾、學術與歷史的高牆。於是,不得不承認社會學這個學門,至少以我在東海大學社會系這些年所親歷的,畢竟還曾有那麼一點點「自由度」,課可以任意開:「德意志意識形態」、「E.P. Thompson」、「威瑪時期」、「陳映真」、「魯迅」與「論語」……。「自由度」主要是因為學科年輕,學術範式與產品規格還沒有像經濟學那麼標準化,沒人有足夠的權威說:「你這不是社會學」。這本雜文散論或許就是一個現身說法;你可以說它這裡不行那裡很爛,但你還就是沒法說它「不是社會學」,因為你說不出什麼是社會學。但這樣的「自由度」確實也在新世紀快速流失中,而且在越是「精英」的地盤裡越是如此。我聽說,台灣有不少社會學界同仁,都是先英文發表於SSCI刊物上,行有餘力,則出以中文副本,好再變現一筆TSSCI。大陸的社會學的教學、研究、寫作與發表環境會好些嗎?我不清楚。
抵抗越來越逼仄的學術分科,與在思想學術上反思自我殖民並重新展開社會聯繫,對我而言,是同一回事。
這本集子所收錄的文章跨越二十年。敏銳的讀者會看到作者的一個「變化」走向:從一種比較是西方新左翼的「普世的」、「批判的」、「現代性」立場,一腳深一腳淺地、不甚優雅甚至有些笨拙地,走向一種中國的與第三世界的歷史文明主體性立場。您若簡稱此一過程為「從洋左到土左」我也不反對,但需要一點澄清:這個「土左」立場,既不籠統否定「現代性」,也不採中西二元對立簡化姿態,而是以一個歷史的、實事求是的前提──不同文明必然是以不同的承繼與想像進入現代──為基點,朝向人類多元一體共進未來這一規範性前景。是在「多方共進」的作為過程中,所謂普世才可能浮現。用魯迅早年的話,這是一條「審己知人」、「取今復古,別立新宗」的路徑。今日回望,這不就是清末以來,在西方對「現代性」的壟斷解釋下,中國知識分子的那一始終敗而不潰、屢伏屢起,義理情感上與「弱小民族」或「第三世界」同在的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大議程嗎?在章太炎、魯迅,乃至陳映真等人的思想世界中,其實都能看到這條隱晦而強野的線索。在當今「中國崛起」的情境下,這個計劃反而更重要,因為所謂中國道路必然牽涉中國如何面對西方文明與知識霸權、如何定位自身與第三世界。這條道路既非從人失己,也非引人從己,更非獨斷而行,而是形成於與不得不共其命運的各種文明主體之間的對話交織。長期以來,西方以一種超然的傲慢的姿態宣稱它的價值是「普世價值」,其實經常是霸權竊「普世」之名的宰制飾語。美西方的「普世」從而只意味「我說了算」。歸根究底,世界不可能在相互理解與批評缺位之下產生真正的「普世性」。對中國崛起,我們在台灣的知識分子學者文化人,有責任也有幸運作為主人公一分子,要求思想與道德上的同步崛起,對人類擺脫以美國為首的深具種族與宗教底色的單極霸權及其幫閒的軍事脅迫、經濟榨取、文化宰制、身分歧視、以及自然耗竭,並對那以人類共同體為核心意象的「普世」進程,承擔起一份知識責任。承擔起中國人身分,因此不是大國崛起後的享樂主義,而是更大的責任承擔。如何重認(重新認同以及重新認識)中國、如何有根關切社會發展、落地批判社會現實,是擺在我們面前的最大的挑戰。這樣一種挑戰,對1970年代的進步香港青年而言,曾濃縮為四字:「認中關社」(認同中國關心社會)。對1970年代末鄉土文學論戰時的陳映真,同一立場則展現為:「關切文學的民族歸屬性;關切文學的社會意義」。
如果說,重新認同並認識中國以及那遼闊的第三世界,是本書的一大嚮往,那麼,它的另一面,不待言,就是學術與政治上的反帝反殖。台灣的社會學學門(暫且不言其他學科)的出生,就與冷戰時期兩大陣營的對抗密切相關,無法不落下冷戰、反共,乃至反中的地緣政治胎記。根據「總統府網站」的張貼訊息,2000年陳水扁上任不久,接見美國「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 代表時,就表揚該基金會曾「協助」「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東海大學社會學系、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等學術研究單位的設立」。因此,如果說台灣的社會學自成立以來就與帝國的地緣政治利益,以及它在台灣進行的(沒有總督府的)「新殖民」有密切關係,絕非無稽。不直面這一對美國糾纏依附到無意識程度的深度關係,那麼任何對「社會學本土化」的自我宣稱,都將嚴重缺乏歷史基礎,從而僅是一自戀空想。長期以來,台灣的社會學界從不曾萌生過對這一學科的知識社會學或學術史的審視興趣,毋寧是可悲的,而本人當然是責任人之一。近十年來,這個集子的撰寫者,在陳映真的啟發下,越來越意識到人文社會學科的知識狀況與新舊殖民及帝國主義之間的關係,而將「反殖民」(或「去殖民」)置於思索的一關鍵位置。陳映真的晚期思想,尤其是展現於小說《忠孝公園》的,讓我越來越認識到「反殖民」不只是「反」,「去殖民」也不只是「去」,因為最終而言都無法不展開「主體的確立」這一正向努力,而後者又必然與「家園」、「家國」、「傳統」,甚至「迷信」密切相關;而西方現代性的核心困境之一就是各種家園的失落。如果沒有一種家園意識,那麼無論是以西方內部的「反現代性」來反西方現代性,或是超拔家園徒以「第三世界」反殖民……,最終都有可能落入某種虛無危機。難怪魯迅在《破惡聲論》裡說「偽士當去,迷信可存」。
因此,若要標定這本集子的核心關切,也不妨說它是朝向「主體社會學」的一個初步嘗試。主體(subject)或主體性(subjectivity),是一個來自西方、麻煩不算少的概念,常與唯心論與意志論互綁、後設二元對立世界觀,且有滑向唯我獨尊的右翼民族主義甚或法西斯主義的危險傾向……;這都是我們使用這個概念時所可能蹚到的「渾水」。但我們不應怕腳濕就不去海邊;過度潔癖的後果,於個體,是道德虛無主義的危機,於大群,則是民族自尊、文明自信的地基淘空。已經高高在上的帝國可以主體空白,但對第三世界、對所有被殖民、被剝奪主體性的群體,不談主體則是不可想像的。取消了主體概念,所有反帝反殖企圖尋找自身發展道路的思想,以及誠、愛、信念與希望這些人間價值,又將著床於何處?如果我們不打算將「嬰兒」跟著「渾水」一起潑掉,那就必須重思主體,重新審視自身的主體狀態。
在美西方社會學傳統裡,「主體」經常僅僅是悖論地作為彰顯「結構決定性」的被決定對象而存在,從而「主體社會學」這個提法就幾乎是一個矛盾複合詞(oxymoron)。於是,被客觀規律(或「社會事實」)所決定的「主體」,或「行動者」,或「能動性」(agency),就因為動能的自我解消,而使自身無法成為變革思想的一有機組成。然而,本書的寫作旨趣卻是欲想那包括台灣在內的中國人的社會學,不再是民族的與第三世界主體性思想與關懷的外在物,且與所有進步的人文與社會科學一道思索中國與第三世界的現在、過去,與未來。而若果有如此的知識計劃在抱,那麼似乎叫不叫它「社會學」也都可以是無關宏旨;本書作者對僵化而自戀的學科分工一向缺乏虔敬。在「主體社會學」裡,「主體」如有預設,也將首先是它的「非決定性」(indeterminacy)。在此前提下,「主體性」是一包容的聚集:可以指涉廣義的黑格爾─馬克思歷史哲學中那摘除鐐銬作興變革的「歷史主體」;可以指涉全球範圍內的特定歷史文明身分;可以指涉新舊殖民體制下人民對主奴體制的反抗;也可以指向資本主義市場與行銷體制下人對剝奪與異化的反抗……。在以上諸面向中,最為核心的則是它們所共同涉及的一種「人民的」(經常也是階級的與民族的)倫理立場──論說者是否站在一種民眾的、民族的立場思考、表達,與行動。以文藝為例,「主體性」的有無決定於你是否能自由自在真實無妄表達自身喜怒哀樂情思志節,或,你只是一隻學舌鳥,唱說他人(帝國、殖民、資本、強勢宗教或文明等)的顛倒夢想。於是,「主體性」其實並不具大型理論、歷史目的論,或任何終極「確定性」的保證,其第一義是歷史時空中實踐,所謂執之則存,失之則亡。「主體性」因此不是玄學概念,而是倫理─政治概念,是魯迅所謂「內曜心聲」的砥礪發揚。以此而言,「主體性」的曖曖之光反而經常明滅於那一向被精英視為迷頑的「草民」身上。於是我們更明白魯迅為何特別看不起那些看來有「學問」的「偽士」了;他們失去了主體,也絕緣於誠愛。
雖說「主體」是一來自西方的概念表述,但並不意味中國的思想傳統對這個概念的所指是陌生的。豈止不陌生,甚可說是核心的,只是不以「主體」之名罷了。儒家傳統裡的君子與小人之辨,講的就是主體。《論語* 魏靈公篇》「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所刻畫的不就是一種不為利誘不為勢劫、能學能守能固的「主體」狀態嗎?不妨這麼說,「君子」就是有主體性的存在,而小人則反是,無時不受外在條件牽引制約;難怪尼采曾指社會學是西方中產階級的腐朽(decadence)知識形式,因為它的核心關切就是人的被決定,以及以「掙脫被決定」為套路的「悲劇」。相對於薛西弗斯或是大衛的西方浪漫英雄主體形象,中國古人的「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中庸》)的主體形象,則又是一種什麼樣的境界啊!
回想起來,從1980年代到美國受訓社會學起,到其後長年的讀寫教學生涯中,大約能以2003-5年為一轉折點,從那兒開始慢慢的(甚至是在自己不甚了然的狀態下)對西方的知識背景與習性萌生出不足感乃至不適感。美國小布希政權的伊拉克戰爭對我衝擊很大,它扯下了1990年代克林頓政權長期經營的政治正確華麗外衣,顯露了污漬與虱子──以「科學」證據、「民主」之名,與沛然「民意」征伐小國,殘天下之民以鞏固「美國優先」。而那幾年竟然是民調中的美國人最以美國為榮的時刻──這能不讓人對「民主」之為物驚愕從而反思嗎?也是在那幾年裡,我在卑南族Kasavakan(建和)部落頭目哈古的言談身教下,從少數民族的命運與反抗中首度體會了「傳統」的意義與尊嚴;要知道,之前的社會學訓練讓我在「元」層次上就鄙薄「傳統」了。2005年北京訪學,2008年頃我重讀陳映真文學,後來又從陳映真順藤摸瓜摸到魯迅……回想起來,似乎都是懵懵懂懂地想找出反殖的、反帝的、具有民族主體性,同時能正視並敢於「拿來」自家過去與其他民族的優點,的一條出路。臨老學新步,這一路走來舊步難忘、新步維艱,而這本集子就是如此可憐復可哂的知識狀況的一個見證。好在總是還有幾位同行(xing)的台社老友相互證學,不至獨學無友。同時,也有幾位大陸學者,由於多少對我們這樣的知識狀況有所同情體會,願意承認台灣的朋友們所關切的「殖民」與「主體」問題從來不曾真正外在於中國大陸,而成為了知識上以及思想上的諍友。所有這些朋友,我們相視而笑莫逆於心,就不隨俗一一列名了。再會了,社會學,我曾經的名片、我曾經的逆旅,願你視此為我回報於你的一份小禮物罷。
《主體狀態:雜文散論於歷史、文學與社會理論之間》2024年7月,台北:台灣社會研究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