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蘇哲安為法國巴黎十大《跨領域多語研究中心》研究員,感謝作者供稿)
中國2022年11月所謂「白紙革命」爆發前,同年9月英國伊莉莎白王室太后葬禮舉行之際,反對王室體制的英國律師兼氣候活動人士保羅.鮑爾斯蘭(Paul Powlesland)在葬禮隊伍前舉起了白紙以示抗議,並立即遭到英國員警的盤問,甚至被「威脅逮捕」。隨後,以白紙顯示抗議的活動此起彼落,成為當時引起注目的小眾運動。不到三個月後,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傳媒似乎都已經把這個重要的先例拋諸腦後。連網路搜尋「白紙抗議」都不容易找到。此一事件的啟發,除了焦點經濟的特殊時間性之外,還凸顯了媒介的重要性。為了進一步瞭解這兩點,且讓我們先回顧一下英國那次的先例。
根據《觀察者網》2022年9月13日的中文報導:
其中有員警對其(鮑爾斯蘭)表示,若他在這張白紙上寫下「這不是我的國王」,有人「可能因此被冒犯到」,他會被以違反《公共秩序法》的名義遭到逮捕。保羅將現場與員警的對話拍攝下來,視頻在網上瘋傳後引發對警方的激烈批評,有線民嘲諷稱「員警是怎麼預測出他要寫什麼的?他也有可能寫『天佑吾王』啊」[1]。
警察的反應之所以有示範的意義,是因為它充分呈現了眾人面對白紙的一種普遍反應。作為化約定型的舉動,英國警察將兼具媒介與意象特質的白紙立即視為「文本」,進而在此預設上展開預防性(預期性)的「閱讀」。
/cloudfront-ap-southeast-2.images.arcpublishing.com/nzme/HJPNXD7TABZZ6ZM5UWXSZCG7PE.jpg)
同樣的邏輯就在最近這場中國「白紙革命」相關的國際輿論中不斷地被複製傳播。對於白紙的解讀,眾多評論者口徑一致,將其立即化約為「文本」,並且針對假設性的「文本」展開閱讀。就「文本」的具體內容而言,論者的看法也大致一樣,並分為兩種訊息。從牆內反抗這點出發,論者一律賦予「反對威權」的基本意義,進而將其解讀為一次表達「民主轉型」的訴求。甚至有海外華人,在「民主轉型」之餘還賦予涵蓋西藏、新疆、香港與臺灣等地「民族自決」的延申意義[2]。換言之,空白的紙張在「文本化」的強勢論述下儼然成為現代性「普世轉型」的範本。這樣一來,「白紙」頓時失去了意象與媒介的特異性與不確定性,並被「普世轉型」既有想像收編,成為十分熟悉、甚至是刻板的「政治腳本」。

假設將媒介與意象轉換為文本的舉動可以被視為一種翻譯過程一樣的話,那麼我們就更能理解隨後發生的第二種翻譯動作。以國際知名中國當代政治研究專家柯瑞佳(Rebecca Karl)教授的觀點來說,牆內的抗爭立即被牆外流離失所的華人社群擴大,而無論牆內、牆外,「他們都對於歐美『民主』的語言操作十分流利,並善於讓自己被世界所聽見與看到」[3]。如此的「流利」表達,通過柯瑞佳那樣將語言與區域搭上連結的預設,顯然就包含著潛在性的翻譯預設。而這兩種翻譯的步驟重疊在一起,隨即成為「普世轉型」的物質驅動力。短評結尾,柯瑞佳提問,「這些行動會不會像滾雪球一樣變成我們尚不知其名的東西呢?」,使得翻譯與轉型的腳本之間潛在性的連結獲得進一步的鞏固與強化。
此時最需要的,就是回歸白紙作為媒介與意象的本質,追尋一切「文本化」與「政治翻譯」動作發生之前的特異性與不確定性,以便還原當代「中國」走出一條無法預期,無法化約為固定腳本的道路。眾所周知,殖民-帝國現代性霸權論述當中,「轉型」佔有非常特殊的核心地位,以均質性直線式的時間觀,將世界人口分為「進步文明」與「落後文明」的兩大區塊,將時間化為地理空間,並點出從一個區塊到另一區塊「現代化」標準的道路。即使殖民主義衰微之際的今天,如此的霸權論述如同一具打不死的僵屍般在全球規模上出沒,讓知識解殖的任務顯得遙遙無期。此一困境的最佳寫照,莫過「自決」(self-determination)的解殖初衷被單一「普世轉型」論所收編,落為新殖民主義的利器。
說到白紙在現代中國的意義時,誰能忘記毛澤東曾經在1956年的講座上,將尚待發明的「新中國」及其新人種-「社會主義新人類」比擬為一張白紙。後人對於毛主席此舉的分析大半都強調其威權的含意,譴責這句話顯露的獨裁狂妄,就好比「中國人」為一幅空白的畫布專供獨裁者任意擺佈,畫出「專政」意志的恐怖想像產生出來的怪物形象—新中國的新人類。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係》的報告:
我們這兩條缺點,也是優點。我曾經說過,我們一為「窮」二為「白」。「窮」就是沒有多少工業,農業也不發達。「白」,就是一張白紙,文化水準、科學水準都不高。從發展的觀點看,這並不壞。窮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難。科學技術水準高的國家,就驕傲得很。我們是一張白紙,正好寫字 [4]。
毫無疑問,毛主席的想法表面上也是屬於現代化固定腳本的典型範例。作為「落後」的國家,「新中國」尚待發展的地方實在太多,甚至可以說是非常全面的,連「中國」本身都還是處於如同原料一般的初階狀態,需經過一番徹底的塑造過程,方能成實現。而規模如此龐大且深刻的任務,唯有恒常的革命是道。尤其在殖民主義支配與資本主義剝削的共伴效應下,手段除非很徹底,否則社會主義轉型成功的幾率就非常渺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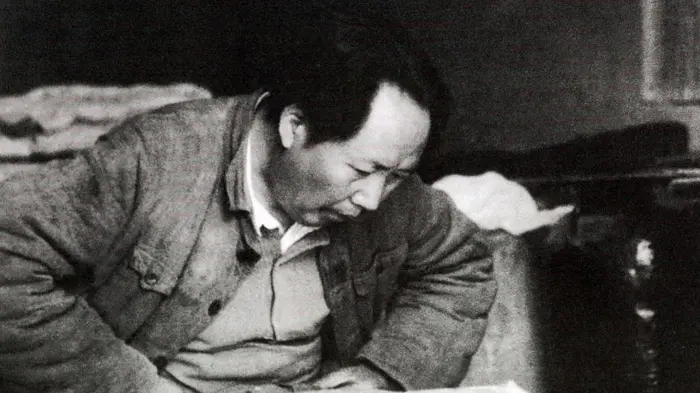
正因此,冷戰期間國際上曾經一般認為,毛澤東的立場等於是對「中國」文化的否定。用美國歷史學者周策縱的觀點來說,毛澤東思想從五四時期「文化破壞偶像」(cultural iconoclasm)模式繼承了對中國文化全盤否定的嚴重謬誤。周策縱這種論點容易導向一個歷史結論,將馬列共產主義及其整體性社會批判視為不符合「中國」國情的「外來」思想或勢力。然而,論者所理解的「中國」,其實不是別的而正是資本開始吸納社會關係,滲透到知識領域之後,通過「普世轉型」論述產生的標準產物。
美國學者謝牧(William Schaefer)在一篇討論張新民紀實攝影的學術論文中,對於毛澤東知名的「一窮二白論」提出了獨到的見解,衝破冷戰時期區域研究的局限。根據謝牧的觀點, 「一窮二白論」的重點取決於白紙作為媒介(medium)的物質特性。毛將中國人民比擬為「白紙」其實就是將他們視為一種媒介或載體,而所謂「窮」的含義,指的不僅是媒介上缺乏筆劃的窘境,而更是劃出新痕跡的強大潛能本身。對於毛澤東來說,人民與其說是一種處於「欠缺」狀態的被動對象,不如說是富有潛能的主體。謝牧特別強調,媒介作為媒介的特質在於它並非一個純粹單一的現象,而是具有物質的矛盾特性,可以同時起著傳達與過濾各種紋路訊息的作用。謝牧雖然並未論及翻譯與白紙之間的關聯,可是我們確實可以隱約感覺到,媒介如此「傳達、過濾」的特質本來就包含著明顯的轉譯契機。
謝牧對於「一窮二白論」的詮釋展開了錯綜複雜的辯證關係,在去疆域化與再疆域化之間遊走。然而,謝牧如此的精闢創舉似乎包含了超出毛澤東原意的成分。雖然毛澤東1956年「一窮二白」相關的表述最後以「寫字」收尾一事確實可以被視為一次與上述英國警察一模一樣的「文本化」動作,但是在謝牧的展論中,「寫字」行動之外,毛澤東白紙的隱喻還一直包含著影像圖本的另類契機。我們也不妨揣測,對於毛澤東本人──一位曾經受過部分傳統士大夫教育、書法藝術被後人奉為扭轉乾坤的重要作品的人而言,所謂「文」、所謂「寫字」,均超出了現代性「文本」的狹隘範圍,並自然包含紋路圖本的特質在內。畢竟,中國書法的特性本來就在於屬性的曖昧性,在「字」與「圖」之間呈現尚未歸類、反對歸類的特異性。謝牧對於毛澤東「一窮二白論」如此「樂觀」的詮釋不但容易理解—謝牧畢竟是一位專門研究視覺藝術的學者,而且還頗有洞見,將「一窮二白論」還原其特異性、媒介性與曖昧性:
毛的文本彌漫著視覺、文字與媒介等種種關係之間,懸而未決且讓人感到不安的精神,並且在窮困、占奪與當家作主的歷史脈絡之下,探討再現與自我呈現的諸般問題。[5]
離岸中國研究圈將美學與政治分開處理,自從第一次冷戰時代迄今一脈相傳,成為一種牽涉屬性分類的慣性原則。此時引用謝牧的觀點,正好可以協助我們突破僵局,從另類角度再思考政治空間裡被收編的特異性。怪不得,謝牧在文章的結尾特別強調,「拒絕簡單解決方案」的問題意識非常值得堅持。而這點恰好可以凸顯當代中國政治相關論述經常最缺乏的視野。「白紙」被立馬化約為「文本」正是這個現象的最佳寫照。
有趣的是,當中的欠缺現象往往跟翻譯有關。從中國到歐美、從圖本到文本、從影像到文字、從特異性到普世性、從藝術到政治,這一系列的轉譯過程在在叫我們重新思考翻譯與特異性的關係。作為一種將「不連貫性」轉換為「連貫性」的跨界動作,翻譯活動每每展開就是一次又一次特異性乍然浮現的時刻。然而,在現代性翻譯體制的支配作用之下,被大眾傳媒所壟斷的溝通機制,往往將翻譯所臨時曝露的特異性遮蓋並納入既有的再現範疇,成為固定腳本的複製品。正因此,對於解殖任務仍然抱有使命感的我們,更需要盡可能還原特異性被刪除的原貌。當前的中國人果真如同柯瑞佳所說那樣, 可以「流利操作歐美的民主語言」,這不但並不代表那是翻譯唯一的可能性,而且更加凸顯翻譯政治全面解殖的任務尚未達成,甚至是根本尚未啟動。
從這個角度來看,「白紙革命」剛開始燃燒的時候,中國政府試圖將矛頭指向「外來勢力」一舉也是頗耐人尋味的事情。就「外來勢力」的概念而言,毛澤東「一窮二白論」的原句其實本來就有所涉及。無論「窮」還是「白」,都是相對的概念,而其主要的指涉對象都是帝國主義列強國家。這樣一來,「白紙」注定與殖民-帝國現代性轉型中兩種矛盾的現象—「失語」與「邊界」搭上密不可分的連結。如今這種矛盾情結又被重新機活一次:一方面民眾拿著白紙表達對威權體制下失語狀態的抗議,另一方面國家當局力圖操作「境外勢力」論述,將自己的角色,無論是針對新冠病毒也好,還是對於民眾的抗議活動也好,都定義為邊界的捍衛者與英雄。
雖然雙方的立場一起構成了一個完整的論述機制,但是這也並不代表雙方的關係是對等的。對民眾而言,國家實際上永遠是一種「外來勢力」。說到此,我們就會想起義大利哲學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一篇寫在天安門事件一年後的政治哲學時事評論裡,將中國89年的抗議運動解讀為特異性政治勢力的抬頭。與主流評論不同,阿甘本認為「民主、自由」的訴求並不「具體」(specific),而僅能算是一種「類屬」(generic)式的概念。將訴求放在「類屬」的層次上對阿甘本而言就意味著一種新的抗爭主體儼然成形。這是一個脫離再現與認同政治的特異性主體,與「國家」之間形成了對立。然而,這種對立的局面,與傳統現代性政治哲學「社會vs國家」的格局不太一樣。重點是國家無法忍受「特異性」的浮現。而特異性的浮現不但衝破了認同政治的手銬,而且還創造了新的抗爭主體,為了爭取「類屬」的生存權而奮鬥。阿甘本該文的主張牽涉錯綜複雜的政治哲學脈絡,筆者在此無法充分展開分析與批評,而僅想拿來強調另類翻譯-也就是說忠於特異性的社會實踐的重要性。至於國家與「類屬性」之間的關連,這是一個非常深刻而晦澀的議題,最好謹慎處理。

然而,筆者還是需要承認,即使從翻譯的再思考與二元對立的解構等角度出發,最後結果未必就能達到特異性被還原的預期效果。〈生命政治二元論:如何避免對中國抗議浪潮的誤讀〉一文的作者盧貝爾(Nicholas Loubere)與索拉切(Christian Sorace),即使以二元解構與「逆脈絡化翻譯」(con-textual translation)等方法論為出發點,力圖建立全球左翼跨國視野,他們最後也難免重蹈為西方辯護的覆轍。該文主要的解構對象,乃是「西方論述」,特別是反疫苗社群的論述當中,有掉入中共大外宣圈套之嫌的傾向,將中國的清零政策與西方展開對比,建構出一組「假二元選項」(false binaries)。根據那些論述的觀點,以生命優先一切的中國政府的政策方針可以被視為一種珍惜生命的「生命政治」,而西方所施行並導致了光是美國單獨一國死亡人數超過一百萬人、平均壽命首次低於中國的「死亡政治」(necropolitics)之間,呈現鮮明的對比。然而,根據盧貝爾與索拉切,該二元組其實算是一種障眼法。中共政權即使嘴皮上標榜「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但是唯一真正想要延續其生命的對象乃為中共自己的政權。由此可見,中共在乎政治形象遠比真正關心人民生命還要重要。造成10人殘酷活活被燒死的烏魯木齊大火掀開了中共虛心假意的面紗,揭露了其真正的目的並非「生命至上」而是「保衛政權至上」的事實。
或許吧。然而,就正當性而言,何止中國,時不時被潛在的「正當性危機」所威脅的政府,應該包含世界上當前所有的國家無餘。自從德國哲學家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1973年《正當性危機》一書問世以來,正當性危機就被視為二戰後相當普遍的政治處境。當前世界上可以免除如此潛在危機的政府應該無幾。盧貝爾與索拉切真正的批評對象,其實就是西方國家內部從「反疫苗」到「新法西斯」的政治勢力。然而,與一般後/帝國自由派立場一樣,他們進而預設,國內反法西斯與國際局勢之間則形成毫無裂縫的統一戰線。也就是說,不存在任何有實質意義的邊界或翻譯的必要。
從這樣的預設出發,各種疏忽、錯誤與潛在共謀難免叢生。歸根究柢,論述歸論述,美國與中國死亡人數的懸殊落差再怎樣還是不能被化約為「假二元選項」吧。遑論,新冠長期的影響,特別對於免疫系統、T細胞與血管的負面影響,不但尚有許多尚待深入研究的地方,而且還構成統計上的嚴重挑戰。甚至新冠長期的禍害,可能最後無法確切評估。
還是歷史學者亞當.圖茲(Adam Tooze)的觀點比較踏實一些。在一篇發表於2022年12月2日的博客貼文裡,這位深信大西洋主義的資深學者針對「白紙革命」提出分析,提醒讀者不要因為習近平—這位牆外華人社群媒體喜歡戲稱為「總加速師」[6]的關係而陷入「幸災樂禍」心態的陷阱:
儘管反清零政策抗議活動很號召我們的支持,我們還是需要提問,政策上的選項何在?即使清零政策的解除對習近平構成一次的打擊也並不代表那是個正確的政策決定。北京所面臨的難題超出了習近平政權與政黨的問題。儘管清零政策已經顯得很搞笑,儘管對中國人民日常生活的侵犯太過任意與虐爆,它還是拯救了無數的生命。假設北京現在就棄守了這個政策,那就注定釀成不僅是中共而是整個中國的公共衛生災難 [7]。
圖茲較為理性的地方,在於他至少可以承認,中國當局所面臨的選項均不理想,甚至相當困難。從這個角度來看真正的「假二元選項」就是發生在中國清零政策的「生命政治」與美國任由肆虐政策的「死亡政治」之間被劃上道德等同關係,進而取消即使包含烏魯木齊大火在內死亡人數差距十分驚人的懸殊狀態。
更有甚者,盧貝爾與索拉切在呼籲左翼帶頭衝破「假選項」,展開全球跨國「正向生命政治」(positive biopolitics)之際,對於「全球疫苗隔離制」(global vaccine apartheid)中西方國家的關鍵角色始終沉默,隻字不提。
今年六月WTO達成協議,讓部分有資格的國家可以暫時免除新冠疫苗產權的限制。被西方領導人拿來充當政績炫耀的協議,其實是西方國家存心確保大型製藥財團繼續獲得暴利的騙局:
「富裕國家在世貿組織的行為是完全可恥的,」人民疫苗聯盟聯合主席馬克斯.勞森說。 「歐盟已經阻止了任何類似於有意義的知識產權豁免的事情。英國和瑞士利用了談判在傷口灑鹽巴,使一切內容變得更糟。美國一直在談判中保持沉默,抱著「紅線」去限制協議的任何影響。」
「這種所謂的妥協在很大程度上只是重申了發展中國家在某些情況下凌駕於專利之上的現存權利,」勞森補充道。「它甚至試圖將這種有限的權利限制在那些還沒有能力生產 Covid-19 疫苗的國家。簡而言之,這是一種旨在挽救聲譽而非生命的技術官僚招數」。[8]
根據 IPWatchdog (智財權看門狗)組織的分析,協議中將暫時免除智財權的權力限制在無生產能力的國家一事,純粹是西方國家專門針對中國,旨在排擠中國的條款[9]。
由此可見,積極阻止全球跨國「正向生命政治」因應措施的勢力,正是西方國家與財團的複合體,而並非中美之間的什麼「假二元」。
最後這點之所以值得再次檢討,正是因為氣候變遷這個重要性超出新冠疫情N千倍的議題。在未來的談判上,西方國家注定會反覆耍起同樣黑心的招數,世人對此不可不覺醒[10]。
盧貝爾與索拉切展開解構的動作,歸根究柢只不過是為自己去建立不在場證明的道德動作而已。他們瘋狂地誇大所謂「批判」知識分子的作用,好像他們的必要任務是為一個他們並不代表的且並不存在的國家機器「決定」正確的地緣政治路線。那種「扮裝真人角色遊戲」 自二十世紀初以來,對激進左派的國際主義造成了無數的自我傷害。更有甚者,他們利用如此的不在場證明,將自己定位在一處什麼地方都不是的地方(因此自然就有不在場證明),就好比要表明他們是完全獨特的後國家人類,根本不在某個特定的地方。因此他們幻想自己有資格呼籲他人去否定一切與國家具體權力有關的事情。 這種無處(因此無處不在)的幻想是西方假定統一聲音的一次完美表演,這些聲音通過如此勇敢的、後國家、後民族的「批評家」發表,方便地解除了西方對世界的任何集體責任。事實上,這正是北約詞彙中的一種標準論點:我們不是侵略者,因為在我們的世界觀中,凡是拒絕通過「普世轉型」去融入「世界秩序」者都是絕對邪惡的溫床,而由於世界秩序正由我們主導,所以任何背離這一點或試圖在霸權集團之外存在的行為都是絕對邪惡的表現,是犯案在場的證據,是真正的侵略行為,而為了剷除這些邪惡勢力,任何恢復秩序的必要暴力都是神聖的義務與特權。
假設說,疫情是世界大戰的排練,那麼從清零政策起,對中國展開絕對罪惡化的動作,乃是戰爭進入箭在弦上階段的預兆。
此時,還原特異性的翻譯實踐顯得更加重要。
註解:
[1] 阮佳琪,〈英國男子舉白紙被員警盤問:你要是寫「這不是我的國王」就逮捕你〉,《觀察者》,2022年9月13日,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2_09_13_657718.shtml。
[2] 参见Promise Li, “Socialists Should Support the Popular Resistance in China (社会主义者应当支持中国民众的抗议),” The Call (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面包与玫瑰小组的官方期刊), November 30, 2022. https://socialistcall.com/2022/11/30/socialists-should-support-the-popular-resistance-in-china/.
[3] Rebecca Karl, “China in Protest (抗議中的中國),” Positions Politics, November 30, 2022. https://positionspolitics.org/rebecca-karl-china-in-protest/.
[4] 毛澤東著,《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287頁),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marxist.org-chinese-mao-19560425.htm。
[5] William Schaefer, “Poor and Blank: History’s Marks and the Photographies of Displacement (穷而白:历史纹路与置换的摄影相片),” Representations, Vol. 109, No. 1 (Winter 2010), p. 6.
[6] 他們認為習的獨裁作風注定加速共產黨的潰敗。
[7] Adam Tooze, “Beijing’s Tragic Dilemma (北京悲劇性的困境,” Substack December 2, 2022. https://adamtooze.substack.com/p/chartbook-177-beijings-tragic-covid.
[8] Jake Johnson, “WTO Deal on Vaccine Patents Decried as a ‘Sham’ Dictated by Rich Nations, Big Pharma (世貿組織有關疫苗智財權的協議被詬病為富有國家與大型藥廠強加的騙局),” Common Dreams, June 17, 2022, https://www.commondreams.org/news/2022/06/17/wto-deal-vaccine-patents-decried-sham-dictated-rich-nations-big-pharma.
[9] Eileen McDermott, “WTO Announces COVID Vaccine Waiver Deal That Virtually No One Wants (世貿組織宣布幾乎沒有人想要的 COVID 疫苗豁免協議),” IPWatchdog, June 17, 2022. https://ipwatchdog.com/2022/06/17/wto-announces-covid-vaccine-waiver-deal-virtually-no-one-wants/id=149670/.
[10] 參見David Wallace-Wells, “What Vaccine Apartheid Portends for the Climate Future (疫苗隔離制對氣候未來的預示性意義),” The New York Times May 24, 2022, https://www.nytimes.com/2022/05/24/opinion/covid-19-pandemic-vaccine-climate-change.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