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0年9月5日(六) 14:00 ~ 17:00
地點:國家人權博物館——人權學習中心
主辦:人間出版社;協辦:國家人權博物館
主持:鍾喬(差事劇團團長)
致詞:國家人權博物館 陳俊宏館長
發言:
出版—呂正惠老師(人間出版社社長)
影視—黃志翔(列夫特文化公司負責人)
媒體— 張智琦 (苦勞網記者)
劇場— 賴淑雅(台灣應用劇場發展中心負責人)
口述歷史—許孟祥(白色恐怖口述歷史作者)
兩岸—林深靖(新國際傳媒負責人)
作者— 吳俊宏成大共產黨案政治犯
座談會紀錄:蘇品瑄(台灣應用劇場發展中心專員)
行政與現場布置:林春暉、杜韋樺

鍾喬(差事劇團團長):我是差事劇團的團長鍾喬,今天由我來主持新書發表和座談會,開始之前先和大家介紹,空間上希望用不是那麼嚴肅的方式,大家可以上台來自在地講;第二個是邀了各方面的朋友和不同世代的講者,希望透過發表會將1970年代的政治犯經歷,跨越世代表達出來。
首先,今天致詞的是陳俊宏館長。接下來有呂正惠老師,出版此書的《人間出版社》社長。接下來請到黃志翔,他是《列夫特影視公司》負責人,最近他們的電影受到很大的重視。張智琦是《苦勞網》的編輯和記者。賴淑雅是《台灣應用劇場發展中心》的負責人。這些年,因為轉型正義,很多年輕人用戲劇或電影表達轉型正義,她們所做的應用戲劇也在展開白色恐怖的田調和表演。接下來,是在做白色恐怖田野調查中,幫《台灣應用劇場發展中心》做讀書會導引的許孟祥。以前在《夏潮》、《政治受難者互助會》工作,從事相關白色恐怖田野調查。最後是林深靖,《新國際》負責人。
我和作者俊宏說,我們前面的來賓發言過後,他再發言,最後再展開QA,昨天晚上他和我通訊息,說他有重要的話要講,打算講三十分鐘。前面每個人講十分鐘左右,依你對這本書的想法,最後再請作者來分享。
館長上台之前,我稍講一下,我覺得這本書有兩個子題一個母題。第一個子題是關於作者講到的轉型正義,用他的語詞大概是說,人權平反政府做得還不錯,思想平反並未做到,這當然有歷史的原因。這些年,我工作的《差事劇團》提出,白色恐怖不是用西方的標準來看普世人權價值,簡化為將威權希特勒化,我們要談內戰、冷戰的歷史背景,才能將白色恐怖肅殺談清楚。
第二個子題,是七零年代的紅色政治犯,俊宏用苦命這個詞。我發現他蠻喜歡用苦命這個詞,可能和他的人生遭遇有一定相連;但,我覺得崎嶇或曲折比較接近,看他寫這子題後,我重讀陳映真在《東亞人權會議》的國家暴力座談上,談到七零年代左翼政治犯,是經歷雙重鎮壓後的思想荒蕪狀態。第一次是1930年代,日據時期的左翼運動被鎮壓;再來是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雙重鎮壓;而後才有後來是七零年代的紅色左翼政治犯。我覺得這是苦悶和曲折下,導致思想上的荒蕪,產生當年紅色政治犯的一些背景。在這個題目上,作者在書中談到左翼運動在台灣的整個斷裂,特別是他去到綠島的經歷,讓我聯想起陳映真在綠島遇見五零年代,例如:林書揚陳明忠等等的老政治犯,在島嶼上無人問津的狀態。35年前剛認識俊宏時,在《人間雜誌》,他就跟我談起一生受教於林書揚先生的經歷。
本書母題,透過溫鐵軍的重要著述,去討論革命、解放後的中國;前四十年社會主義階段和後三十年改革開放,這在台灣反共的情境下不,並非那麼淺白易懂的題目。溫老師認為;關於解放和革命初期的四十年,不能只是用社會主義集體生產或人民動員來看,它有國家資本主義性質在裡面。吳俊宏認為:這件事和他今天要講述統獨問題,相關左統派或統左派,為何在台灣社會變得弱勢有所關聯。他覺得在實踐上應該去表述,這也是當初這本書出版的目的。最後這個母題,聆聽他半個小時講演會更了解,我們就陸續開始。首先,請陳館長致詞。
陳俊宏(國家人權博物館館長):今天很高興能夠看到俊宏前輩的新書在這裡發表,幾年前偶然看到吳前輩在風傳媒發表的文章,我們碰到都會討論,之後他也陸續傳文章給我,讓我看到前輩持續關心台灣轉型正義的發展,看到今天這本書的出版,我很高興,特別選在國家暴力侵犯這些政治受難者的場域,轉換成一個新書發表會地點,特別有意義。
這本書我看完後有蠻多想法,第一篇讓我很感動,提到劉耀廷、施月霞、陳美虹,岳父岳母和自己太太的歷程。呼應中團長提到的,人權館這兩年也一直嘗的,台灣白色恐怖期間,特別是五零年代遭遇到國家侵害的所謂左翼社會主義思想平反的工作上,是否應該有更多的努力。我們也看到台灣在經歷過228跟白色恐怖歷程當中,這些左翼的年輕朋友遭遇到國家暴力的過程中,現在的平反工作上已有除名、除罪的過程,但如同前背書中提到,他們的思想平反還需要更多努力。他有一句話說,歷史終歸歷史,要平反白色恐怖的歷史,就應該回歸當時的情境,忠實的分析、詮釋,才能夠真正做到這一點。今年在綠島展出的是五零年代在叛亂犯的真相平反工作,這裡面其實有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透過展覽,邀請社會大眾共同來思索這個嚴肅的問題。
在書中也看到,台灣整個白色恐怖平反運動裡,政治受難者如何現身?過去經常在冤假錯案的敘事架構下看到他們的身影,事實上似乎無法充分展現當年這些政治犯面對國家權力的壓制過程,他們的能動性和抵抗的過程沒有被看見。
比方說我們透過訪問,了解到他們當年是如何在政府新生訓導處的這些管理及機制下,還可以相互學習讀書,不願意受到思想控制。俊宏前輩在書中也談到和林書揚、陳明忠在獄中相互學習的過程。所以如何把當年政治犯的能動性跟他的主體性透過忠實的歷史呈現而呈現出來。我想,這也是我們在推動轉型正義過程當中一個重要的工作。
書中也提到有很多俊宏前輩對於目前台灣推動轉型正義過程當中的一些看法,這些看法可能跟我們很多主流、政府在推動的一些路徑有些不同,所以今天也很期待前輩的分享,還有我們今天也邀請好幾位不同領域的朋友們,透過不同的角度來理解來分析,讓我們對於未來台灣在推動轉型正義工作能有更多元不同的一些視野。
所以今天代表官方歡迎大家一塊來參加這次的新書發表會,也非常謝謝團長,其實非常用心,這個我們光是籌備這件事情其實團長已經來過兩、三次,參與場地的規劃,當然我也很期待等下的分享,會非常充實。
鍾喬:謝謝陳館長的發言,以及主辦這次活動。接下來,這本書是由《人間出版社》出版,請呂正惠社長,分享對於出版本書的重要想法。
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社長):名義上是人間出版社出版,其實現在出版社沒錢,出版費用是作者自己出,說自己是出版者有點不好意思,以前有出過陳明忠的回憶錄,現在是特價期間,今天出席的人可以買三折免運費。另一本是綠島老同學檔案,一下就賣光,現在沒錢重印,講綠島同學如何受到陷害,講得非常清楚,主角非常有趣,他是冤枉,他關了十多年後變成真正的共產黨,被綠島同學教育,故事非常精彩。很可惜現在經費不足,先停一陣子再說。吳俊宏這本書其實講了十多年,到現在才出版,俊宏跟我大學同年,他讀成大我讀台大。那時候我說「你們寫我來出」,結果沒有一個人寫出來。等到我沒錢他們才說他可以自己出錢出版。
我現在看到我的大學同學,他爸爸是白色恐怖被槍斃的,過了好多年我才知道,我還有一個初中同學,他爸爸是鍾浩東,我透過藍博洲說我希望跟他見面,他大陸的大哥也想見面。白色恐怖在他心中造成很大傷害,他不想面對,拒絕跟他爸爸的朋友見面,他是我看到老同學後代最奇特的。還有一位是呂赫若的兒子,他長期怨恨他爸爸,不願意面對爸爸是共匪,後來慢慢接受,二十多年來都和我們在一起。
受害者有兩代,第一代是犧牲者,第二代是家屬,受到的苦難遠超過我們的想像。你從小被說你爸爸是共匪,怎麼有臉見人,鍾浩東的兒子72歲,他從幾歲就開始認受這樣的苦難。我認識的老同學後代,他們自己講都很難過,極少數父母會教育,孩子心態才比較健康,像是陳明忠的孩子。
怎麼正義?怎麼轉型?這沒辦法賠償,不能重新給他們一生。大時代政治環境,思想的高壓對於人性的壓迫,導致很多人沒辦法訴說內心的痛苦,這種事情不只有台灣。應該說在二戰結束,冷戰的態勢,白色陣營鎮壓紅色陣營,像台灣、南韓、希臘、印尼,全世界都有。冷戰之後形成兩大陣營對立,從生活上來講,成千上萬的人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南北韓被劃斷後,開放探親時,在南北韓的家人雙方抱得哭哭啼啼,只有那天才能見面。
這比兩岸還殘忍,我們要考慮政治立場對立對老百姓造成無限的傷害,這跟老百姓有什麼關係?很嚴重到現在還是這樣,老百姓只是生活,怎麼會知道白的、紅的,這是全人類最大的悲劇,我們要考慮的是這個,必須站在人的立場去考慮我們如何去面對。
這個東西之上,還有更大的,我們怎麼面對莫名其妙捲進去的妻離子散的家人。我們要留心的是那種說不出口的民間故事,這種苦難才是無法補償,甚至到第三代都無法,這是我喜歡看書的長期感嘅,希望大家從人的立場多多考慮這些無辜的受難者。
鍾喬:從人的觀點談到意識形態,一般而言是重要的出發點,當然我們也要談論到意識形態的問題,冷戰的這件事,歷史要讓我們有得以反思的機會,從過去看到未來,溫鐵軍最近談的是舊冷戰、後冷戰、新冷戰,新冷戰透過金融資本,美國以中國作為首要敵人。回到過去冷戰的國際格局裡,吳老師說當時冷戰發生時,比熱戰還不理性的是,很多事情在你眼前發生是不講道理的,譬如最近美豬的事情。
黃志翔(列夫特文化公司負責人):我跟俊宏是921認識,當時在災區工作,多半是在左翼朋友聚會場所,在興高采烈談左翼如何重建的場合認識。他給我的印象是非常謙遜的人,後來陸續在網路上或微信的群組上看到他的文章和評論分析。我看到的許多像吳俊宏一樣的前輩,一輩子像苦行僧一樣默默、堅定地實踐理想,包括投身社會與政治運動,也包括不斷思考與評論解析身處的世界局勢。在這本書裡面,我看到的是一個特別篤實、像苦行僧一樣的左翼工作者,70幾歲都還敏於思、敏於學,對我們這代人來說,尤其值得敬佩。
這幾年流行一句「碎片化的時代」,我的工作與媒體相關,尤其深切感受這種情境,碎片化的結果,往往演變成所謂「後真相時代」,謠言滿天飛,似是而非、顛倒黑白,針對轉型正義、左右、世界局勢、台灣島內、香港、大陸等議題,常常充滿似是而非的論述,看到俊宏兄非常堅持,用自己的閱讀和學習寫出這本書,用紙本的方式出版,讓那些因為碎片化而逸失的真相、真理得以結晶,整體化、凝結化。
這幾年,台灣影視、文藝圈有些創作者開始把轉型正義當成寫作題材,似乎把政治受難者視為某種抽象的弱勢者、受害者,這種創作思維,像東方主義一樣,揭露種種白色恐怖事件的同時,作品本身卻成了獵奇的欲望,創作者並不理解左翼政治犯及其思想與歷史脈絡,又如何能夠真正觸及他們的生命處境?轉型正義的議題原本應是內在於人民與土地的歷史記憶,在那些作品中卻異化成為陌生的他者。
相比之下,吳俊宏的作品非常特別地標志出一代革命者的形象,他從庶民的、實踐的、歷史的、政治經濟的觀點求索這個時代的困惑與迷局,以此而論,《綠島歸來文集》這個作品就足以在人民的歷史巨流中為我們留下一個彌足珍貴的航標。
鍾喬:碎片化、把歷史當作他者、當作創作題材,影視比劇場更敏感到這件事,影視背後是工業、錢的事情,透過作品能否有市場,是這個行業的殘酷性。列夫特最近做的無主之子技能在藝術性表達,在主題上仍能抓住結構性的問題,他也是用他的方式在做抵抗碎片化這件事。接下來是代表媒體的張智琦,或許可以跟我們分享媒體的挑戰性,這個世代怎麼面對電腦、虛擬世界。
張智琦(苦勞網記者):我和吳俊宏大哥已經認識一段時間,經常在採訪互助會的活動見到吳大哥,吳大哥年紀不小,還是持續關切白色恐怖議題,參加反對《國安法》、反對《反滲透法》等運動。最初認識吳大哥,是因為2015年桃園縣新世紀愛鄉協會有辦一個吳大哥的講座,叫做「年輕人,你知道什麼是白色恐怖嗎?」,我雖然沒有到場參加,但看完上傳到網路上的影片,當時我對白色恐怖一知半解,都是參照網路上破碎化的論述,而講座上吳大哥細緻深入地談白色恐怖的本質和來由、台灣白色恐怖的三個歷史時期的分析,讓我對白色恐怖有整體的全面性了解。
我過去也在《方向》叢刊讀到吳大哥的〈永不開花的枯葦〉一文,這次也收錄在新書中,我讀了也深受感動,對白色恐怖有了比較感性的理解,了解到原來白色恐怖家族的受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現在很流行白色恐怖的家族史書寫,我認為這篇文章可以說是白色恐怖家族史書寫的一個典範。
吳大哥的新書可以說是一本解惑之書,一般人不了解台灣白色恐怖的歷史,或者可能對中國大陸有妖魔化印象,都可以從這本書得到不同的理解。這本書也顯示出大哥的確是一個具有唯物史觀和人民觀點的馬克思主義左派,例如他會用經濟基礎分析中共為什麼要搞一些政治運動等等的,其實是跟當時國家要推動工業化有關係。對於白色恐怖,吳大哥也提綱挈領地定義為:「一個反動的國家政權對起而反抗革命人民的鎮壓行為。」
吳大哥也談到對於白色恐怖的認識,並不能侷限在台灣一島範圍,例如吳大哥將白色恐怖回溯到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清黨」屠殺共產黨人,這其實就是因為在中國內戰的背景底下的階級鬥爭、國共對抗,產生了白色恐怖。國民黨遷移到台灣來之後,繼續在50年代清剿台灣的共產黨人、左翼同行者等等,所以這是延續性的。這讓我們看到,只有放在中國或更大世界性的範圍才能真正理解白色恐怖。
很多人說50年代的政治犯是「匪諜」、共產黨人,不需要同情,但吳大哥就有力地反駁,說他們是「台灣民主運動路上的第一批烈士」,這對現在的民眾來說是一點就通,他們那時候做的事情是希望能改造社會,就和現在很多抗爭者抱持的理想是一樣的,吳大哥書中突出了當時的白色恐怖受難者的革命理想,而非只有悲情的一面。
在轉型正義的部分,吳大哥也提出很深切的檢討,比如說現在是蔡政府執政,那我們到底要怎麼去面對過去「親共親中」的政治犯?有沒有更多的書寫或展覽?
我覺得現在在高雄勞博館展出的「郵電案」展覽是個很好的範例,這個案子也發生在50年代,是一個很典型的有中共黨人涉入的案件,當時郵電員工在行政院遊行抗議,爭取同工同酬的權利,同樣也是工人抗爭一部分,這個展覽就是正面去評價這個事件,不去扭曲這段歷史,我覺得就很好。或是說像六張犁公墓這個地方,我知道現在在做白色恐怖人權遺址的規畫,台北市文化局等單位正在做一些像是修整草皮、建步道,做告示牌的工程,其實就會有涉及歷史詮釋的問題。重要的是,我們到底要怎麼還原六張犁墓區的歷史?能不能不去迴避那邊埋的多數是中共地下黨員,不迴避他們是左翼的立場,如果能夠如實的呈現這一點,我覺得就會比較偏向吳大哥所談到的史觀。
讀這本書也讓我想到,南韓白恐政治犯徐勝的《獄中十九年》一書,徐勝是1971年入獄,成大共產黨案是1972年,我覺得很可以相互參照,當時徐勝在獄中會見了一批50年代被關的政治犯,就跟陳映真、吳大哥入獄後會見了50年代的林書揚那些人,受到了思想的刺激和啟發,非常相似。吳大哥提到林書揚寫紙條給其他政治犯,傳遞社會主義思想,徐勝也同樣提到在監獄裡學習了50年代政治犯的理論、風骨和人格。
值得探究的是,南韓有嚴厲的思想轉向制度,分成「轉向政治犯」和「非轉向政治犯」,徐勝是非轉向政治犯,也就是屬於不屈服於南韓政權、不願放棄共產主義思想的政治犯。我好奇的是,台灣雖然有像吳大哥講的這種思想教育,國民黨同樣要求改造思想,可是好像沒有這麼強制、暴力性的要求做思想轉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異?
我自己的想法是,是不是因為,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時候,本來就有一套對付共產黨的方式,比如說他是全部抓起來,基本上殺掉所有幹部,到台灣也延續這樣的方式。徐勝則講到南韓的轉向制度,是來自於日本帝國主義統治朝鮮時成立的,日本殖民者把殖民地朝鮮追求獨立解放的抗爭者抓起來後,要求他們轉向,而南韓政權實際上延續了轉向制度,但台灣在國民黨接收之後,就不再延續這樣的制度。但是不是這樣就比較不暴力呢?或者是因為台灣是因為50年代的重要人物都清光了,所以也沒有必要再去強制轉向剩下的政治犯?我想聽聽看吳大哥怎麼去比較台灣跟南韓的白色恐怖。
鍾喬:從歷史上理解,東亞從冷戰階段,在亞洲印尼1960年代的左翼肅殺是100到200萬人的狀態,我們很難以想像。如果我們仍然以獨裁政權的法西斯化,完全無法說服冷戰背景的影響,導致的大肅殺。印尼當時的肅殺一直到現在,十來年前,有紀錄片工作者去拍片的時候,一般市井小民還是認為共產黨不是人,而是妖魔的狀態,固殺之無涉罪刑。反共宣傳的深入,如此可見一般了。
另外,南韓搞劇場的朋友,在朴槿惠政府時代,只要講到「歲月號」沈船事件,情治單位便從背後監聽,可以用國家安全法控訴和北韓有關係,也是亞洲反共宣傳直到今天的案例;左翼聯盟前陣子很關切新冷戰在台灣發生的趨向;就作者而言,透過溫鐵軍的角度,也希望能從亞洲新冷戰的視野,在民間展開一些反思與批判工作。
接下來介紹賴淑雅,她和我一樣做民眾戲劇,這些年以應用戲劇,帶動一般民眾透過戲劇工作坊登台演出,也做外籍勞工的議題,今年展開白色恐怖的議題。請她分享怎麼樣碰到年輕人,及年輕人對轉型正義與白色恐怖的體會與理解過程。
賴淑雅(台灣應用劇場發展中心負責人):我在1993年演出陳映真的報告劇《春祭》時,第一次接觸到白色恐怖議題,那一年正好六張犁公墓被發現,在鍾喬的帶領下對白色恐怖歷史有了一些學習,但還沒太深刻的感覺。二十年後我自己的劇團裡,每年都有大專實習生來實習,也招募了青年團團員,都是二十多歲的年輕人。我遇到的困境是,在重大社會/政治議題上很難跟年青人真正展開對話,因為台灣長久以來的反共教育,對中國大陸、共產黨的妖魔化已是常態,而我過去的學習經驗讓我認知到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的影響其實一直延續到我們現今生活中,我會以不同的角度去理解現今的兩岸關係、中美關係、乃至全球局勢,但年青人無法如此,因為現今台灣社會很民粹,他們缺乏從更大結構認識白色恐怖歷史、延伸認識台灣政治經濟等議題的機會。
另一方面,這幾年政府推動轉型正義工作釋放很多資源到民間,很多劇團因為這些資源而開始做白色恐怖議題的表演創作,也讓我思考如果我們要做的話該如何做?該如何把很難跟年青人展開真正對話的困境一起放進來思考?我無法為了消化資源而迅速做一齣戲,我需要累積很多內涵和對話去建構戲劇,於是我們啟動了一個關注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歷史的三年劇場計畫,叫做〈幽噤的聲音〉。第一年我們只做兩件事,第一件事是請許孟祥規劃一系列讀書會,讀書會成員就是十多位我劇團的年輕團員,在四個多月的閱讀討論過程中慢慢打開對於那段歷史大結構而客觀的認識,而不是依從主流白色恐怖論述強調的冤錯假、被逮補關押刑求的悲情敘事。我們透過每週至少一本書的閱讀量,去認識和反思如何從雙戰結構的脈絡去理解當時為什麼發生白色恐怖,加害的結構長什麼樣子?在從台灣延伸看見東亞具有反共的共同歷史背景的其他國家遭遇,最後回到白色恐怖影響下的學生運動及原住民自治運動的被迫害歷史。
這個過程四個多月下來,我的年青團員不經意說了:「共產黨好像沒那麼壞」、「我開始懷疑我是不是也有共產主義的想法了?」,他們的腦袋開始鬆動,這個打開認識的過程很重要,這讓我知道應該再跟這些年青人展開更多的學習,再繼續往下走。
〈幽噤的聲音〉計畫今年要做的第二件事是,用應用戲劇的方法培訓中學老師,跟老師們一起探索如何在教學現場進行不一樣的歷史教育,如同我們過去用同樣的手法跟老師們做移工、性別、精障等議題教學一樣,我們覺得教育現場是一個機會、一個空間、也是一個戰場。轉型正義除了政治平反之外,思想平反這一塊,現在顯然是相對薄弱的,我覺得站在教育第一線工作的這些老師們很有機會做這件事情,尤其是在一〇八課綱開始實施之後,制式的課程規範已經比較鬆動,老師有相對多一點空間去做這件事情。現在一〇八課綱的歷史課本裡談白色恐怖的部分只有兩頁,老師們除非自己去再去進修學習,不然談白色恐怖真的非常侷限,所以我們就通過一系列的戲劇工作坊,培訓兩批中學教師通過劇場的手法,怎麼跟他們的孩子展開對於白色恐怖歷史的更多認識。目前他們正在設計戲劇教案的階段當中,總共分成四組,分別以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時期的四個典型政治受難人為案例來發展戲劇教案:鍾浩東、黎子松、許金玉、林昭明。
在師資培訓的過程中,有一個值得一提的小故事是,桃園高中的一位公民老師問我們一個問題,他說:「我們知道在台灣發生白色恐怖之前,全世界各地就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思潮,到了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發生之後,東亞第一島鏈國家成為反共堡壘,這些東亞國家是不是因為都有反共的共同歷史經歷,所以雖然他們現在已經民主化了,可是他們的國家(包括台灣),並沒有發展出以勞工為主體的政黨,不像歐洲發展出親資本家的政黨,也有相抗衡的勞工政黨?」
公民老師的提問,說明了他對白色恐怖的認知已非常深刻,也反思到白色恐怖時期對左翼人士的撲殺對現代政黨政治發展的影響,但像他這樣的老師畢竟是少數,因為一般老師們所處的教育結構讓多數老師沒有機會和資源進行這樣深刻的歷史認識及反思,這也讓我們明白這樣的培訓工作必須繼續進行下去,希望像他這樣的中學老師可以越來越多。
剛才我分享的工作經驗正好也連結到吳俊宏大哥的新書對我的啟發,其一是左翼思想在白色恐怖時期被砍斷,沒有傳承到台灣當代社會,是斷裂的;其二是造成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歷史的冷戰意識型態一直還影響著我們現代的社會生活,我們應該通過認識這段歷史,重新認識台灣、重新認識美國、重新認識中國大陸,這也是我可以帶給我劇團的年輕人以及我所培訓的老師們的思維。最後,關於吳大哥在他書的第二章講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與歷次危機的內容,對我來講的收穫很大,這也是接下來我們的讀書會下一個階段的重點之一,就是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去展開對於台灣近代政治經濟發展的重新認識,我們希望用這樣的方式,讓我們的應用戲劇工作做的更扎實,以回應我們所處的現代社會。
鍾喬:淑雅的工作很實在、有很多反思,新冷戰重新在台灣,再產生舊冷戰的影響,在政治操作上會越來越清楚。民間上有這樣的戲劇工作、媒體工作、文化工作對年輕人影響的重要性。
另外一件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冷戰構造的歷史,1993年,年輕團員後來很後悔,他當時和陳老師聊天,說你好像在講一些教條。這是對於歷史的完全空白,這種空白一直在重複,讓我有很深的感觸。在80年代人間雜誌認識陳老師,都是從結構層面去看社會階級問題,是這樣的世界觀。但到了90年代後,你忽然發現參加座談會的時候,你不先開始說,我是異性戀者、我是一個爸爸,不先從性別看的話,好像在場的人都不是太有興趣。面對年輕人需要先有個小鑰匙,再打開大鑰匙的對話性比較高。
許孟祥(白色恐怖民眾史工作者):我是在2013到16年期間,與一群年輕夥伴參與了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為展開的兩個階段的白色恐怖受難人口述歷史調查。對象包括1950至1970年代的白色恐怖受難人及家屬。團隊在2015年曾經就「成大案」訪問過吳俊宏大哥。這期間有很多難題需克服,團隊裡面多是1980以後出生,到90後都有。也在這樣的工作過程中通過讀書會、座談或展覽等形式,與中學、大學的年輕朋友們有了或多或少的接觸。明顯地,大家對近代以來包括台灣在內的兩岸史認識不一,相當零碎,更年輕的甚至已經不大曉得歷史上的台灣光復是怎麼回事。中間有很多需要共同學習和克服的問題,特別是1950年代白色恐怖歷史的內容以及質因。畢竟,只有搞清楚究竟在什麼樣的歷史條件中,導致了白色恐怖肅殺的發生,才能說明當下人們關注的「人權」問題是怎麼產生的。
吳大哥的這本書分成四個部分,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苦命中國的崛起之路、統獨與民主、左翼與帝國主義。這樣的書寫或說關懷、實踐,讓我產生一種親切感。我跟夥伴們訪問過1950年代的老同學,發現他們幾乎不重視談自己的受難遭遇,而是將生命經驗鑲嵌在客觀歷史的進程和結構裡去表達。吳俊宏大哥的書寫與實踐基本也是這樣的。這跟當下台灣白色恐怖人權敘事多半強調受難與悲情的內容有很大的不同。受難經驗並不是不重要,而是說應該還有別的,那些他在受難前的主客觀遭遇、思索、行動等等。好幾次,我聽他們做如此的表達:「我的一生經歷日本殖民統治、台灣光復賦歸祖國、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肅清……。可以說,我們是內戰的受難者、見證者、行動者」。這讓我想到,島內很喜歡談大寫的「台灣人」,那麼時代典型遭遇下的典型「台灣人」究竟是怎麼樣的?在1950年代受難前輩的身上,其實已經體現了這樣的典型性,並且正待當下的人們反思與面對。
大約是2013年,兩岸情勢不較現在那樣對立。有個白色恐怖犧牲者的家屬從大陸來台,在六張犁亂葬崗苦尋父親的遺骸。我們沿著小徑上山,沿路還有不少寫著「平價撿骨、運回大陸」的殯葬業者廣告。他果然在亂草堆中找到父親的墓碑,但是挖掘了半天只挖到犧牲者的假牙,什麼都沒挖到,殯葬業者賣給他一個要價不菲的骨灰罐,他就把墓石邊的泥土放到罐子裡,當作對父親的思念。當天,一旁還有另外一個不認識的陌生中年人,拿著一疊彩印的資料,說是亡者的埋葬證明。裡頭果然有一張這名犧牲者的資料,陌生男子問大陸家屬:「一張1500元,要不要?」因為挖掘不到父親的遺骨,又由於他的大陸身份,檔案局也以礙於法規為由將他拒於門外,什麼都資料都拿不到。除了一座墓石,一顆假牙外,所有關於父親的消息就這麼斷了,他終於還是買下了這麼一張要價昂貴的影印資料。大家想想,六張犁亂葬崗上究竟埋了哪些屍骨?從1993年現場被發現至今,二十七年過去,除了受難人自己的統計以外,官方讓我們知道「真相」了嗎?
還有一次,趁著連假到屏東潮州探望一位年屆80的忘年之交。他是政治受難人的家屬,但是他也被官方「礙於條例規定」不承認他父親的受難身份。每次見面老人家都要問,有沒有查到他爸爸的資料,不斷地追問「我爸爸為什麼要死?」進一步了解才知道,他的父親在1950年代白色恐怖肅清中,歷經特務兩年的圍捕,最後在萬丹的蔗園裡自殺身亡。當時的報紙用斗大的標題報導:「匪諜江某某畏罪自殺,死時一身新裝,期待來世重新做人」,過不了多久又用來當作反共教育材料出版以「警世」。1998年官方公佈「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他沒有資格申請補償。官方告訴他,你爸爸是自殺,沒有經過司法程序,不是「補償條例」意義下的政治受難者。今天在場的呂赫若先生公子呂芳雄也有同樣的遭遇。
近幾年,台灣社會從官方機構推廣到民間,談人權、談轉型正義,實行的邏輯與基礎幾乎是以1998年公布的補償條例為前提,也就是說還僅僅是在「司法不法」的層面上處理這段歷史,這個吳大哥的書裡也有詳細的論評。剛剛舉的幾個普世人權價值照耀不到的例子,只是要說明,吳俊宏大哥這本文集的結構安排與內容思索,恰恰與上例一樣,在揭露一個長期以來的聞共色變的社會不願意面對的問題,也就是1950年代白色恐怖或者某種以反共為前提的「戡亂」,是內戰/冷戰的歷史帶給兩岸民眾的悲劇,它直接涉及兩岸的近代史。若不直面究竟這個延續到當下的「敵我」關係是怎麼形成的,卻只在這個島上談人權或者轉型正義,那必然如上述的例子一樣,所謂的正義怎麼轉都轉不到這些當事人身上,台灣社會也就沒有機會突破歷史遺留的保守的意識形態網罟。因此,怎麼樣把這個歷史放到中國的近現代史上去談,去重新認識,繼而找到前進的方案?我想這是我參與口述史工作以及在吳俊宏大哥的思索中得到的最大收穫。
鍾喬:十幾年前去光州,他們當時針對光州事件的受難者,把小的墳遷移到更大的墳,這都是國家、政府在做的事,這裡面也不只是光州事件,是對整個運動以來的犧牲者進行完整資料建構。他們有一種說法非常觸動我,「就算我們對於紅色政治犯有平反(實際上沒有),就算在韓國有全面的追思平反,但是韓國的後代人、搞運動或搞文化進步的人,認為其實不是我們透過這些事情來招喚他們,向殉難的人的過去,是他們在招喚我們。」那裡面有更深刻的意涵讓我們感動。
林深靖(《新國際》召集人):恭喜俊宏出書,《綠島歸來》這個文集將是許多關心白色恐怖年代者的重要讀本。詩人導演鍾喬給我題目是要我談兩岸,不過,今天主角是俊宏,談起兩岸議題,會有說不完的話,肯定偏離主題。我就只談跟本書作者吳俊宏有關的。
俊宏跟我的關係,首先是戰鬥上的「同志」。2018年5月5日,馬克思誕辰兩百週年,我們與一大群朋友,就在這一天於台北成立了「左翼聯盟」,因此,我們是在社會主義的路線上一起奮鬥的同志。
不過,與俊宏的淵源可能得從30、40年前開始談起,某種意義上俊宏是我們的「媒人」。鍾秀梅高中畢業,在台南準備考大學,偶然間在書店看到《夏潮雜誌》。她高中時就喜歡閱讀俄國十九世紀的小說,夏潮雜誌的內容觸動了她的一些想像,就打電話到夏潮,問要如何訂閱。哪知道,很快的,沒過幾天,就有人搬了一整套《夏潮》到台南給她閱讀,而且,就直接贈送了,不用買。這對一個窮學生而言,該是如何的感動!於是,一個17歲的少女就這樣被改造了,也因此,在多年之後,成為我的「同路人」,在運動的路上攜手前進。再後來,攜手變成「牽手」,同路人最後成為同床人。
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俊宏在某種意義上,就是秀梅和我的「媒人」。照理說,應該要包「媒人禮」的,我們當然沒有,但是以另外一種方式付給他媒人錢了。大家都知道,俊宏被送到綠島坐牢,他的案子就是「成大共產黨案」。當年,他們幾個好學又好奇的成大學生,從成大圖書館偷出英文版《資本論》,相約到烏山頭水庫中的小島偷偷開讀書會。這個小島,秀梅和我以及井迎瑞最近還試圖去探勘。老井在台南藝術大學擔任過音像學院院長,學校就在烏山頭水庫旁。秀梅後來到成大教書,我們也做了一些努力,為「成大共產黨案」平反,促成校方把過去不敢提、拒絕提的政治案件列入校史。俊宏當時沒畢業就被抓去關了,成大校長後來親自頒發給他畢業證書,而且,很優惠,沒有要求俊宏回學校補修學分!
此外,這本書的第一篇「永不開化的枯萎」首發是在我負責主編的《新國際》,那是在《立報》還發行紙版的時候,《新國際》是夾在《立報》裡面的週刊,專門報導國際左翼的思想動態。當時,我們用了兩個完整的版面,刊登這一篇動人的文稿,我還特別要求要編輯部把俊宏提供的老照片以最清晰的方式,附帶圖說印出。《立報》停刊之後,《新國際》以網路版的方式繼續存活到今天,俊宏傳給我的文稿,我也會轉傳給《風傳媒》的總編夏珍,爾後,俊宏也成為時常在《風傳媒》發表文章的寫手。
這本書包含四個主要篇章,第二個篇章裡,俊宏多次提到溫鐵軍的著作對他的啟發,尤其是有關八次危機的論述。而俊宏認識溫鐵軍,是我介紹的。多年前,長居北京的溫鐵軍應邀到台大開會,他打電話找我,我就約了幾個朋友,在台大校園的石板凳上,共同聊了一整個下午,俊宏就是其中之一。這是俊宏首次認識溫鐵軍,也開始閱讀溫的著作。俊宏在政治經濟學方面的開闊視野,與此多少有關。
溫鐵軍在國際上有一定的聲望,我們多次在海外碰頭,普受敬重的左翼經濟學家薩米爾‧阿敏(Samir Amin)生前在委內瑞拉召集過一次國際會議,溫鐵軍和我都應邀參加了,也一道見過當時的委內瑞拉總統查維茲。
聯合國開發計畫總署的駐華代表羅黛琳說過:「溫鐵軍是個用腳做學問的人」,又說,「政策研究必須基於與基層民眾在一起工作得來的實踐經驗。」俊宏也是這樣實踐的,也很重視和基層朋友在一起,他在書裡談韓流,就是在闡釋從「艱苦人」,從勞苦大眾出發的理念。溫鐵軍常強調「不積涓滴,難以成江海」,俊宏也是勤勤懇懇,一點一滴去做,一個一個去連結群眾,包括一字一句的寫作。
俊宏這本書的第三個篇章裡,有一篇是跟李敖的通信。這篇通信反映了台灣對於統獨問題的特殊觀點。很多人認為獨派不敢真正搞台獨,主要是怕戰爭,怕中國大陸打過來。俊宏卻指出,台灣社會內部真正的危機是道德危機,心性上就是自以為是,看不起大陸、鄙視大陸,這其實是做為人的「品格」出了問題,這種心態不改變,兩岸潛藏的危機就不可能去除。李敖的回信在書裡的第226頁,他很感謝俊宏的評論,不過,李敖也指出,在台灣生活久了,看多了,他已不敢向云云眾生要求道德面,台灣基本上就是是淺碟的、現實的、短視的社會,人也就變成這副不堪的德行,因此,無法談道德,只能曉以利害。從兩人的對話裡,可以看到俊宏的理想性格,他對於人的道德面有比較高的要求。
最後的篇章談到左翼與帝國主義,其中有一篇題為〈台灣左翼當奮起!〉,這其實是當時我們共同組織「左翼聯盟」時的內部閱讀文件,俊宏執筆。在台灣,要真正深入談兩岸議題,很困難,因為整體台灣社會十分缺乏對社會主義的了解,也缺乏對中國革命的認識。沒有這些基本知識,很難開展兩岸之間實質的對話。
其實,比較務實地說,所謂「兩岸問題」其實已不存在,我們說「兩岸問題」,那是因為過去彼此之間還有平等對話的空間,兩岸是對等的(此岸/彼岸),於今,在國民黨遲鈍、民進黨遲誤的境況之下,「對等」的概念已逐漸消逝,往後,不再有所謂「兩岸問題」,只剩下「台灣問題」。所謂「台灣問題」,就是北京當局單方面要面對、要解決的問題,台灣本身自行棄守話語權。
這樣的處境,對於台灣的左翼,對於像我們這樣對社會主義用心,對中國革命有情感的人,是很大的考驗。或許,只能引用俊宏書中的最後一句話:「時機稍縱即逝,左翼此時自當奮起」!
鍾喬:剛剛講到溫老師用腳做學問的人,某一部份來說深靖也是這樣,他是一個讀書寫作並行動的人,和作者有很多相互學習的地方。我們該怎麼在汙名化的這個狀態下,在反共反中的這個歷史的背景下,仍然能夠展開世代對話,是很重要的,是這場新書發表會的構思。那麼,最後,便請作者現身說法。

吳俊宏:作為一個作者,要講的東西其實都在書上。要講三十分鐘其實有點後悔。首先感謝館長,很有民主風度,上次提到我出了一本書,要在這裡辦新書發表會,馬上很支持,我說我們政治立場不太一樣,館長說沒關係、大力配合,非常感謝。其次感謝主持人,幫我設計這麼有情調的空間,感覺好像很風光,我這一生從來沒這麼風光過。
書名叫做《綠島歸來文集》取這個名是我去過綠島、學過政治經濟學,才寫得出這些文章,原本想找人請教有沒有比較好的名字,找不到人,我就這樣取名。這本書本來是應互助會二、三代的人要求集成的,因為我感覺我寫這些文章不是什麼大學問,不好去對外宣揚,但政治受難人後代要我把他集起來,比較能系統地來讀。
書中分成幾個單元,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這應該是一個政治受難人二代最基本應該了解的,我們那些二代還很多不太了解。其次他們也不太認識中國,不了解當時他們父母為什麼那麼喜歡中國。再者台灣台獨運動是怎麼樣的運動,我寫的是本土有錢階級的階級運動,不是一小撮人的,所以會發展起來。最後是帝國主義,必須了解資本主義怎麼發展,如何具有帝國主義的本質,必然走向帝國主義的對外侵略,我覺得二代應該了解這些。所以我就結集成書出版。
我想就從書裡比較不容易懂的地方講起,如從溫鐵軍的觀點。溫鐵軍的「八次危機」一書讀起來很難讀,它的文字比較學術。我當初看了覺得有些觀點很重要。我記得夏天的時候太熱,我家沒有冷氣,我開車到山上一個拜三太子的廟,在樹底下讀。你們看也不見得看得懂,我是看了又看又做筆記才讀出來。我也利用這個機會向各位簡單介紹,讓各位有些入門。
我寫書裡這些文章的背景,第一是,看到當前轉型正義的極限,思想這方面沒有平反,就會有政治受難人及其二代,談到那時候的思想,有點畏縮,像是周賢農說:那時比較有正義感的年輕人都會走向偏左的路線,不敢大聲講出社會主義、加入共產黨。有一個二代在電視採訪中,說他父親沒有說要暴力、要推翻蔣總統,然而當初其父母是要革命的,怎麼會不暴力?怎麼會不要推翻蔣總統呢?當然要,然而為什麼他心裡不敢講出來,問題就在思想部分沒有被平反,就不敢講,講出來就會和這個社會格格不入。促轉會撤銷了五千多名受難者有罪判決,裡面很多都是共產黨,藍營批評說,一方面說他們無罪,一方面又說新黨那些人親共有罪,自相矛盾,對這樣的批評,促轉會也沒辦法回答。你怎麼回答?說以前的共產黨很好?跟現在的政治生態不合的。
然而思想的平反其實非常不容易,它牽涉到我這本書第二單元所提到的「苦命中國的崛起」。因為你對中國的印象影響你對轉型正義的態度,你認為中國可惡、邪惡,50年代那些親共親中的人就錯的,平反就會有相當的障礙。
剛剛我提到我寫這些文章的背景,第二是,在統獨問題上我碰到了困局,我在綠島學了很多左翼的理論,覺得我們左派將來一定成功,綠島當時有獨派跟統派之間的對立,尤其泰源事件之後,對立很嚴重。當時不講統獨,講紅、白,紅的主張社會主義,主張中國統一;白的主張資本主義,主張台灣獨立。
我剛到綠島時不曉得有此嚴重的壁壘分明,有次放風我沒出去,站在走廊上,另外兩間房子也有兩個白派的年輕人沒出去,其中一位用日文向另一位問我是什麼顏色的,剛好我被送去綠島前在景美監獄學了三個月的日文,他們的話我剛好聽懂,我就也用日文回答他們我是紅色的,回答以後我也不曉得紅怎麼一回事,剛到還沒好好學習,因為我的案子是成大共產黨我就說紅色,他們就把我歸在與他們對立的一邊了。
在綠島我從林書揚那裏學習到一些左派的理論,林書揚當時跟我們說,民族只是形式,階級才是內容,台獨運動是一個階級運動,階級運動會以民族的形式出現,本質上是階級運動。我學了這些理論以後,對左派理論深深地信仰,覺得將來左派必然成功,因此出獄後就繼續投入左翼運動。
不過幾年下來我發現情況不太對,台獨越來越壯大、左翼越來越萎縮,跟我在牢裡想像的不一樣,因此我遇到一個困局,是什麼問題導致如此?我想跟當時大陸改革開放有關,當時兩岸一交流,大陸呈現出來的各種負面形象,使得台灣人對大陸沒好感,即使在那邊做生意也不想統一,這深深影響台灣左統派的發展。
我當初看到這個困局就寫了二、三篇文章,評論台灣左統派的統獨理論不合現實。那時左統派代表性理論有像陳映真的雙戰理論,林孝信的美國帝國主義論,王曉波中華文化論,藍博洲的50年代先烈史記等等,左統派試圖以這些理論影響台灣民眾,但沒什麼效果。擋不住大陸改革開放後出現的貧窮落後、官員的貪污腐化對台灣民眾的重大負面影響。就連老同學郭明哲198幾年去大陸,回來跟他的外甥也是左派坐過牢的林華洲說,你趕快過去大陸看看,我不相信共產黨會變成這樣,改革開放的衝擊對老同學來說非常嚴重。
我寫那幾篇文章,說我們現在統派的論述不合乎現實,沒辦法說動台灣民眾,結果那些老同學都起來罵我,有一個人還去質問林書揚說,吳俊宏怎麼變成台獨,你要負責。其實他們也沒看清楚我文章的內容。
六四以後,整個左統派幾乎沉到谷底,內部就產生一些問題,有些老同學認為共產黨變質了,不是他們50年代時所喜歡的共產黨,很多後來轉向台獨了,如我在這本書自序裡提到的吳聲潤、蘇友鵬,其實這也難怪他們走向台獨,中國的那些負面現象真的很難讓人認同。
這時我也是很困擾。但我沒有和他們一樣走向台獨,在我的世界觀裡,中國再怎麼爛它仍是幾百年來受壓迫欺凌的國家,美國日本是帝國主義國家,我不會去認同,我還是站在被壓迫者這一邊。但大陸的狀況也深深困擾著我,中國究竟是怎麼樣了?六四為什麼會開槍?官員為什麼貪污腐化?共產黨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社會主義不行了嗎?
不斷的思考一直沒有找到答案,直到看到溫鐵軍的八次危機,才發現原來答案在這裡。中國出現的各種問題不是共產黨壞了,也不是社會主義不行,是中國太苦命了。一百多年來帝國主義的侵略那就不用講,建國以後要從一窮二白的國家建成工業化的國家,這過程非常坎坷。
以下我簡單地比較台灣與大陸在兩岸分隔後的經濟發展過程來介紹溫鐵軍的論述。
大陸建國以後跟台灣一樣,都在進行國家工業化的建設,工業化第一個要資本,對一個落後國家來說,資本要從哪來?一般都是引進外資,台灣引進美援,大陸引進蘇聯資本,另外一個就是對內的剝削,就是對農民的剝削,台灣是以「農業輔導工業」、大陸是「工農剪刀差」,把農業部門的勞動剩餘價值剝奪到工業部門來,積累工業部門的資本。
在引進外資這方面,台灣因為把主權賣給美國,得到美國援助。蘇聯原本因韓戰援助中國,但蘇聯想把中國置於其附庸下,毛澤東不同意,因此鬧翻,蘇聯把所有資本和人員撤走,中國工業化就變得非常艱苦。
另外兩岸之間,中國走重工業的工業化,台灣是輕工業。重工業跟輕工業的區別是重工業投入資本大、創造就業少,輕工業相反,投入資本少,創造就業多。加上生產出來的產品,台灣可以賣到美國,賣到全世界,中國的產品被世界封鎖,只能賣給自己人,再從裡面進行剝削,以積累資本,那時候有人民公社、農業集體化,我們以為是建設社會主義,其實是工業部門生產的東西要賣給自己的農村,當時中國是每個農民都分到一塊小土地的小農經濟,東西怎麼賣得下去?尤其中國搞重工業,韓戰蘇聯來支援中國,設立各種軍需工業,以應付韓戰軍需用品所需,結束以後製造坦克的變成製造拖拉機,一個大部頭的拖拉機怎麼賣得下去給那些分散的小農,因此才有農業集體化出現。
另外引進外資的時候除了常會產生主權負債外,還會有財務負債,必須還本付息。像台灣輕工業進行得還順利,創造了就業,有就業政府就有收入,就可以還本付息。而大陸搞重工業,投入資本大,創造就業少,國家沒足夠的財政收入,就常常出現財政赤字,政府沒錢繼續投資,引發經濟危機,城市出現大量失業人口,只得以「上山下鄉」為號召,把城市失業人口往農村送,解決這場經濟危機。
蘇聯資本撤走後,中國用人力取代資本,發動全體官員、知識分子以及廣大的人民群眾投入國家的基礎建設,基礎建設一動,工業部門的產品就可以賣出去,就可以繼續經營下去。但如此搞了兩三年就出現三年大饑荒,餓死兩三千萬人。面對這樣的問題,中國共產黨內出現路線分歧,劉少奇主張往私退,把土地還給人民,毛澤東反對,他擔心工業部門積累怎麼辦?並說若往私退,沒多久農村會出現有人賣土地、有人娶小老婆。這樣的分歧就成為文化大革命的背景。
改革開放前出現幾次的經濟危機,出現危機就把人民往農村送,農村除了是工業部門積累的被剝消者,還是城市危機爆發的轉嫁處。因此農民一直很窮,而城市工人也拿著很低的薪水,因此大部分人都很窮。之前去大陸的時候我掏出一百美金,就是他們幾個月薪水了。
中國大陸就是在這種艱苦的環境下完成國家的原始資本積累,建立各種有生產能力的產業,改革開放後,進入世界產業資本的對外發展,但這產業資本的發展,仍需資金,因此需進一步引進外資,要引進外資就必須容許私人擁有資本,這時中國的資產階級就出現,官僚貪污腐敗也出現,最後爆發六四事件,這是經濟規律,除非你不搞工業化,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產業,否則你必然會碰到這些問題。
中國的國家建設過程是非常辛苦的,但他們終究完成國家的工業化,當然他們還有很多問題要克服。我看了溫鐵軍的書後才發現原來中國是這樣的,不是共產黨壞或社會主義不好,而是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要工業化,自然會付出不少的代價,出現不少問題。所以我才寫第二章要介紹給大家,了解中國苦命的一條路。
鍾喬:最後還有半小時,開放幾個問題,可以問也可以談你的感想。
鍾春蘭(問題一):我是成大文學院,當時我大二,學校瘋傳學校有共產黨多可怕!共產黨長什麼樣子?不管是吃自助餐還是在宿舍,大家都說要小心不能被吸收,我心裡想那是不是沒有來往,是不是游泳或飛過來?那時候形容得三頭六臂像魔鬼一樣,我同學在談都是妖魔化的。我就很想知道共產黨長什麼樣子,我很想認識,我畢業後當《遠東人雜誌》當總編輯,因為柏楊認識共產黨人也嫁給一個共產黨人簡永松。他在世新大二成立讀書會,被判十年的牢,出獄後國民黨調查局都到處說這個人做過牢你敢用他嗎?後來我先生跟陳映真一起去彰化幫黃順興助選,台灣第一個無黨籍立委,那時候他是第一個有選舉歌的候選人。當時黨外人士集資給我先生成立一個公司,除了這層關係,吳俊宏也成為我們公司股東,我們公司和他的關係是這樣。
我是媒體人出身,我們有時看三立、民視等等,觀點相反就對了,因為我心有戚戚焉,舉個例子,我十幾年去大陸,北大研究生說「我去台灣一次就不去,台灣報導我們隨地大便、吐痰,都講大陸的醜事,為什麼不講好的?」
我是媒體人,非常關心社會局勢,兩個大象在打架,我們是小螞蟻應該閃一邊,我們卻一直往前走,我憂心的是我們的下一代。我昨天和柏楊太太吃飯,我有時擔心她八十幾歲生活會怎麼辦,她說她有的是錢,柏楊在大陸的版權費之高,簽名也都可以賣錢,大陸人求知若渴。我們在講人家時,為什麼沒有看到人家的年輕人在晚上11點多的晚上在燈下讀書,我們要擔心我們自己。我現在開的公司,從2000年開始是全世界最開始做互聯網公司,大陸的互聯網很厲害。
吳俊宏:跟他先生簡永松在綠島認識,柏楊在綠島跟我關同房,我不曉得他的行情這麼高。柏楊不是左派,我感覺他沒什麼好學的,我是和林書揚學習。這裡就出現一個問題,大陸這段苦命的過程,連大陸人都不曉得,出現西化派,長年批評共產黨。西化派的出現,反映在自由派的柏楊這麼有銷路,我在書裡的文章有談到六四事件,那就是反映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大陸人不知道開放前做了什麼事,開放後覺得西方人怎麼那麼富有、彬彬有禮。這也是六四事件發生的背景,因為他們在這種狀況下太看不起自己的國家。
問題二:苦命,我曾經跟吳老師學過溫鐵軍的八次危機,為什麼叫苦命,中國從建國幾十年以來,有八次危機,第一個危機是繼承以前的危機。危機的意思是我因為經濟發展的規律就產生了這樣的問題,這個問題去解決,又因為規律的關係產生新的問題,每過幾年就有一次,有週期性的危機,溫鐵軍這樣說,別人說這是資本主義社會才有,社會主義沒有。
苦命是因為這不是我要的,這經濟危機是自己來的,不是我主觀要的或是我控制的,但我處理問題可以處理好的話,這就不是苦命,你能夠處理你的命。我們看到中國越來越強,以前被人封鎖,現在被人隔離,都是一種苦命,有沒有經濟規律我就不知道,應該也不是單純的川普在發瘋,苦命就是客觀規律,陳明忠寫過一本書說中國是走一條社會主義的道路,他從馬克思的論述裡找出很多句子,描述中國是走出一條社會主義的道路。溫鐵軍不在乎那些名詞,而是看到很多現實的證據,這就是唯物主義,馬克思當年也是同樣的概念,當年是看到很多事實總結出來的規律,溫鐵軍做的事情就是馬克思做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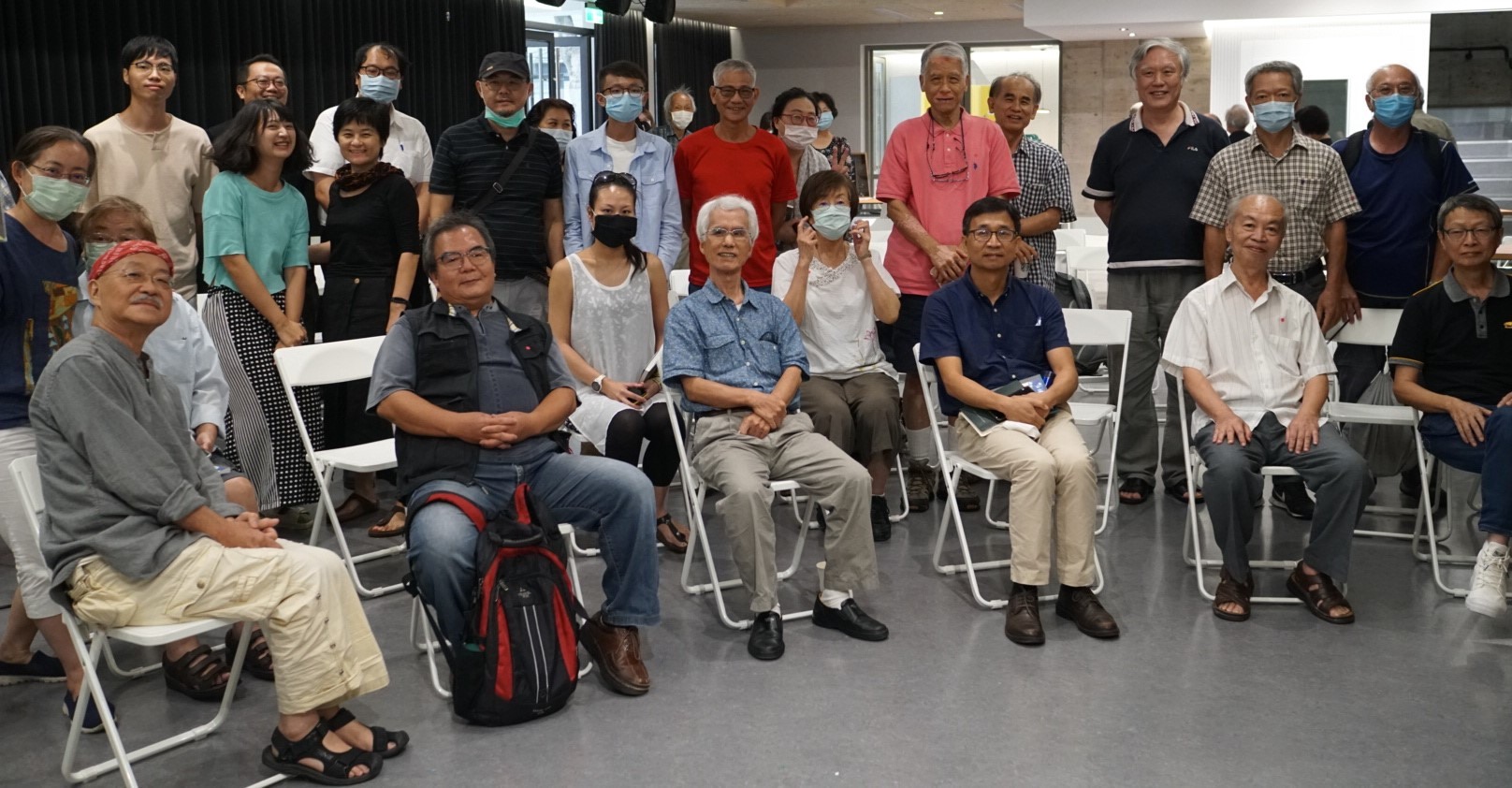
發佈日期:2020/09/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