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許我們能夠從這些事件中提取新的期望,像是更警醒(拒絕遺忘)每一個時代的排外邏輯,以找到更具建設性的方式,來和社會裡、歷史裡、文化裡、現實裡、地理空間裡、世界裡的歧義共處──就像目前整個世界必須聯合起來,找到與陌生病毒的相處之道,才能逐步回到原本生活的步調。而不是自顧自地活在虛假的、隨政客與媒體操弄,因恐懼而搖擺的被害者處境裡。」
(本文為《文化研究》學刊、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文化研究國際中心舉辦的「新冠肺炎下的兩岸移動」論壇的一系列文章。前兩篇分別為:孫賀︱何以解怨:一個「前陸生」的「後陆生」體悟;以及朱凌毅|無用的兩岸關係。本文原刊於2020年6月18日《文化研究》學刊網頁,感謝《文化研究》學刊與作者武當山授權轉載。)
一
2020年初,「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疫情與防疫工作在臺灣的發展,無疑已經從對病毒的防治,轉變為對必須進出臺灣生活的人,依其身分裡的「含中量」予以排除與防制。這當然和一月初總統大選甫結束的「反中」氣氛的延續有關,而此次的疫情則提供了操作「反中」或「疑中」一個借題發揮的「事件現場」(選前「反滲透法」的通過早已是前奏)。以至於,在疫情發生的早期在大陸發生的歧視武漢人與湖北人的狀況,在臺灣是幾乎同步發生的,並且反映在臺灣的管制辦法:首先「篩選」湖北籍的陸生──只要是湖北籍,不管你從大陸其他地方,或是大陸之外的國家,都不准入境臺灣。
這個管制辦法祭出之時(約農曆年期間),我受一位大陸籍臺灣研究生的託付,打電話給臺灣海關詢問:他過去長達半年都沒有入境大陸與湖北的記錄,可不可以在三月的時候從日本入境臺灣回校。
我打電話給海關的時候是大年初六(臺灣開工日)。海關聽我說明原委後,重複問我:「湖北人嗎?」我說對。他說:「那就是不行。」我說:「如果他可以證明這六個月都在日本?」他說:「我們現在就是海外湖北人也都禁止了。」掛完電話後,我心裡不免默想,相對於這位陸生朋友,我一月中才從大陸回臺灣,論有感染病毒的可能性的話,我都比這位在日本的湖北朋友高。到底是什麼樣的醫學與科學依據,造成必須一刀切地預判已離境半年的湖北人傳染病毒的可能性極大,實在令人想不明白。
事後這位朋友聽了我轉達的情況後,告訴我:他不意外。而同時他也向我解釋為什麼找我幫忙打電話的原因。因為以往在臺灣有出入境事宜需要找臺灣海關的時候,臺灣的海關人員聽到他的大陸口音後,問答都是非常不耐煩的,所以才委託我這位「臺灣人」幫忙。聽到這位朋友的感受之後,我對他表示非常的抱歉,我說「公家」機關與「我們」不應該如此對待你們。
舉這個例子,不是為了全盤否定臺灣社會,好像我們全無對外地人友善與寬容的一面。但是,在這次事情上,我也更清楚地感受到,臺灣現在面對中國大陸(或曰「中國因素」),絕對不只是十幾年前的藍綠鬥爭這麼簡單,而是接著藍綠鬥爭的血骨把自己再往某一種更為單一的、更具排除性的國族意識形態推,以豢養民眾對中國大陸的對立情緒。包括我觀察到,疫情期間的新聞,假使是關於中國大陸的報導,即使出現少有的未經加油添醋的新聞,多數網民對新聞的評語也多半是「你們看中國果然⋯⋯」、「不意外,中國⋯⋯」這些多是沒有現實根據的粗評或情緒話語。令人感慨的是,互聯網時代,資訊與新聞的流通這麼豐富,甚至跨區域異地的實際交流早已經是常態。但是多數人卻寧可浸潤在情緒式的片面資訊裡,去脈絡地任意(甚至是惡意)解讀,而不願離開這氛圍,直面報導視野不夠寬廣的新聞和資訊環境,為我們認識事實造成多大的屏障──我們是否願意承認,這種資訊條件正是我們的「不自由」、正在腐蝕整個社會對於歷史與現實的判斷。
在戒嚴與黨外運動時期,民眾與各方社會團體、文藝、(地下)媒體運動所爭取的各種「自由」,如今形同讓渡給更形對立的選舉式政治意識形態,只為了選票和執政,而不是為了長遠的、和平的公共與公義的政治。民眾、在野黨、大眾媒體、民間組織、文化人、學者、「知識份子」在「護臺」兩個字前,也日漸失去監督執政黨的進步力量,喪失了遠見。何時「愛臺灣」成了這麼敵我分明與排外的名詞?難道我們忘記了1990年代「怕死的回到大陸去」這種省籍仇恨政治邏輯,曾經給社會帶來多麼深重的撕裂?
二
在這期間,我時常想起兩個文本,都來自1990年代對臺灣本土主義意識形態最高漲的時刻的反思:
漢族往臺灣移民的歷史中,有陰慘的暗部。是蛇頭苛酷榨取,在大海中謀財害命,在臺灣島的近海中棄溺移民,名曰:「種芋」。幸而登岸的「羅漢腳」,立刻陷入先來移民殘暴的主佃關係中,受盡盤剝。幾百年後,這幕大肆魚肉兄弟骨肉的慘劇,在「文明開化」的臺灣變本加厲地上演。「大陸客」、「大陸妹」、「偷渡客」、「外勞」這些稱呼,使骨肉兄弟變成了奴隸。非我族類,人可得而壓迫之。非我族類,死了,也不過死了一條野狗。親愛的兄弟,移民同胞構成的社會,相煎一何太酷!
── 陳映真(1995)[1]
我要問你哦 從幾歲來臺灣 你吃的是什麼米 喝的是什麼水
另外兩個政黨就一直給我們抹黑 他說你是外省黨外省黨 說你一百次 你就變成外省黨了
我不知道你們的良心在哪裡 我想這是在這次事件中我最大的一個感觸
大不了死了 有什麼關係 怕死的人回去大陸 怕死的人回去大陸……
如果為了保衛我們的家園為了我們的人民 我們起來戰爭 有什麼沒有尊嚴
人比鬼還兇 人比鬼還兇……
── 黑名單工作室(1996)[2]
會有這樣的「聯想」是有感於當前臺灣社會,不管有沒有「疫情」,「反共」與仇中的情緒與論述並不自外於冷戰戒嚴時期親美反共意識形態,以及解嚴後本土主義意識形態的建構。而這個持續建構的動力,除了來自於我們並沒有看到社會組成轉變的現實與外部關係外,也來自於我們並沒有從族群(包括原住民)撕裂、互相不了解的歷史裡吸取教訓。
我想要指出的是,身於一個移住民社會,假使我們期許自己的社會並不是一個善忘的社會,假使我們期許自己的社會未來的公平、民主、正義不只是由選舉的勝敗來定義的話,我們該怎麼面對整個社會當前「排外」與歧視的階序邏輯 ──「非我族類,人得而壓迫之」?我們什麼時候才能脫離動不動就希望誰滾出去、滾回去的態度,來對待(或創造出)異己?
很記得一句閩南語俗語「有量才有福」,這是我從小聽到大的一句話。就我自己的成長經驗而言,臺灣民間社會雖然免不了對人分門別類,但是大致來說對外都可以展現包容與寬厚的一面──尤其當他們有更多機會瞭解對方的生活狀況與不同的處境的時候。換位思考,我認為這也是不少人認為,就防疫過程中臺灣政府對陸籍人士與相關身分採取的措施而言,當有人指出這是帶有「歧視」的做法時,不少人會覺得不舒服的緣故──臺灣這麼棒、臺灣人這麼讚,我們怎麼可能歧視他人?但是,假使我們有機會不只是透過媒體來瞭解陸生、大陸配偶、臺商、在大陸工作的臺灣人,甚至是在疫情中的大陸普通老百姓如何生活── 我們才能知道臺灣人「沒有歧視」這個說法是否禁得起挑戰。如果臺灣的歷史主體性、與區域和世界的關係(當然包含中國大陸)需要靠建構一個憎恨與復仇的對象來達成──這個仇還有可能因為不同時期利益集團不同而變化或加大。試問你我,能夠相信這樣的社會會有愛和寬容嗎?這樣的社會會有互信嗎?而我們希望自己的下一代傳承這個仇恨的基因嗎?
期許我們能夠從這些事件中提取新的期望,像是更警醒(拒絕遺忘)每一個時代的排外邏輯,以找到更具建設性的方式,來和社會裡、歷史裡、文化裡、現實裡、地理空間裡、世界裡的歧義共處──就像目前整個世界必須聯合起來,找到與陌生病毒的相處之道,才能逐步回到原本生活的步調。而不是自顧自地活在虛假的、隨政客與媒體操弄,因恐懼而搖擺的被害者處境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解
[1] 引自:陳映真。2004(1995)。〈十句話〉,收於陳氏著《陳映真散文集1(1976-2004):父親》,頁97-104。臺北:洪範。
[2] 引自:黑名單工作室。1996。〈生命之輕〉,《搖籃曲》。臺北:滾石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所屬公司魔岩唱片股份有限公司。這首樂曲沒有演唱者,由黑名單工作室在1990年代由媒體所收集並錄下的法西斯「話語」與政治人物「言論」所剪輯的人聲與編曲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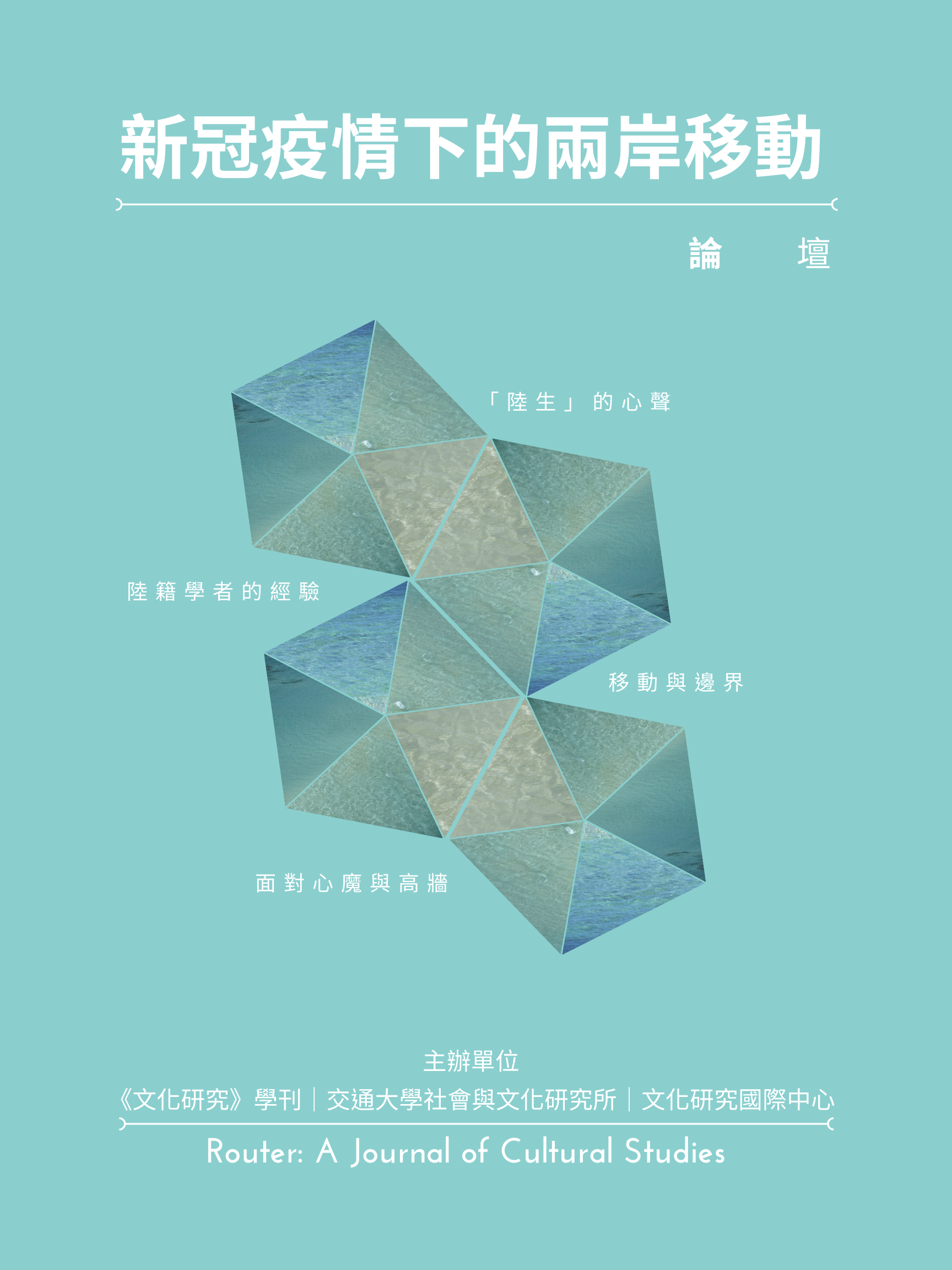
發佈日期:2020/07/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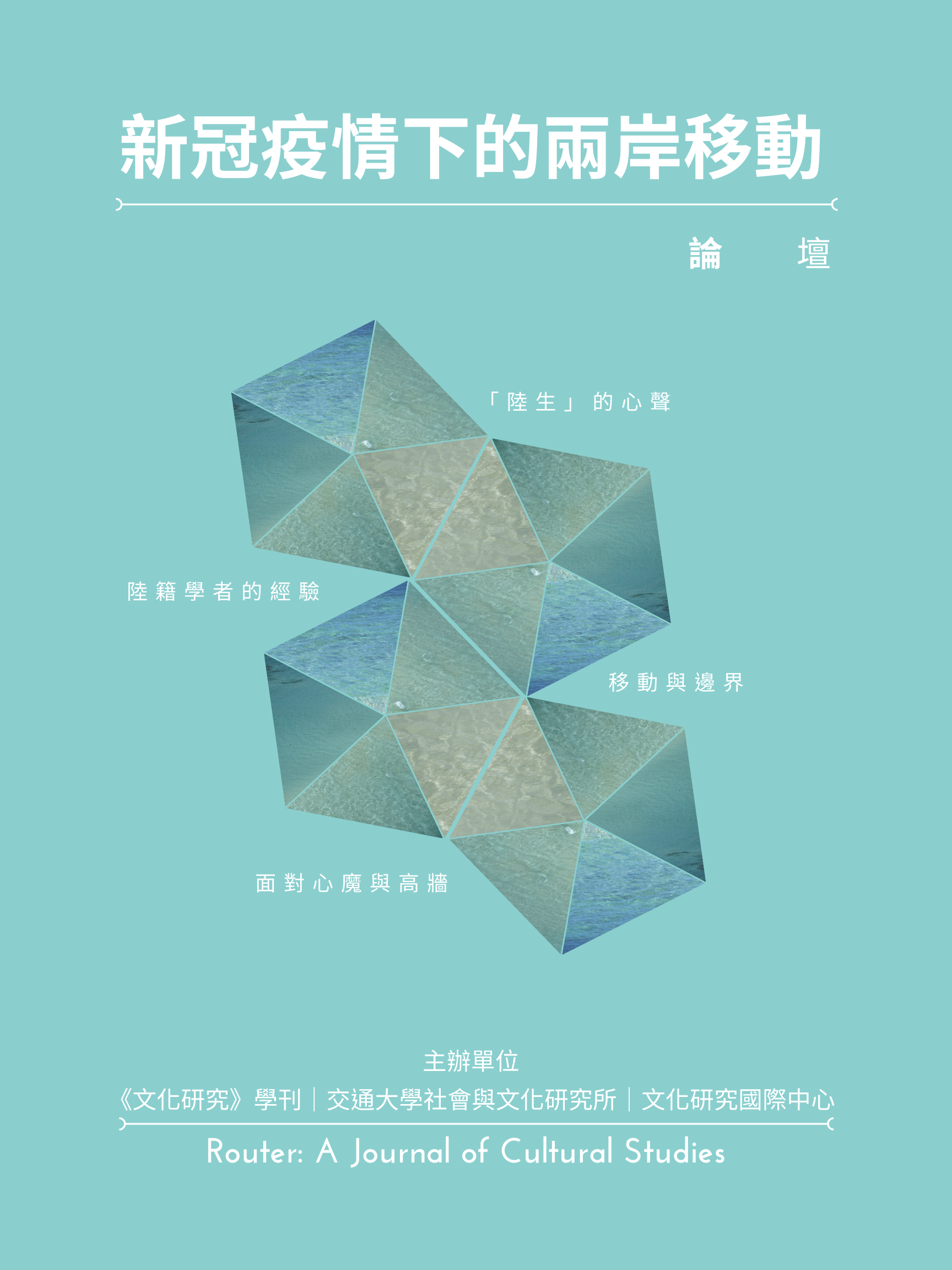

One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