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為男人,我很抱歉:台灣碼頭工人的下墜人生
◎馬蓋先
本文是對岸對《靜寂工人》一書的閱讀筆記,精準地捕捉到書中所描繪的新自由主義浪潮變遷,以及對一群碼頭勞動工人的階級與性別位置的改變。轉載自2018/08/03土逗公社(tootopia),感謝土逗公社授權轉載。
摘要:八十年代,台灣碼頭工人曾是一群「很有本事」的男人:他們拿著高薪的鐵飯碗,口袋中溢滿鈔票,同時還有多個婚外女友。而隨著新自由主義的浪潮席捲台灣,大量工人失業,這使得他們無法養家糊口,更無法延續婚外戀情,而面對婚外女友的自殺,更是手足無措。他們從「高高在上」到「被踩在地上」,從「像個男人」到「不像個男人」,再到最後無以為人,這種個人的悲劇命運折射出背後更大的社會結構變遷。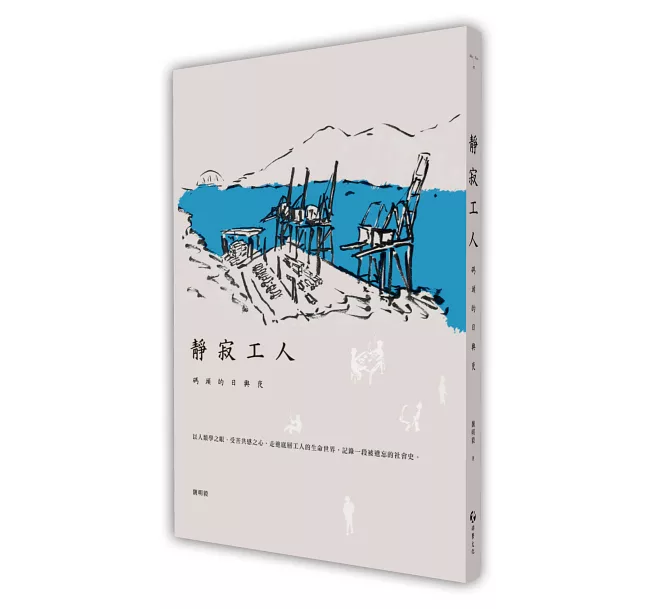
2014年冬,我曾步行於台灣港口城市——基隆的碼頭。偶有貨櫃車駛進或駛離,我會被尖銳又巨大的金屬擦撞聲嚇到心悸。聲響消逝,隨之而來的便是無比漫長的沉寂,與沈寂色調相搭配的還有形單影隻的碼頭工人[1]。踩著緩慢腳步、神色不緊不慢卻毫無生氣的碼頭男人們,更給這片死寂的港口增添了些許灰暗。誰曾想到,在台灣經濟騰飛的八零九零年代,這片死寂的港口,曾經是在船燈和貨車燈映照下「紅透半邊天」的不夜碼頭;而這群沉悶的工人,則曾經是手持重金、神色飛揚的工作者。
那麼,在這四十年間,基隆碼頭和在此為生的男人們,到底經歷了什麼呢?
2016年,魏明毅出版了《靜寂工人:碼頭的日與夜》。在書中,以基隆二十多位碼頭工人的敘事和在碼頭的民族志,作者分析經歷新自由主義浪潮席捲前後台灣基隆碼頭的歷史興衰和碼頭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的起起伏伏。
民營化:從「工人變頭家」到「被新自由主義掛斷」
基隆地處台灣北端與東北端的匯合處,在日本殖民時期,基隆海港作為殖民國與南方貿易的轉運港。憑藉著地理優勢和日本的既有開發,基隆港成為國際大港,在全球分工與運輸體系中扮演著關鍵角色。
當時,碼頭的裝卸工作都由港務局委託工會承攬,由工會的班隊長負責招募與安排人力;工資則透過班隊長進行分配。當時的工會發展兩套人力模式,第一種是僱用已經加入工會的正式工人——「拿牌仔」,這些工人每人都有印著個人姓名的名牌,這張通行證還能轉化為經濟資本,比如有需要時可以拿著名牌作為擔保借貸,總之,這群工人享有高薪和多種福利;第二種則是僱用非正式工人——「沒牌仔」,這些臨時工人工重酬薄。「拿牌仔」等同於鐵飯碗,享有比較高的權威,可以挑選較輕鬆的搬運工作,那些粗重的工作,例如搬運糖或鹽巴則多由沒有保障、沒有福利、錢又較少的「沒牌仔」來做。這樣不公平的工作安排,引發了非正式工人的不滿,最終在1972年引發了散工的集體抗爭,在這場轟轟烈烈的抗爭之後,一千兩百多位散工晉升為有牌的正式工人。
1980年代,碼頭上的搬運與裝卸工具逐漸機械化,承擔了多數依靠勞力的裝卸工作後,工作量頓時驟降,促成了「工人小頭家」(在台語中為老闆的意思)和「貨車司機」群體的出現。具體地說,工作量下降、工資不變的情況使得一些工人開始自己當起頭家,聘僱另一位工人代班,而自己在外兼差、投資股票或返鄉與妻小重聚,以每個月四六或三七分的方式分賬。同時,隨著越來越多國際貨櫃輪船到達基隆港口,一大批貨車司機也湧現在碼頭。這些貨櫃車又分為公司車和契約車,前者司機是公司聘僱的員工,車屬於公司所有;後者本身即是頭家,車屬於自己所有,透過一般公司在外接單。這一時期是這群口袋溢滿鈔票的男人們的黃金時代,他們擁有高收入和高尊嚴。
然而,碼頭工人的黃金時代在九零年代隨著全球市場的變遷而逐漸灰暗下來。在1990年代末,國際運輸航線版圖更改,國際貨船入港數量驟降,台灣政府為求降低成本、提升競爭力,頒布民營化政策。在這場新自由主義浪潮下,工會也因面臨財務的困難,試圖以犧牲不再年輕力壯但尚未達退休年齡的裝卸工人,藉此卸責。於是,裝卸工人與貨櫃車司機的命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轉變。在民營化政策中率先被犧牲的中年苦力,缺乏接軌外部市場的技能,他們表面代工,實則失業,瞬間掉入工作的不穩定與不確定的漩渦之中。
年近40的林進益這樣說道:「實際上裝卸公司需要的人沒有那麼多,到最後真正可以留在碼頭的人不到八百,剩下將近兩千人,那麼多人馬上就沒有工作了。我們的專業在外面沒用,出去怎麼辦?像我們這種從小就在碼頭的,根本沒有其他謀生技能」(魏明毅,153)。也如在碼頭上開橋式機的張富昌所言:「我們從『高高在上』到『被踩在地上』。」(魏明毅,156)
和林進益與張富昌共享失落命運的還有無數碼頭工人。缺乏謀生技能使得這批工人落後於時代,而時代所需要的正是政府所大力發展的觀光業所需要的高學歷人群。新自由主義席捲之下的國際航線版圖更改和台灣港口貨運民營化,催使政府發展解決方案,而代表著現代和進步的觀光產業則成為基隆港口的新興產業。這一產業吸引著大批擁有語言專業、國際接待和行銷等專業的人才,在這樣的情況下,裝卸工人和貨車司機被遠遠甩在僱傭大隊之外。僅有少數工人順利找到工作,而這些工作,不出意外地,也大多是低技術門坎的工作,例如大賣場、警衛、開出租車、擺小販。
在被新自由主義「掛斷」之後,曾經有派頭的碼頭工人漸漸失去身為工人的地位和尊嚴,如魏明毅所言,這是「集體下墜至底層、陷落無疑遁逃的失能(感)。」
底層文化:從gâu lang 墜入pìnn-bo-lian
一通來自刑事組的電話打破了碼頭工人王家龍的安靜生活。他交往許久的婚外女友自殺了。事後,王家龍說道「女朋友變成這樣……很多人聽起來還以為我很行,同時交很多個,可是我自己知道,是悲劇收場。」王家龍口中的悲劇,是女友的死,還是他的生命歷程,抑或是台灣碼頭工人的共享命運?
如以上所述,碼頭的改變只是被觸動的「第一張骨牌」,隨後,無數碼頭工人的生活日常和文化互動經歷了巨變與瓦解。
第一層劇烈變動發生在碼頭男人們彼此為伴的同事情誼中。不管是被排除在碼頭外的待業工人,或是民營化後繼續留在崗位上工作的工人,對於這份工作的認同已經不如以往。被資遣的工人斷了與原來同事的社會聯繫;碼頭上的工人因工資緊縮、追求效率的分工而獨自作業、貨品機器損壞的風險個人化,皆使得同事之間的彼此為伴的情感連帶與工作認同產生改變,這份工作不再具有極高尊嚴,而僅僅是一場蒼白勞動(魏明毅,169)。
曾經,碼頭工人呼朋引伴、成群結隊地聚集在小吃店中互相取鬧談天的場景已然成為歷史時刻,如今只有一個一個的孤身工人散落在碼頭的日與夜。
第二層變動則滲入碼頭男人們的情感連帶,扭轉了男人們在與妻子、婚外戀對象、兒女互動中的主導地位。標誌著碼頭男人們的黃金時代的一個關鍵是,能否在家外發展情感關係。gâu lang,在台語即「很有本事的人」,對碼頭工人而言,能否發展出婚外戀情,則界定了什麼樣的男人是厲害的、有本事的。茶店仔是碼頭工人們經常光顧的一類小吃店,曾經,在茶店仔中消費千金顯示著碼頭男人具備經濟能力,而茶店仔中的阿姨仔則扮演著碼頭男人的情緒出口。碼頭男人與店裡的阿姨仔頻繁互動,阿姨仔藉由傾聽與陪伴,一步步進入碼頭工人的工作與日常生活,於是,與茶店仔的阿姨仔發展出婚外關係則是碼頭男人引以為傲的事情。與此同時,碼頭工人的妻子則被期待扮演好情緒平衡的角色,即在得知丈夫與婚外女友交往時能夠忍氣吞聲、照顧家裡。
如開篇提到的王家龍,當時正在經歷民營化打擊的他與婚外女友的相處不斷惡化,而惡化的根本原因是經歷工作地位的嚴重下滑的他無以支付與多位女友交往的費用、也無力承擔情感支出。他自己都不知道未來要怎麼辦,「每天想、每天頭痛」,這不斷惡化王家龍與婚外女友的相處,使得女友不堪情緒重負而自殺。這段在外人看來符合傳統對男性性別期待的gâu(有本事)的輝煌歷史——畢竟,王家龍看似「擁有」多個女友,還有女人為他自殺、崩潰——其實是王家龍難以言說的痛處,這些痛處伴隨著碼頭工人地位滑落、無以維繫男性氣概的歷史命運。
親子關係則是另一重碼頭工人的情感連帶。遭遇碼頭民營化的打擊,李正德從碼頭退居家內,被迫成為了一個失能的工人、失格的丈夫與父親。曾經信誓旦旦地說「再窮也不能窮孩子」的他,在失業在家時面對著孩子無意間透漏出的表情、語言和動作時,總是被推進驚慌失措的情感泥沼中。如此一來,在家中的許多時刻,在米酒中加水成為李正德的習慣,「加水,可以喝的比較久一點」,透過喝酒,他迴避與兒子共處時的靜寂氣氛和伴隨而來的失能感,「我喝一點酒,讓自己有點醉,這樣也比較不用去想說,不知道要和小孩說什麼。」
原本在情感世界得以維繫男人尊嚴的gâu-lâng,在九零年代後,隨著市場波動,被擠出勞動市場的舞台,瞬間成為pìnn-bo-lian(變不出其他把戲的男人),也即在文化上無法作為的失能男人。
第三層變動則發生在基隆城市地景的階層劃分,這伴隨著的是大幅度更改了的基隆的日常生活空間。觀光業進駐之後,基隆的城市地景和個人的生活空間均經歷重塑。絡繹不絕的國際郵輪、潔淨的觀景台和日漸稀少的貨櫃船都在傳達著「誰才是空間合法使用者」的訊息。國際觀光客自然首當其衝,而碼頭工人則是不受歡迎的一群人。於是乎,「碼頭工人因為其自身形像不符合國家觀光意向,而被驅逐出可見的公共空間。」(魏明毅,198)
「像個男人」:自證男性氣概的文化意象
在台語影片《大佛普拉斯》裡,窮人的世界是黑白的,富人的世界是彩色的。而被新自由主義洗禮的碼頭工人則親身經歷了生命的色彩斑斕與黑白暗淡。這些色調的轉折體驗,始終圍繞著一個文化意象,即對碼頭男性工人必須要 「像個男人」的文化期待。
「像個男人」所展現出來的框架是一種男人的理想狀態,即督促男人思考如何形塑自身以成為一個有價值的男人。而工作是連結個人和文化意象的方式之一。正如書中所言,「工作,不只是一個位置,它同時影響著人如何看待自己、能與什麼樣的人互動、可以在什麼樣的時間行走在哪些地方。」碼頭工人的工作正是這樣一個機制,這份工作決定了男人們在全球勞動市場中扮演的角色和他們身處的社會關係。在工作面臨整體政治經濟結構轉變的影響下,這些角色和社會關係也在發生變動,然而,男人們被所期待的文化形象卻鮮少更動,這使得碼頭工人在發現自己難以快速適應工作和社會關係變動時變得無比焦慮和失落。
具體地說,從gâu lang 墜入pìnn-bo-lian體現的是遭遇了由不確定、不穩定和不安全的工作帶來的各種情感失能體驗。碼頭工人變成一個壓抑的群體,他們的文化認同變得破碎,社會連帶瀕臨瓦解,成為一個個孤身的工人。更重要的是,他們把錯歸諸於自己沒有本事、沒有能力因應這個改變,而無法看穿外在的結構力量。例如,在民營化潮流中倖存下來的李松茂,即便已經進入裝卸公司,擔任主管並且為孩子攢下房產,他仍然對自己比「小拇指」,認為自己是最差的,「到頭來就只是工人而已」。
以碼頭男性工人為例,跨國供應鍊和台灣(乃至東亞)地方社會文化情境的相結合,我們社會對男性產生一套期待,例如要養家、要有高學歷、要買房、要買車、要滿足一定物質條件,否則,男人則被批判為「不像男人」。於是,這些期待促成了男性的情感形態,這些情感形態包括親子關係、夫妻互動、家外親密關係以及同事情誼。然而,當社會整體的經濟結構重構勞動和受僱形態,使得個人無法快速適應社會結構的轉變之時,男人們則被急速地推向邊緣,最終,正如魏明益所言,他們從「像個男人」到「不像個男人」,到最後的無以為人。更唏噓的是,當他們急於將這些失敗歸結於個人的無能,便也同時忽視了個人悲劇背後的更加宏大的社會結構與變遷。
註解:
[1] 在《靜寂工人》一書中,「碼頭工人」指的是工作空間在碼頭上的男性勞工,但不包括碼頭上的公務人員。
編輯:xd Targaryen
美編:黃山
發佈日期:2018/08/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