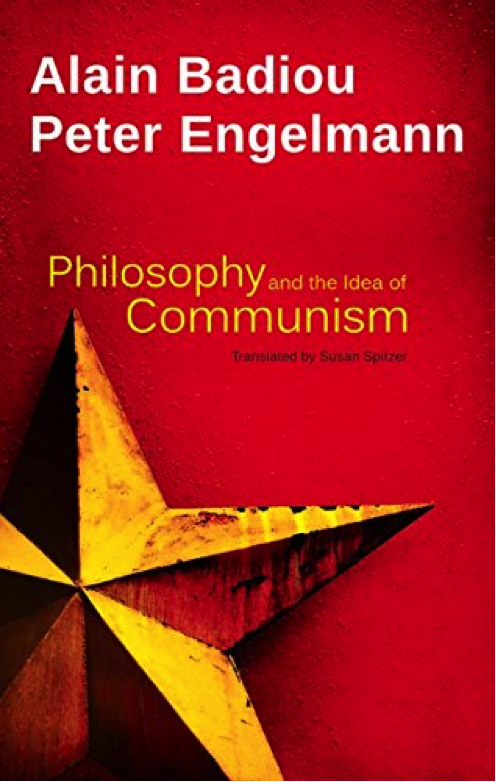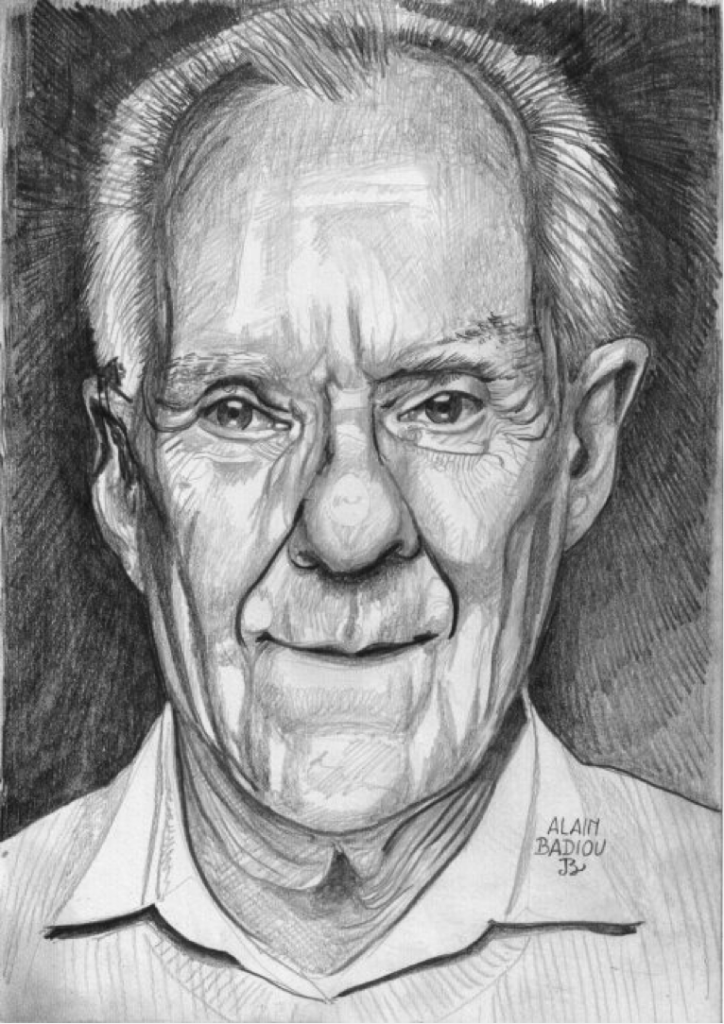巴迪歐:三種馬克思
◎九月虺
【譯者按:最近讀2015年Polity出版社新出的巴迪歐(Alain Badiou)和彼得·英格爾曼(Peter Engelmann)的對話錄《哲學與共產主義觀念》(這本書的首版是德文版,與2012年在Passagen出版社出版),讀到了巴迪歐對馬克思的詳細簡介,我比較感興趣的是,巴迪歐很明確的區分了三個馬克思。第一個馬克思實際上是論費爾巴哈的馬克思,巴迪歐稱之為黑格爾式馬克思,這個馬克思有一種歷史哲學,即歷史唯物主義,他提出了一種關於人類社會發展一般規律的辯證法。第二個馬克思是《資本論》的馬克思,這個馬克思著眼於那個歷史時代下的資本主義社會的詳細剖析,即一種政治經濟學分析,不過巴迪歐的極端看法是,在《資本論》中,辯證法完全是靠邊站的。通過這個問題,我聯想到張異賓老師在《回到馬克思》中提到的廣義歷史唯物主義和狹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區分,第一個馬克思對應於廣義歷史唯物主義,而第二個馬克思對應於狹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而第三個馬克思,在巴迪歐看來,是最對他胃口的馬克思,一種非哲學,非經濟學,純粹政治上的革命性的馬克思,這個馬克思提供的不是完善的辯證法和結構性分析,而是面對未來的勇氣和革命的意志,將無產階級化身為革命主體的馬克思。這個觀點,在巴迪歐那裡,還算是比較新的,畢竟此前,尤其在《存在與事件》之後,巴迪歐直接論及馬克思及其著作的文本極少,這本新書,為我們呈現了巴迪歐對馬克思看法的冰山一角。
另外值得一說的,巴迪歐談到了中國,在巴迪歐眼中,這是一個帝國主義式的中國,一個擁有掠奪和軍力強權的中國,這個中國,他不感興趣。或許這是中國學者多次邀請巴迪歐,巴迪歐不太願意來中國的原因之一吧!對於巴迪歐對當下中國的看法,雖有偏頗,但值得我們中國的學者細細反思一下,實際上朗西埃也好、阿甘本也好、齊澤克也好、甚至已經去世的拉克勞也好都對當下的中國有著特殊的看法。
由於讀著興起,忍不住將其中的幾個段落翻譯出來,時間所限,我不能提供全文的翻譯,而且一夜完成,很多細節未能細細考究,所以不到之處,還望海涵。】
彼得·英格爾曼(以下簡稱彼):馬克思又如何呢?馬克思是一位哲學家。他是一位黑格爾主義者。他將黑格爾的辯證法覆蓋在費爾巴哈的問題之上。是否如你剛才談到的尼采一樣,這是從一種原則轉向另一原則的情形呢?
阿蘭·巴迪歐(以下簡稱巴):當然,可以在馬克思那裡找到這種企圖。我已經說過,這個企圖就是一種典型的十九世紀的企圖,此外,這種企圖也可以在佛洛德和精神分析那裡找到——這種企圖代表著達爾文式的解釋。在所有這些主要的作者那裡,都存在著某種十九世紀式的實證主義的希冀。但是,對於馬克思,我想說的是,實際上存在著三種不同的馬克思,在他那裡,這三種東西天衣無縫地契合在一起。首先有一種帶有黑格爾哲學遺產的辯證的馬克思,這種辯證法主要被視為客觀性的辯證法,即矛盾運動發展的辯證法。這就是構建了歷史哲學的馬克思,實際上,這是一個擴展版的歷史運動。
彼:是否馬克思的哲學史實際上就是黑格爾的哲學史?
巴:當然。不過他用唯物主義的哲學史取代了黑格爾的哲學史版本,其代表性特徵是有著明顯的必然性因素。即以一種必然的方式從一個階段過渡到另一個階段:從封建制過渡到資本主義,而在此之前,是從奴隸制過渡到封建制。這就是我所謂的作為歷史哲學家的馬克思。
彼:非常正確,他使用了黑格爾的邏輯。
巴:的確如此。因此,正如我剛說過,這就是第一種馬克思,即黑格爾式的馬克思,一種帶有廣闊的歷史視野的馬克思。然後,在我看來,還有一種完全不同的馬克思,這個馬克思真的按照真正的社會功能理論,來構建了一種關於社會的科學。正如他自己說過,這個理論不是起源於歷史哲學,而是起源於英國政治經濟學。不是來自于黑格爾,而是來自于李嘉圖。眾所周知,馬克思幾乎畢其一生來寫作《資本論》,這本書並沒有寫完,此外,這本書建立在非常詳細,非常精緻的分析科學研究的基礎上,在這本書中,黑格爾的辯證法完全處於次要地位。我並不是說,辯證法在其中完全消失了,而是說,它不在其中佔據主要地位。其中起到主要作用的是剩餘價值及其分配機制的分析。
彼:但這裡沒有歷史哲學的內在邏輯。
巴:剩餘價值及其分配機制的內在邏輯就是功能邏輯。
彼:這難道不是一種危機邏輯嗎?
巴:在最終的分析中,這更多是一種功能邏輯。
彼:但《資本論》第三卷走向了經濟危機
巴:但週期性經濟危機的力量並不是馬克思的創見。實際上我們在亞當·斯密那裡就可以找到資本主義社會由於生產過度造成週期性經濟危機的觀念。馬克思所發現的是資本如何起作用的規律,以及對資本的規律進行了分析性評價。我並不認為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完全是辯證法的馬克思,而是一個分析性的馬克思。毫無疑問,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受到了科學理想的驅動,一種實證主義的科學理想的驅動。
彼:這個分析性的馬克思往斯密身上添加了什麼?
巴:他添加的是從如下事實中的得出的結論,即問題的絕對核心就是剩餘價值,加上了一個分析性和規範性的結論,即當一切都說了和做了時,最基本的規律就是不惜一切代價來維持利潤率。這就解釋了社會和政治組織的不同的興衰變化。因此,他引入了一個明顯的新觀念,甚至與李嘉圖相比也是十分新的,但馬克思與李嘉圖在精神理念上高度一致。這個馬克思就是十九世紀的科學主義的馬克思。
不過,還有第三個馬克思,即作為一個政治人的馬克思。這個馬克思是第一國際的創立者,在法蘭西階級鬥爭的特殊時期大聲宣告,賭上一切,同無政府主義者,同普魯東等人進行極其艱苦卓絕的鬥爭。一旦有必要,這個馬克思會援引另外兩個馬克思,一旦需要,他會援用歷史哲學。很自然,他也會援用對經濟科學的討論,但他所追求的目的卻是第三種類型。第一種類型的目的提供的是歷史發展的一般框架,第二種類型的目的是對當代社會運作機制,進行極其精細的分析,第三種類型則創造了一種革命工具,某種可以積極地用於顛覆既已確立的秩序的工具。畢竟是馬克思開始了德國的革命。這個馬克思也開創了另外一些東西。我認為,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總會有個問題,就是各種不同的馬克思主義思潮究竟所指的是哪一個馬克思。這個問題取決於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時期,不同的人,甚至不同的參照文本。那些被隱匿,被禁絕的文本往往占了很大一部分。在法國共產黨的背景下,在長達三十多年的時間裡,他們不允許大家閱讀《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這些文本是被禁絕的。這些文本被視為黑格爾主義的文本。事實上,當你們閱讀這些文本的時候,你們會發現《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就是試圖將第一種類型的馬克思和第二種類型的馬克思結合起來的文本,最終結合為第三種類型的馬克思,即讓無產階級的歷史主體可以將歷史哲學和對資本主義的分析角度熔合在一起。
所有這些都說明了對於這種特別的複雜性,於我而言,馬克思非常令人神往,非常令人著迷,因為,歸根結蒂,馬克思是試圖在一個由結構辯證法所支配的情境中生產出一個革命主體理論的思想家,亦即,在這個情境中,它不會自發地讓自己去創造出一個新的政治主體。因此,在馬克思自己那裡,必然存在某種矛盾的東西,一種必須要麼使用分析材料,要麼使用辯證材料才能解決的東西,具體採用哪種方法,取決於他所要討論的是經濟學還是歷史哲學,但綜合所有東西來考察,他深入關涉的東西,以及其紅痣正是在於去構建,去讓一種全新的政治主體得以出現。
當阿爾都塞說,在馬克思那裡根本沒有主體理論時,這是因為阿爾都塞在《資本論》中沒有發現主體理論。如果你們閱讀一下《資本論》,你們不會找到一種新的政治主體:我們知道,當馬克思開始考察階級概念的時候,他停止了《資本論》的寫作。他那時根本沒有面對政治主體問題。因此,我們不太可能從《資本論》中獲得一個新的政治主體。不過,在構建新的主體的時候,倒是可以使用它。我認為,馬克思已經首先嘗試了如何將結構性分析同辯證法以某種方式結合起來,通過這種方式,可以讓主體問題有可能呈現出來。這就是為什麼我喜歡這一點,因為我曾說過,這就是最吸引我的問題:我如何可能從最為嚴格的形式數學上,以這種方式實現最終為主體問題所應用的東西?這就是馬克思打算去做的事情,在某些方面,這也是佛洛德打算去做的事情,正如拉康已經清晰地說明了這一點。在佛洛德那裡,也有一個理論,一個非常強的進行分析的癖好,即他用熱力學的模式來解釋無意識。和馬克思一樣,他也是實證主義的死忠,事實上,對於十九世紀思想家們而言,均是如此,不過最後,從這種思潮中誕生的正是一種新版的人類主體。正如拉康後來所說的那樣,這是一種史無前例的人類主體的版本。當你們開始接觸這個問題的時候,他們正在面對這樣的問題,即必須將結構分析推進到這樣一個地方,在那裡,真理本身需要某種類似主體的東西。我認為,我們在馬克思和佛洛德那裡都可以發現這一點,有點反諷的是,他們的共性就是他們都是主觀化的實證主義者。
彼:但如何在結構分析中來想像一個主體呢?
巴:那裡必然有一個決裂的範疇。
彼:是的,必然有。
巴:絕對有。在馬克思那裡,它就是“革命”的範疇,因為革命是一個事件,革命既不是必然的,也不是不可能的,它是一種可能性。但與他所說的恰恰相反,馬克思從來沒有想過這種可能性是不可避免的,是絕對必然的,它將會靠自己來發生一切。倘若他對此想得過多的話,他就不會花掉其畢生精力去創建第一國際。而佛洛德,他對於分析治療有一種麼特別的觀念,這種觀念導致了在主體那裡的病兆和精神組織的真正的改變。在我的更富有哲學味的體系中,這就是事件的範疇,我們知道,它包含了所有外部的衝擊,同時它擾亂了分析所揭示的一切。恰好,為了真正理解決裂,你們也必須堅持進行分析,因為決裂就是同結構的決裂,同分析的決裂,它將會保留結構的某些特殊的特徵。換句話說,對於決裂結果的知識上的認知,需要你們牢記在心,並且要理解,決裂何以影響了結構。我認為這些正是革命性的馬克思的問題:在革命或決裂的前提下,之前分析的分析性和辯證性的力量是否可以仍然被保留下來?因為通過決裂的過程,在馬克思分析法蘭西情況時所清楚面對的問題正是,決裂不是總體的決裂。決裂往往發生在一個特殊點上,這個點或許可以擴展開來,但它總是發生在某個特殊點上。因此,事實上,存在著決裂,但圍繞著決裂的一切,這個決裂的點,被囊括和納入到結構分析所揭示的東西之內。
彼:那麼,我們想知道,如果存在著一種傾向於描述出革命主體的邏輯,源自於兩種活動,即分析行為和辯證行為的主體定義是什麼,馬克思在其政治著作中所闡述的主體的所有要素是什麼。
巴:我認為主體的本質實際上只能回溯性地體會,或部分地被揭示出來。主體就是一場運動,在運動中,事件性決裂的結果在知識和精神層面上被揭示出來,它可以在情勢中被發現。至於共產主義運動,很明顯,主體通過使用辯證哲學和對資本的分析,闡明了革命性決裂的結果,這是一個人性歷史的視野,其實例是由先前的革命和起義所提供的。主體通過使用所有手段,創造了某種方式,讓正在進行中的過程變得可以理解。這種可理解性通常是有偏頗的,因為運動才是首要的東西。這個決裂的結果是自由運行的:它們是創造性的,它們是積極的,它們總會有些相當複雜的關係,在一些良好的老馬克思主義時代中,這就是著名的理論與實踐關係問題。
……
(關於中國的部分)
彼:我們是否可以說,對於那些生活在“新興”國家中的人們來說,你並不認為那裡有什麼進步?
巴:現在,就我所關心的問題而言,進步在未來。我覺得沒有理由為中國去爭取民主,我對此一點都不關心。當中國足夠富足的時候,它會變得民主的,就是這樣。這就是資本主義歷史本身,但不是我的歷史。一旦中國擁有了帶有巨大軍力的帝國主義式的生產能力時,它或許會與美國進行一場戰爭,這就是我們當年同德國的戰爭一樣,它最終將會讓自身變成一個議會制國家。今天的人類歷史太過相似。當你擁有了巨大的武力,擁有了不害怕進行戰爭的帝國主義式的支配性權力,你就可以建立一個政治體制。事實上,我們所謂的民主制度就是一種治理制度,它就是適應於當代最發達資本主義形式的治理制度。
彼:對於是否生活在中國的人們來說,還是有差別,難道不是這樣嗎?
巴:當然有差別。
彼:難道不是要去改善生活在那裡的人們的狀況嗎?
巴:正是因為有差別,所以這並不意味著在西方,資本主義就是一個標準。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仍然是一種資本主義形式。近些年來,美國人比中國人殺的人更多,例如在伊拉克。所以你不能帶著有色眼鏡來看問題。帝國主義權力就是那些擁有強大軍隊的權力。他們公開洗劫非洲——他們是掠奪者——在那些國家裡,他們收買了大量的公知。因此,對此一點也不令人驚奇。我對此一點興趣都沒有。所有這些都並沒有指向一個平等的方向,一個共同體的方向。那裡沒有任何東西關乎共產主義的觀念。而且,我認為這是有病。
彼:有病?
巴:我認為資本主義就是有病。這麼小的大陸攫取了如此眾多的財富就完全是野蠻之至。這就是有病,病得不輕。最終,所有人都認為中國病得越來越厲害,最終在某些我們已經認為會成為強大權力的前提之下,中國變成一個強權國家。因此,我對中國的發展一點興趣也沒有。中國變成了一個帝國主義式的強權核大國,支配世界市場,並掠奪著非洲,中國人已經開始這樣做了。隨後,它會與富有的中產階級聯盟。那會帶來移民——例如,非洲人到中國去。我對於世界上這樣一個力圖想變成和我們一樣的國家不感興趣。那是徹底的錯誤。沒有理由讓所有人變得和我們一模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