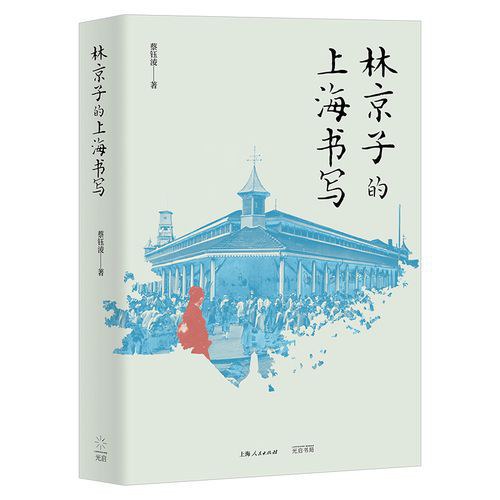本文為《林京子的上海書寫》序言及導論之書摘,獲作者蔡鈺凌授權轉載,原文刊於微信公眾號「謂無名」。本書圍繞日本作家林京子的生命歷程及其上海題材系列作品展開,作者嘗試還原林京子上海題材系列作品的創作脈絡與裂變過程,並參照日本社會的歷史文化脈絡、林京子個人生活史等,討論林京子的上海書寫所具有的能動性與時代意義,釐清她以「上海」主題表達文化與自我的具體內涵與過程,分別以《米歇爾的口紅》、《上海》、《預定時間》等作品為中心作了細緻的文本剖析和背景梳理。該書對既往林京子研究作了有意義的補充,注重挖掘林京子的個人生命、同代人的經歷,注重在歷史文化脈絡中分析林京子的文學創作,具有文化參考意義。
通過林京子聯結中國和日本——蔡鈺淩開拓的新天地
島村輝(菲利斯女學院大學教授)
本書是蔡鈺淩多年來通過對日本作家林京子的探討,所取得的關於中日文學、歷史、文化的研究成果。這部力作不僅本身成果豐碩,同時又呈現出林京子研究的廣闊前景。
鈺淩於2010年至2011年和2016年至2017年這兩個時期,作為外國客座研究員來到我就職的菲利斯女學院大學研究生院,進行研究學習。我記得鈺淩將林京子文學選為研究對象是在第一個時期,即她來到日本之後,在我的指導下開始的。正如本書介紹的那樣,林京子是 1945年8月9日在日本長崎市投下的原子彈的受害者,以獲得芥川獎的《祭場》(『祭りの場』,1975年)為代表,她書寫了大量關於核爆及其受害者此後人生的作品,她以「原爆文學」(原子彈爆炸題材文學)作家的身份為人所知。其次,林從幼年時代開始,長期生活在中國上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返回長崎,那段時期的體驗也成為構築她文學世界的極其重要的素材,再次,後來她跟隨到海外工作的兒子遠赴美國——投下原子彈的國家,在那裡接觸到當地的生活,也和當地人進行了交流。這也是影響林的文學的一個重要因素。因此,除了作為「原爆文學」作家外,林京子作為文學家的存在本身,亦受到大江健三郎、井上廈等同時代一流文學家同行的高度評價。
林女士是我長期關注的作家,即使是放到20世紀東亞的歷史中,她也算是一個擁有特殊經歷,並以此為素材進行創作的作家。她的住宅就在我家附近,一直以來我們通過當地的和平運動保持著聯繫。來自中國台灣的鈺淩將林京子的文學作為研究對象,意味著上文介紹的關於林文學的三大基本要素,有了從台灣這一新的視角切入的可能性,我作為指導教師從一開始就很關注這一點。
鈺淩在菲利斯女學院大學的研究態度非常熱忱和認真,我作為導師也從中受益良多。在她第一次在日研修期間,2011年3月11日,大地震和海嘯襲擊了日本的東北地區,東京電力福島第一核電站因此發生了包括燃料廠房爆炸在內的重大事故。這件事引發了放射性物質洩漏的問題,這與林氏長期思考、不斷言說的事情密切相關。在這場災難發生後不久,我有幸獲得一個機會,對林氏進行次基於其一生經歷的訪談(訪談結果見《生於被爆》[『被爆を生きて』],岩波小冊子第813號,2011年7月)。當這本小冊子出版後,我前往林女士家拜訪並彙報時,有機會向林女士引見了鈺淩。林女士為鈺淩的來訪感到十分欣喜,她們進行了親切而熱烈的交談。此次會面對得到全集簽名的鈺淩而言,其意義自不待言,在林女士心中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記得之後每次我見到她,她都會提起那次會面。
鈺淩結束在菲利斯女學院大學的第一次留學生活後回國,之後她不斷鑽研。其後,仍然是在我的指導之下,她在菲利斯女學院大學進行了第二次留學研究。我計劃再次帶鈺凌去林女士家拜訪,但林女士的身體狀況惡化,最終於2017年2月19日逝世。沒能如願與她再會,實為憾事。
第二次在日本的研究結束後,鈺凌完成了博士課程,並獲得了學位,其研究成果,即博士學位論文,如今出版成書。本書主要是通過追溯林京子的上海生活,探討她的中國體驗及其文學化的問題。近來,以中日兩國為首的青年學者對林京子的研究相當活躍,但就管見所及,至今還未有以中國(上海)體驗為主要素材的林京子作品被翻譯成中文出版。希望以本書的出版為契機,作家林京子既獨特又重要的地位能夠引起學界及讀書界更多的關注,也希望她的文學作品能夠在中國得到更多的介紹和接受。
我發自內心地為本書的付梓感到高興,同時由衷地期待鈺淩能在林京子的文學世界及相關的日本學研究領域,進行更深入和廣泛的研究。
寫於2024年8月9日,長崎被投下原子彈79週年日
導論
1930年,一個小男孩在上海租界出生,他是英國纖維公司負責人的長子。小男孩當然是英國人,但與一般的英國小孩不同,他是個在上海租界出生長大、接受教育的英國人。小男孩三歲時曾被宋靄齡接見,就讀上海大聖堂學校,居住在有游泳池和大草坪的西式豪宅,出入皆以高級私家車代步,家中還有數個幫傭的中國阿媽和雜工。小男孩還是一個飛機迷,在他眼中,日本人設計製造的零式戰鬥機是當時最厲害的戰鬥機,因此他手心裡總是揣著一架零戰的模型。
1941年12月初的某天,小男孩將自己打扮成海盜辛巴達,與父母一起去租界參加聖誕變裝派對。當小男孩乘坐的高級私家車從楊浦路駛向外白渡橋時,他望著沿途的街景——蹲在家門口乞討的中國老人、滿街狂奔的黃包車車夫、沿街叫賣活雞的中國小販、拍打著車窗對他不知講著什麼通關密語的中國少年、擠在外白渡橋口等待日軍檢查哨放行的中國難民、黃浦江邊的苦力,以及那用他完全聽不懂的語言所喧嘩出來的一片嘈雜。這個小辛巴達和他打扮成各式各樣童話人物的小夥伴們一臉懵懂,與車窗外的世界格格不入。
派對上,小孩們忙著玩耍嬉鬧,大人們則忙著交換戰事情報。小男孩父親的朋友跟父親表示,自己已先將家人送去新加坡了,建議他也先把家人送到他處避一下。但小男孩的父親卻猶豫不決,只決定先將家人安頓到旅館幾天。然而,就是在這個坐落於黃浦江岸的旅館,小男孩親眼目睹了日本戰艦「出雲」擊沈英國戰艦「彼得列爾號」(HMS Peterel)這歷史性的一幕。十年河東,十年河西。一夜之間,歐美在上海的百年勢力傾頹在黃浦江上,公共租界易主,日章旗就此在上海迎風飄揚。也是在同一晚,在黃浦江岸的另一頭,有一個日本小女孩在密勒路(今峨嵋路)自家的頂樓房間裡,與小男孩同一時間目睹了這個歷史巨輪轉動的場面。巧合的是,這個小女孩和小男孩一樣,也出生在1930年。這個英國小男孩名叫傑米,是美國導演斯蒂芬·斯皮爾伯格(Steven Spielberg)所執導的電影《太陽帝國》(Empire of the Sun)的男主角。這部電影改編自英國科幻作家J.G.巴拉德(James Graham Ballard)的同名自傳性小說,傑米正是巴拉德以自己為原型創作出來的人物。而另一頭的日本小女孩名叫宮崎京子,她正是在1975年以《祭場》一作榮獲芥川獎,並從自身的上海經驗出發,書寫出一組上海系列作品的作家林京子。而彼得列爾號被出雲號戰艦擊沈的那天,不用說,正是爆發珍珠港事變的1941年12月8日(美國時間12月7日)。太平洋戰爭就此爆發,日軍驅逐了上海租界的英美勢力,掌握了上海的統治權。
也是在那一天,巴拉德在逃難的過程中與父母失散,被關進了戰俘集中營,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後,他才得以重回父母的懷抱。然而此時這個為求生而在戰俘營中拼盡全力的小男孩,已和昔日那個天真稚氣的小男孩判若兩人。反之,成為上海新主人的「帝國日本」之一員的宮崎京子的命運又如何呢?於日本敗象漸露之際,在父親的安排之下,宮崎京子早在 1945 年2月底便與母親、姐妹們先行離開上海,返回長崎。然而在同年的8月9日,美軍在長崎投下原子彈「胖子」(Fat Man)時,宮崎京子卻在三菱兵器大橋工廠內,遭遇人類戰爭史上最殘暴的瞬間。此後,不管時間如何前行,這個小女孩的人生始終停頓在8月9日上午11點02分,難以前進,亦無法後退。
一、選題緣起
在此為何要花這麼長的篇幅,講述英國小男孩和日本小女孩戰前的上海經驗呢?當然不是想要凸顯他們兩人人生際遇與命運的偶然性和戲劇性(雖然的確如此),筆者主要想借此說明,本書嘗試處理的是一個什麼樣的「上海」。
(一)「上海」:三種上海敘述,三種敘述視角
本書中的「上海」,意指日本現當代文學中所指涉的「上海」。並且,這個「上海」不只是高杉晉作《游清五錄》中,那個西洋文明露骨地展現其先進性和侵略性的上海;不只是芥川龍之介《中國遊記》中,那個充滿「惡俗的西洋」的「蠻市」上海;亦不只是橫光利一《上海》中,那個隱含著殖民地都市、革命都市、底層都市三種向量(vector)的上海;更不只是村松梢風或井上紅梅筆下的「魔都」。本書要處理的是林京子筆下的上海,這個上海是有著林京子幼年生活記憶與「鄉愁」的生活場域,是有著眾多日本僑民的日本「外地」,是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者所定名的「租界都市」,是有四十多國人雜居的「國際都市」,是已然承載糅雜了自鴉片戰爭(1840)以來,日本近現代文學中所有上海意象的、具有總和性質的上海。
在林京子的上海系列作品中,林京子交叉呈現出三種敘述和三種上海論述視角。第一種是林京子透過孩童視角,試圖再現她記憶中的「我的上海」。這正是林京子記憶中的幼年生活場「密勒路」,以及從「密勒路」輻輳出去的「東洋人街」虹口與大上海。這個滿溢「鄉愁」的「我的上海」,在林京子被爆(指遭遇原子彈爆炸事件)後,成為一個暫時能夠安頓其身心的「至福」空間。第二種是在林京子寫作當下,重新被她接觸、講述與分析的上海。這又可再細分成兩個層次,其一是林京子在閱讀了大量相關資料後,以由此得來的事後知識,重新對幼年的上海經驗與記憶,做出歷史性的分析與檢證;其二是林京子在戰後兩次上海之行時,與久別重逢的上海再次碰撞後所描畫出的新中國上海圖像。第二種則是林京子借用前夫——林俊夫的上海經驗,以「另一隻眼」所勾勒出的1938年到 1948年,自己不在場的「大人的上海」。
可以說,林京子巧妙地以三種敘述視角——孩童視角、寫作當下的作者視角,以及借用自他人經驗的視角,表達出三種性質迥異的上海論述,進而以此呈現出一副變化萬千的上海面貌。這是在解讀林京子的上海系列作品時,首先必須謹記於心的。
(二)林京子:日本當代文學中的一朵異色凜冽的花
本書的主角——林京子雖然在漢語世界鮮為人知,但正如前述,她實際上與中國有著千絲萬縷的複雜關係。
林京子在1930年8月28日出生於長崎東山手町31號,舊名為宮崎京子。在她七八個月大時,因父親宮崎宮治就職於三井物產上海支店的緣故,舉家在 1931年4月移居上海。在宮崎家定居上海的近 14 年間,除了1940年到1941 年春(當時林京子為小學中年級生),因宮治被派往浦東支社而舉家搬至浦東的三井宿舍之外,其餘時間都居住在上海市密勒路281弄12號的英式煉瓦房。要特別留意的是,在密勒路這條弄堂裡,只有宮崎家一戶是日本人,其他住戶多數是中國人,且除了房東一家外,不少是像木工、小販、娼婦等諸如此類的底層庶民階級。
進入1945年,中日戰爭已到了關鍵性的決戰時刻,基於安全考量,宮崎家的女眷在該年2月底先行離開上海,返回長崎,獨剩宮治留在上海。在此之前,林京子除了曾在1932年一·二八事變和1937年淞滬會戰爆發前,兩度短暫回長崎之外,15歲前的絕大多數時間都是在上海度過的,包括她中學前的教育亦多數在上海完成。1945年3月初,林京子回諫早不久後,即轉入長崎縣立高等女學校(即中學)就讀。這其實並非林京子第一次在日本本土接受教育。第二次回長崎時,林京子曾短暫進入長崎市北浦小學校(即小學)就讀一學期,當時她是小學一年級的學生。不過這段「內地」就學經驗留給她的記憶不多,而1945年這次的入學則帶給她深遠的影響。在學徒動員開始後,林京子被編入三菱兵器大橋工廠。是年8月9日,她便是在大橋工廠內照射到原子彈的閃光的。
被爆之後,林京子保住了性命。然而,作為一個原爆幸存者,林京子不僅得面對許多生離死別,自己亦深受原爆症的威脅,特別是在結婚生子後,「母性」讓林京子深刻地察覺到此前被爆的後遺症,原來現在才正要拉開序幕,因為不只是被爆者本人終身都被壟罩在「內部之敵」的陰影裡,透過遺傳,還可能將「內部之敵傳給下一代。此外,日本對被爆者的排斥和歧視與日本政府不合理的相關政策,也讓林京子氣憤難平。
為此,林京子當時尚未離異的丈夫林俊夫鼓勵她提筆寫作,林俊夫設想或許借由寫作,能夠讓妻子稍稍撫平一下內心的恐懼與焦慮、憤怒與痛苦。就這樣,完全沒有做過一日文學夢、沒有當過一天文學少女的林京子,聽從了林俊夫的建議,走上了文學創作之路。1962年,林京子加入了保高德藏所主持的文藝雜誌《文藝首都》,成為該刊同人,同期加入的還有日後成為日本重要作家的中上健次、津島佑子等。次年10月,林京子以筆名「小野京」在《文藝首都》上發表了處女作《藍色小路》,開始了其創作練習期。往後數年,她每年都在《文藝首都》上發表一至兩篇作品。
1974年,林京子完成了以自身的原爆經驗為題材的短篇小說《祭場》,並得到了文學雜誌《群像》的青睞,於次年在《群像》6月號上發表。《祭場》的出現,可以說如同平地一聲雷,不僅讓林京子在1975年6月得到第十八屆群像新人獎,更在同年7月摘得第七十七屆芥川獎。就此,林京子躍上了日本文壇,成為當中一朵異色凜冽的花。
若粗略地概括林京子的文學創作,依據創作題材,大致可分為四個系列。
第一是原爆系列作品,此系列可再細分為兩種類別。其一是以《祭場》為代表的「八月九日」講述。在此類作品中,林京子從自身的原爆經驗出發,講述被爆者和生死相鄰的關係,講述幸存者終身無法擺脫「八月九日」及其所帶來的「內部之敵」的困境。借此,林京子反復思考人與戰爭、人與核之間的關係,最後做出人與戰爭、與核無法共存的結論。此類作品尚有《兩個人的墓碑》、《空罐》、《金比羅山》、《鑽石玻璃》等。其二是以《長久的時間換取的人生經驗》、《從特里尼蒂到特里尼蒂》為代表的反核講述。林京子認為,日本作為世界上唯一的被爆國,卻始終未能記取教訓,在戰後屢次讓日本國民陷入核災危機中。她痛斥這是日本政府對原爆記憶的忘卻,並以自身的原爆經驗為例,不斷地提醒日本不可重蹈覆轍。1999年,林京子前往世界首次進行核實驗之地——特里尼蒂核試驗場。特里尼蒂的參訪經驗除了讓林京子再次確認人與戰爭、與核無法共存之外,更是讓她重新確認了「加害—被害」這一重層結構。林京子指出,人類引爆原子彈除了加害自身,將自己變成被爆者之外,更是對大地/自然進行了無情的加害,大地/自然是始終默默地背負著這種「加害」的沈默的「被害者」。
第二是上海系列作品,此系列亦可再細分為兩種類別。其一是以《米歇爾的口紅》、《上海》為代表的上海記憶講述。林京子以幼年的上海經驗與記憶為基礎,勾勒出戰前日本人在「外地」生活的情況,同時,也勾勒出戰後這群從「外地」回到「內地」、從「帝國」回到「家」的「異鄉人」對「家」的不適症、對上海不被允許的「鄉愁」,以及漫長的戰後日本生活與新中國碰撞後所導致的「故鄉喪失」。林京子對上海的這種戒慎恐懼卻又無限依戀的心理,正是其筆下的上海圖像迴異於其他日本作家的上海主題作品之因。此類作品尚有《黃沙》、《回響》、《假面》、《啦啦啦,啦啦啦,》等;其二則是借用前——林俊夫的上海經驗,以「另一隻眼」去描寫自己不在場的「大人的上海」。此類作品有《NANKING——1940·秋》、《老上海》、《預定時間》。整體觀之,不管是哪一種類別,林京子都企圖以書寫上海來叩問自我,叩問戰後日本的歷史與戰爭論述。
第三是以《山谷》、《三界之家》為代表的女性與家庭系列作品。林京子透過對與林俊夫的婚姻、與父母子女之關係的思考,探問女性在婚姻和家庭生活中所面臨的問題與困境,並試圖從中尋找解脫的可能。此類作品尚有《幸福的 每日》等。
第四是以《橡木的桌子》、《弗吉尼亞的蒼穹》為代表的美國系列作品。由於兒子被外派美國,林京子在1985年到1988年長住美國,而美國正是原子彈「胖子」的原產國。三年的美國生活經驗拓展了林京子的眼界,讓她進一步思考日本「加害—被害」的重層結構、戰爭責任、戰後責任等問題。此類作品尚有《生存者們》、《長眠的人們》、《四照花開的小鎮》等。
誠然,上述對林京子的文學創作所做出的分類有過於粗略之嫌,也往往容易讓人忽略這四個系列之間所具有的交互作用、相輔相成之關係。不過,透過這樣的分類說明,還是較容易呈現出林京子的創作狀態、創作主題、創作方式以及她所欲表達的關懷,乃至她借由這些作品所描畫出的林京子文學圖像。同時,從中我們也不難看見林京子終身與自我、與戰爭、與核、與戰後日本的歷史和戰爭論述奮力交戰的過程,以及她從不退卻、不妥協、不輕言放棄信念的堅毅冷冽之姿態。正因如此,作家大江健三郎在替《林京子全集》撰寫推薦語時,才會將林京子稱為「無與倫比之人」。
(三)以「上海」叩問歷史與自我:林京子的上海系列作品
本書所要著重探討的是林京子的上海系列作品。
1969 年,林京子在文學雜誌《文藝首都》2月號上,以筆名「小野京」發表了散文《黃色水流》,這是林京子首次以上海為主題進行創作。而第一篇與上海有關的小說,則是同年在《文藝首都》12月號上發表的《維多利亞的箱子》。這篇短篇小說主要描寫主人公「我」一家戰前在「外地」上海、戰後回到「內地」日本生活的故事,換言之,「上海」只是這篇小說的主題之一。然而從這篇小說,其實已經可以看到林京子將上海書寫發展成一個創作譜系的可能性,因而日本文學研究者島村輝將此作視為林京子上海系列的萌芽之作。
至於林京子有意識地書寫上海,則要等到1977年,這年她分別在《群像》7月號與8月號上,發表了《黃沙》與《回響》。這兩篇後來被林京子收錄進原爆小說集《鑽石玻璃》(1978)的短篇小說,可以說是林京子正式經營上海系列的起點。此後,林京子兢兢業業地經營其上海系列,陸續發表了長篇小說《米歇爾的口紅》(1980)、《上海》(1983),短篇小說《賞花》(1981)、《假面》(1997)、《啦啦啦,啦啦啦,》(2006)等。除此之外,林京子還發表了不少與上海有關的散文,如《眺望街道》(全五回,1976)、《春光》(1977)、《上海的日本人們》(1983)、《在羊水中》(1985)等,更撰寫了不少與上海相關的評論,如《上海與八月九日》(1981)、《複雜的我的上海》(1995)等。除此之外,還有內容出現部分上海元素的作品,如散文《字典》(1979),短篇小說《虹》(1987)、《致大河》(1990)、《玩具箱》(1996),長篇小說《青春》(1994)等。
毫無疑問,上述提及的諸篇作品,都是林京子基於她15歲前在戰爭時代的上海中國人弄堂內生活之經驗所創作出來的。其中些更是兼及林京子其他的生命經驗,如原爆經驗、美國經驗、離婚經驗等。與此同時,林京子亦借用前夫林俊夫的戰前與戰後的上海經驗,創作出短篇小說《NANKING——1940·秋》(1983)、《老上海》(1992),以及長篇小說《預定時間》(1998)。換言之,林京子以近40 年的時間,孜孜不倦地編織出一幅名為「林京子的上海」的文學圖像,並且,這幅文學圖像具有超乎想象的複雜性與多元性。
此前,以自身的上海經驗作為創作題材的日本作家並不少見,諸如芥川龍之介、橫光利一、永井荷風、武田泰淳、堀田善衛等都曾留下無可取代的精彩之作。整體觀之,這些作傢具有一些共同點,即他們都是土生土長的日本人,在上海都只是短時間停留,且都是以成年男性的視角觀察上海。林京子不然。首先,林京子15歲之前的多數時間都在上海生活,也就是說在一個人人格養成最重要的階段,她都在上海。因此,林京子並非一般概念下的日本人,而是在中國大陸的風土養育下成長茁壯的日本人。她對上海的情感類似上海日本僑民中的「土著派」,「土著派」以上海為家,將上海視作「故鄉」。其次,林京子創作上海系列作品時,經常使用孩童視角,這在此前較為罕見。再次,相較於上述提及的日本作家立即對上海經驗做出反應,林京子是在經過30多年的沈澱消化後,才提筆書寫上海,進而勾勒出一幅她的「我的上海」。至關重要的最後一點是,中日「15年戰爭」這一林京子的生命底流,與她個人的原爆經驗、美國經驗、離婚經驗等,都階段性地影響了她觀看上海的方式與上海書寫的發展。
基於此,我們可以說,林京子筆下的「上海」不只是空間、個人經驗上的指涉,更是戰前夾纏在中日戰爭、戰後夾纏在中日關係等外在因素中,屬於林京子自身,但又同時纏繞在中日兩國之間的歷史創傷、戰爭傷痕、政治糾葛中的「上海」。並且,林京子對上海的詮釋,始終跟隨著外在事件與內在精神的變化而產生轉變。換言之,林京子筆下的上海具有因時改變的能動性。這種能動性讓林京子的上海系列作品不僅止於展露「鄉愁」,更暴露出夾纏在中日曆史夾縫中的「殖民者的傷痕」,以及中日兩國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糾葛,而這也正是林京子致力以「上海」叩問歷史與自我的「後果」。據此,我們不難看出林京子的上海系列作品,在日本現當代文學的上海書寫中所具有的特殊性與異質性。
二、先行研究綜述
目前關於林京子的先行研究,依據創作題材主要分為四大類分別是原爆系列研究、上海系列研究、女性與家庭系列研究、美國系列研究。其中,以原爆系列研究的成果最為豐碩,這毫無疑問地顯示出林京子研究的重心是在原爆系列作品上。而與本書相關的上海系列研究雖已有一些成果,但相較於原爆系列研究來說,仍屬邊緣。以下,筆者將把具有代表性的上海系列研究分成作者論研究、作品分類研究兩大類,分別加以述評。
(一)作者論研究
渡邊澄子是早期對林京子展開系統性研究的代表性研究者。在2005年出版的《林京子——人與文學:作為一個「看不見的恐怖」的講述者》一書中,渡邊分別從「林京子其人」、「林京子的文學」、「林京子的工作」這三部分,梳理林京子的文學創作歷程。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林京子的特殊人生經歷、這些特殊經歷對其文學創作的滲透與影響,以及以《祭場》躍登文學舞台的林京子的整體文學圖像。在上海系列研究方面,渡邊在討論原爆小說集《鑽石玻璃》時,同時概括了收錄於其中的上海主題之作《黃沙》與《回響》,她指出這兩作充滿了林京子對上海的懷舊之情。針對《回響》一作,渡邊認為林京子雖然如實呈現出當時作為「帝國日本」中的一員對戰爭勝利的興奮,但還不太成熟,尚未找出處理這種侵略者的興奮與她自身的上海懷舊之情的方式。而在「林京子的文學」中的第六章《懷念的故鄉上海》,渡邊著重討論了《米歇爾的口紅》一書。渡邊指出,上海時代確實是林京子人生中的「陽」,且這與她被爆後所背負的「負」是互相纏繞的。因此,渡邊認為,如何通過文學表現戰爭的總體是林京子文學創作的重要課題,並表示林京子在這部分還需要很多的努力。
2009年,渡邊與她所指導的意大利籍博士生蘇里亞諾·曼努埃拉(Suriano Manuela)共著的《林京子——人與文學》一書出版。本書分成兩部,第一部是《朝向暴露「看不見的恐怖」的二十一世紀》,這是渡邊修改增補自上述的《林京子——人與文學:作為一個「看不見的恐怖」的講述者》一書;第二部則是《對「人類滅亡或放棄戰爭?」的追究——林京子文學的世界》,這是曼努埃拉博士論文的一部分。
渡邊主筆的第一部分成12章。渡邊以極具特色的女性視角,分析林京子及其作品,加上她以林京子的生平經歷作為時間軸的章節安排,這一部分幾可視作一本林京子的傳記。其中,針對林京子的上海經驗和上海系列作品的討論,所佔篇幅不多,只有兩章,分別是第一章《林京子的成長史——上海成長的特殊性》、第五章《「我的上海」的光與影》。
在有限的討論中,渡邊強調的重點有三。一是強調林京子成長的上海是一個與當時中國其他城市不同的特殊空間,並指出上海經驗對「歸國子女」林京子具有正面的機能;二是指出在上海經驗與長崎被爆經驗的雙重疊加下,林京子更加深刻地體會到處在中日兩國的夾縫中時,個人不得不面對的糾葛與掙扎,這無疑拓展了她的創作內涵,使她的作品不流於平面刻板;三是渡邊試圖以《米歇爾的口紅》與《假面》這兩部作品,討論林京子對個人與戰爭、個人與國家之關係的思索。她指出,隨著時間的推移,林京子的上海書寫在筆致上和視角上,逐漸排除了感傷的、感情的、情緒的面向,這最終使林京子得以做出自己亦是「大日本帝國」的成員這一反省。讓人稍感意外的是,渡邊將林京子的《預定時間》歸入女性與家庭系列作品中討論。渡邊的這一選擇雖然展現出她強烈的個人研究特色,卻也讓林京子上海系列作品的討論出現了一大片空白,殊為可惜。
曼努埃拉撰寫的《林京子——人與文學》的第二部除了序和結論之外,正文共有八章。第二部的整體結構大致與渡邊執筆的第一部相同,討論的文本亦具一致性,但曼努埃拉以更具學術性的論證與書寫方式,對林京子的作品進行分析與檢討。同時,她對林京子上海系列作品的討論也更為詳細。
在第五章《上海系列作品》中,曼努埃拉以《米歇爾的口紅》、《上海》、《黃沙》、《回響》為討論對象,指出林京子在這些作品中,極為精巧地描繪出個人被國家權力卷人戰爭時的狀態,甚至連孩童也無法不被鑲嵌進這種由上至下的國家權力結構,成為侵略國的一員。因此,曼努埃拉認為,林京子的書寫真實地反映出當時的上海日本僑民在面對戰爭時的感受與知覺,以及深陷於其中的複雜性。
曼努埃拉同時也指出,雖然從這些作品可以看出林京子對上海充滿了鄉愁,但這份鄉愁含有不安,還混雜了反省的情緒。因此,林京子原本「陽光燦爛」的上海產生了質變,朝向「負」移行,這致使她對上海的想念,從純粹的思鄉變成必須打上引號的「鄉愁」。然而,也正是這一轉變過程讓林京子得以重省上海經驗,並借此重新對整個戰爭展開思考與檢討。最後,曼努埃拉亦不忘強調,林京子的原爆經驗與上海經驗是彼此交相作用的,不可分別視之。她認為正是這種交相作用,才讓林京子不單從原爆受害者的角度,而是能從更廣大的「人」的立場出發,重探人與戰爭、人與核的問題。
曼努埃拉較為清楚地分析了林京子上海系列作品的重要性,並指出此系列與原爆系列作品所具有的交互作用,這對一直以來將這兩個系列分別討論的既有研究範式,做出了重要的提醒與修正。此外,曼努埃拉提到了林京子觀看上海的目光會隨著時間而有所轉變,但她並未處理到《預定時間》、《啦啦啦,啦啦啦,》等上海系列後期作品,也沒有考慮到外在事件、美國經驗等對林京子所造成的影響,這使得曼努埃拉無法完整地釐清林京子上海「鄉愁」的變化路徑,亦無法更具體地討論林京子最終的「故鄉喪失」。
2007年6月,黑古一夫的《林京子論:「NAGASAKI」·上海·美國》一書出版。正如該書的副標題所示,黑古是依照林京子的創作主題與時間,依序將林京子的文學創作分成「NAGASAKI」(長崎)、上海、美國三部分來加以討論的。和本書有關的是第二部《上海》,該部分成三章,分別是《另一個原點·上海》、《三十六年後的上海》、《「未竟之夢」——上海》,主要涉及的作品為《米歇爾的口紅》、《上海》、《預定時間》。
黑古認為,林京子的上海經驗讓她養成了一種迥異於日本人的身體感覺、思考方式與大陸感性,並建立出一套以「對等·平等」為基底的人生觀。這種教養、生活經驗與被爆經驗相互作用的結果,就是使林京子得以排除狹隘的大和民族主義,進而以「人」作為思考的起點,重省戰爭問題。因此,林京子能精准地指出,長崎原爆的起因在於此前日本對外發動的一系列戰爭。不過,也因這種加害者的自我認識與中國崛起後所產生的民族自信,讓林京子不斷地被侵略者的罪惡感所拷問,最終導致她喪失了美好的上海。
要特別注意的是,黑古是少數論及《預定時間》的研究者,他將此作視為林京子的上海鎮魂歌,亦是她對婚姻生活的總結。黑古表示,林京子在這篇作品中,未使用慣用的私小說創作手法,而是將以前夫為原型的人物作為主人公,這意味著林京子在「故鄉喪失」後,必須透過他人的經驗才得以重新定義「上海」。同時,黑古還進一步指出,若從林京子的創作內核「戰爭」這一層面來思考,亦可看出林京子試圖透過此作思索一個問題,即若是再次遭遇戰爭,已經長大成人的自己該何去何從。
熊芳的碩士論文《原爆受害作家林京子之上海經歷的文學意義——以〈米歇爾的口紅〉、〈上海〉、〈預定時間〉為中心》,是中國少見的以林京子的上海經驗為研究對象的學位論文。到了博士階段,熊芳繼續探索林京子的文學創作,並在 2018年將其博士論文出版為《林京子的文學——生在戰爭與核的時代》一書。相較於碩士論文,熊芳擴大了討論範疇,從頭整理了林京子的文學創作樣貌,欲以此重新勘定林京子在日本戰後文學史上的位置。其中,與本書直接相關的是第一章《上海(戰爭)體驗》。該章主要以《米歇爾的口紅》、《上海》、《預定時間》為討論對象,是她對碩士論文的增補與修改。
熊芳的研究深受黑古的影響,不少論點可說是對黑古的繼承與深化。相對於黑古評論式的寫作方法,熊芳採取系統性、學術性的方式,對林京子的上海系列作品進行研究分析,並以此對黑古的論述進行補白。與黑古相同,熊芳亦強調不可將林京子的原爆經驗與上海經驗切割討論,兩者是互為表裡、相輔相成的,並進一步指出,林京子作品中出現的「加害—被害」重層結構,與林京子的上海經驗有關。她認為,從《黃沙》與《回響》兩作,已可見林京子具有身為加害者這一自我認識,而透過對《米歇爾的口紅》、《上海》、《假面》、《預定時間》的分析,則可更清晰地看出這一自我認識的形成與變化的經緯。此外,熊芳特別強調宮崎家「恥」的教育,及這種教育在林京子自我認識的形成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並以此圍繞戰爭重探加害者與被害者之關係。
熊芳仔細地梳理了林京子上海系列作品中的「加害—被害」問題,這是其研究的重要貢獻。不過,由於熊芳的分析方式局限在文本內部,而林京子卻是一個與外部世界互動頻繁的作家,僅局限在文本內部討論會無法清楚說明林京子創作的一些關鍵性轉變。此外,熊芳始終強調林京子的加害者意識始於上海經驗和宮崎家「恥」的教育,但如此其實難以解釋在林京子刻意壓抑之下,卻還是溢出的「鄉愁」。
井上聰與上述研究者們一樣,也認為不可將林京子的原爆經驗與上海經驗分別觀之,因而他在《林京子與上海——以「生」與「死」為中心》一文中,以《米歇爾的口紅》與《上海》為主要討論對象,試圖從林京子及其父的瀕死經驗出發,重新探問「上海」之於林京子到底意味著什麼。井上指出,對與「死」緊密相鄰的林京子而言,「上海」是她唯一的「生」,亦是讓她意識到「生」與「死」的場所,同時也是她凝視過去的「生」到現在的「死」的特殊場域。井上跳脫了既定的上海=「故鄉」這一論述,改就「生」與「死」這一角度,定義林京子筆下的上海。
黃珺亮的《話語的政治:暗藏於林京子的弄堂中的美國勢力》是近年頗為新穎的林京子上海系列作品之研究。在論文中,黃珺亮首先指出,以往研究者們在討論林京子的上海系列作品時,多數採用中日二元性的視角,忽略了流動在其間的美國勢力,因此她對滲透於「東洋人街」虹口的美國勢力做出具體分析,嘗試以此打破這種中日二元性的研究範式。再者,她指出由於林京子身處在後殖民理論興起的時代,這讓林京子在短篇小說《致大河》中,得以將美國新奧爾良的被殖民經驗視作一種鏡像,借此重新掌握上海租界的殖民構造。最後,她認為在中日剛恢復邦交之際,兩國之間具有協力、連帶的政治氣氛,加上美日之間冷戰敘述話語的限制,讓林京子並未以後殖民批判的角度創作《米歇爾的口紅》,而是以「人性」作為敘述策略,欲以此超越國籍、階級和人種的「同伴意識」,在密勒路中建構出一個「烏托邦」。
黃珺亮的研究提醒我們,在研究林京子的上海系列作品時,必須將其置於更大的歷史背景、冷戰結構乃至當代思潮中,才得以更完整地對其進行分析。同時,她亦提醒我們不可忽視流動在「東洋人街」虹口的美國勢力,這些都使人深受啓發。不過,黃珺亮在論及林京子上海系列作品中的後殖民批判問題時,預設了一個立場,即確信林京子是一個自始至終都具有後殖民意識的作家,但對此確信卻無具體分析,這除了有概念先行的危險之外,也失去了對林京子反復強調的「鄉愁」情結進行有效分析的可能。此外,在討論林京子弄堂論述的轉變時,並未具體分析最明顯表現此一轉變的《假面》與《啦啦啦,啦啦啦,》,稍顯可惜。
山崎信子的《圍繞林京子〈黃沙〉中的日本娼婦:「明明是日本人」》則是少數以林京子的短篇小說《黃沙》為研究對象的單篇論文。山崎嘗試以原爆文學研究者川口隆行就原爆文學中被害與加害的討論,以及法國學者艾蒂安·巴利巴爾(Etienne Balibar)的國家內部排斥機能理論來解讀《黃沙》,並提出了嶄新的詮釋。在論文中,山崎從人種主義、階級意識、內部排斥、性別出發,認為林京子借由日本娼婦阿清的遭遇和自身的原爆經驗,對「日本人」這一全體性概念提出質疑,討論這個概念所含有的暴力性,企圖從日本內部對日本做出批判。同時指出,性別與性慾在小說中的機能也是林京子的側重點。此外,針對林京子的原爆經驗與上海經驗的不可切割性這點,她亦做出提醒。山崎的研究頗為成功地結合了林京子的原爆經驗與上海經驗,不僅立意深遠,具有現實關懷,更賦予了林京子研究一個新氣象,讓人深受啟發。
(二)作品分類研究
2008年,日本立命館大學國際言語文化研究所舉辦了連續講座「國民國家與多文化社會」。在其中的「帝國的孤兒們——日本與作家」第三回「亞細亞——上海的養女們」專場上,菅聰子發表了《林京子的上海·女人們的弄堂——庇護所的幻想》一文,討論林京子的「養女」身份。
菅聰子主要以《米歇爾的口紅》為中心,分析作品中由中日兩國女性在密勒路共同搭建出來的「庇護所」的幻想性質。菅聰子指出,這個「庇護所」在中日戰爭加劇後越發不穩,逐漸暴露出維持這一「庇護所」存在的「恐怖的平衡」。透過分析這一「恐怖的平衡」,可看出弄堂內所存在的雙重結構與來自「帝國日本」的視線,以及由此導致「庇護所」漸次分裂之過程。營聰子同時認為,「上海」是林京子以含有幻想性質的上海記憶所建構出來的「故鄉」,而這個經驗卻也讓林京子被真正的「祖國」日本視為「養女」。據此,她提出,若從林京子的邊緣身份和林京子文學中隱含的漂泊性、流浪性出發,對林京子及其文學創作進行探索的話,或可讓今後的林京子研究出現新的可能。
菅聰子對弄堂內的雙重結構與帝國視線的分析,以及對今後林京子研究的可能方向所給出的提示,讓人深受啓發。然而在討論弄堂內的雙重結構時,菅聰子沒有對弄堂內的被侵略者/被支配者側的視線進行分析,而這種視線在《米歇爾的口紅》中,其實已有部分呈現,到了林京子上海系列的後期之作中,則越發清楚。倘若菅聰子能將後期作品納入討論的話,或許能更加提升論述的層次。
上海日僑史研究者高綱博文在《「國際都市」上海中的日本人》的第八章《上海日本人歸國者的懷鄉情結——「我的故鄉·上海」的誕生》中,曾論及林京子的上海系列作品。高綱從上海日僑社會史這一角度出發,以上海歸國者為研究對象,探討他們「上海懷鄉情結」的生成與論述方式,以及「上海懷鄉病」的蔓延情況。在高綱的歷史研究中,林京子作為一個案例登場。高綱指出,強大的挫折感和喪失感,導致上海歸國者們在回國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對上海經驗呈現失語狀態。然而,在中日恢復邦交的刺激下,埋藏在他們內心深處的上海記憶死灰復燃,尤其是上海歸國者第一代的子女們,而林京子正是其中最早公開使用「我的故鄉·上海」這一說法的上海歸國者第二代。高綱同時亦指出,林京子的《米茜露的口紅》(即《米歇爾的口紅》)和《上海》兩書的出版,更是觸發了上海歸國者們的懷鄉情結,使上海懷鄉情結成為一種「流行病」。
由於高綱在上海日僑社會史這一脈絡下展開研究,僅僅將林京子作為社會史中的一個現象和案例提出,所以並未對其文學作品內涵進行深究。懷鄉作品都是經過再構築的,裡頭含有「記憶與忘卻」的成分。不過高綱認為,林京子和其他上海歸國者所撰寫的的這一說法,對一向將林京子的文學創作等同於她自身經驗的既定研究習慣來說,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提醒。
而針對這種「記憶與忘卻」,韓國的日本文學研究者朴裕河則在《遣返文學論序說——朝向新後殖民主義》一書中,提出了「遣返文學」這一嶄新的文學史概念,企圖建立一個遣返者文學系譜。朴裕河所言的「遣返文學」,意指日本戰敗後,從中國東北、上海,以及朝鮮等「外地」被強制遣返回國的日本人所撰寫的文學作品,內容主要是他們的殖民地經驗和遣返經驗。朴裕河認為「遣返」這一概念,除考慮了佔領地和殖民地的關係之外,亦涉及了「內地」與「外地」的關係。這群身懷強烈的「異鄉人感覺」的遣返者表面上是回到了「內地」,但在他們被「帝國崩壞的日本」同化的同時,「帝國」的記憶卻仍然清晰地存在,因此他們始終與「戰後日本」格格不入。在此意義上,這群遣返者可說是戰後日本精神離散(diaspora)的代表。同時,朴裕河更進一步指出,遣返者文學或可讓以「定居者」中心主義為主軸的日本現當代文學進行重組,掃除日本近代文學研究的閉塞感。
在《遣返文學論序說》中,朴裕河僅先處理了身為朝鮮遣返者的三位日本作家——小林勝、湯淺克衛、後藤明生,尚未對遣返者文學展開全方面的整理與檢討。而在該書第一部「總論」的《被拋棄的殖民地·帝國後體驗——「遣返文學」論序說》中,朴裕河提到了林京子。朴裕河認為,林京子在日本戰敗前就已經先行返日,不算具有戰後遣返經驗,但是林京子近14年的上海生活讓她確確實實是佔領地上海的「帝國之子」,因此她強調,林京子雖不具戰後遣返經驗,但仍必須討論她的殖民地經驗,且在討論時,還必須結合她的原爆經驗一並來談。根據上述,我們不難發現林京子在遣返文學系譜中所具有的特殊性與異質性,此後樸裕河將如何處理林京子這一特殊個案,值得繼續觀察。
在和田博文、黃翠娥主編的《作為「異鄉」的大連·上海·台北》一書中,則分別以大連、上海、台北這三個佔領地都市為舞台,討論「外地」日本人的主體認同。從和田博文、橫路啓子、小泉京美三人座談的整理中可發現,在不同的歷史背景、治理政策、都市被賦予的角色以及具體的事例之下,根據時代、地點、世代的不同,前往「外地」的日本人對「故鄉」和「異鄉」的思考與感覺也會產生歧異。
在該書中,林京子作為上海日本僑民第二代的唯一代表,被提出討論。石田仁志在《林京子——作為異鄉/故鄉的上海·〈米歇爾的口紅〉、〈上海〉》中,以《米歇爾的口紅》與《上海》兩部作品為中心,探討林京子曲折的故鄉認同。石田指出,上海曾被林京子視為「故鄉」,但事後對日本殖民戰爭歷史的認識及與此伴隨而生的自責(或羞恥),讓林京子發覺這是一種「不被允許的鄉愁」,上海不得不成為「異鄉」。然而,在納入原爆經驗後,林京子不斷地在「長崎的死」與「上海的生」兩者間反復穿梭,最終在其上海系列作品中,以「講述的自己/被講述的自己」這種敘述二重性,展現出自身「死與生/陰與陽」的生命斷裂,以及在故鄉和異鄉這兩種異質概念中交相流動的上海。借此,林京子得以重探戰爭。
大橋毅彥則是長久以來,對上海史、日本人的上海經驗抱持濃厚興趣的研究者。在大橋與他人共著的《言語都市·上海1840—1945》中,可見他特別關心具有上海經驗或相關創作的作家。大橋在其專著《昭和文學的上海體驗》中,延續了這一關心,他以 20世紀20年代後半到1945年間的上海為主要研究場域,討論的文本從文學作品擴展至美術創作、劇場、報刊、大眾傳媒等。大橋嘗試以此討論在多種語言、民族、文化重疊交合下的上海所產生出的昭和文學與文化,究竟具有何種可能。在該書第三部《從國體流出的心》中,大橋以池田みち子、林京子、堀田善衛為例,嘗試以他們的作品討論從「國家」這一政治載體內溢出的「心」,進而思索個人是否具有超越「國體」的力量與可能。
討論林京子的部分為該書的第九章、第十章。在第九章《來往與嚴拒——林京子〈米歇爾的口紅〉的世界》中,大橋透過對《米歇爾的口紅》的分析,指出林京子在此作中對上海時代的記述存在不少記憶的錯誤與欠缺。究其原因,主要是林京子想要打造出一個能夠證明自己的生的世界。並且,林京子更在其中打造出一個現實無法侵入的空間「小孩的房間」。在這個「小孩的房間」中,主人公「我」與上海弄堂裡的中國小孩們打成一片,融合在當地的自然風士中,由此獲得至福。然而大橋指出,實際上從「小孩的房間」看出去的景象,具有「來往」與「嚴拒」的雙重性,而導致這種雙重性的原因,就是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的權力階級關係。在第十章《自責與自尊——讀林京子的〈預定時間〉》中,大橋則試圖處理鮮少被處理的《預定時間》。大橋將這篇以回憶錄形式展開的小說視為安魂曲,認為林京子企圖透過一名日本記者的生命經驗,重新思考中日戰爭,以及在戰爭中,理想被政治偷換了的日本青年的自責與自尊。
此前的研究者們多數將《米歇爾的口紅》看作林京子的個人自傳,經常不證自明地將小說情節等同於林京子的個人經驗,這其實是研究林京子的上海經驗時,不可忽視卻又最容易被忽視的部分。林京子在作品中呈現出的上海記憶為何會出現大橋所言的錯誤與欠缺?出現錯誤或欠缺後的上海記憶為何?而這又導致了何種結果?釐清這些問題將有助於我們更好地分析林京子上海「鄉愁」的變化,以及這個變化在其上海系列作品,甚至整體文學創作中所產生的影響。倘若由此向外擴展,甚至還可進一步去思考如何分析虛構文學中的「真實性」問題。由此足見大橋的提醒與嘗試之重要性。
總的來說,首先,目前對林京子文學創作的研究,在作者論研究部分,多數將林京子的創作分成原爆系列作品、上海系列作品女性、家庭系列作品、美國系列作品四大類討論,且研究成果的分布極度不均,多數集中在原爆系列作品上,對本書主要涉及的上海系列作品的相關研究偏少。與此同時,在為數不多的上海系列作品的研究成果中,同樣存在分布不均的問題。研究者們偏重於討論《米歇爾的口紅》,對上海系列的其他作品卻有所偏廢,特別是晚期作品。基於此,我們有必要對林京子的上海系列作品進行全面性的細讀與分析,如此才能釐清林京子上海論述的全貌。
再者,目前在研究林京子的上海系列作品時,主要是以黑古一夫的論述架構為基礎。誠然,黑古的論述架構與分析方式給予了我們諸多啓發,但尚具有調整與深化的空間,比如:林京子是在何種契機之下,開始書寫上海的?上海書寫對林京子個人而言,究竟意味著什麼?該如何解釋她筆下的「上海」圖像?三部長篇小說中的「上海」圖像為何會如此不同?造成這種不同的因素為何?林京子的上海書寫與歷史、與現實的關係又是什麼?這些林京子上海系列作品的關鍵性問題,迄今都尚未被提出與處理。2005年6月,日本圖書中心出版了《林京子全集》(後簡稱《全集》)。全集的出版使得林京子的相關文學資料更趨完整、健全,這賦予了我們重啓林京子上海系列作品研究之可能性。
最後,雖然不少研究者都曾再三強調必須整合林京子的原爆經驗與上海經驗,但在實際操作中,卻呈現出心有餘而力不足的困境。並且,此前的研究多數著重於文本內部的討論,忽略了戰後日本的反核運動、原爆文學論爭、冷戰政治局勢、當代社會思潮、東亞的戰爭遺留問題等外在因素對林京子的文學創作所產生的具體影響,然而林京子實際上是一個與現實世界互動頻繁的作家,她的思考與文學創作和現實脈絡緊緊捆綁,包括她的創作轉折,也都是在這些外在因素的影響與推動下出現的。要而言之,在現實脈絡中詮釋分析林京子的文學創作,是目前在研究林京子時,亟須調整與補充的一個重要面向。此外,作品分類研究部分雖然顯露出研究者們對上海這一場域與林京子上海經驗的關心,展現出各自的研究方法和論述特色,屢屢出現深具啟發性的見解,但也正因為是作品分類研究,研究者們往往只攫取出與自己的研究主題相關的部分進行討論,無法將林京子的上海系列作品置於林京子文學的整體架構中思考,這是作品分類研究的局限性。
基於上述,我們不難得知目前對林京子上海系列作品的研究、尚有許多待解的謎團和值得深入擴展的面向。此外,中文學界對林京子上海系列作品的研究只是零星出現,這也足見我們尚有許多努力的空間。
三、研究方法
本書將聚焦於林京子上海系列作品,進行分析討論。
首先,林京子上海系列作品的創作量大約佔其總創作量的四分之一,若加上內容涉及上海,但不以上海為主要內容的小說,以及相關的散文、評論、演講稿、採訪等,大概可佔到三分之一。本書主要以這個部分為研究側重,並特別著重於其中的三部長篇小說《米歇爾的口紅》、《上海》、《預定時間》。此外,由於林京子同時發展好幾個創作系列,不同系列的作品之間經常具有某種內在關聯,所以在討論的過程中,也將部分旁及其他系列的作品。換言之,本書將從林京子的文學全貌出發,觀照林京子的上海書寫在其文學全貌中所具有的位置與作用。如此,不僅是對此前研究者們所提出的必須整合檢視林京子複數的生命經驗之提醒的具體落實,也是本書與相關先行研究較為不同之處。
其次,由於此前對林京子上海系列作品的文本解析極為不足,本書將採用作家論與作品論結合的研究方式,通過文本細讀(close reading)與歷史脈絡(context)爬梳,重探林京子的上海系列作品,進而試圖以此梳理出林京子以「上海」與「帝國日本」和「戰後日本」進行對話,並質疑以遺忘「帝國記憶」來和「帝國日本」進行切割的「戰後日本」與「戰後終結論」的路徑,勾勒出她以「上海」叩問歷史與自我的過程與脈絡,探尋出她欲以「上海」應戰的對象與內心的詰問。換言之,本書將從戰後日本社會的歷史文化脈絡出發,檢視林京子上海系列作品的當代意義與時代價值。
最後,通過上述研究側重與研究方法,本書試圖還原林京子上海系列作品的創作脈絡與裂變過程,並參照戰後日本社會的歷史文化脈絡、中日關係的消長變化、林京子個人史等,來討論林京子的上海書寫所具有的能動性與時代意義,釐清她以「上海」叩問歷史與自我的具體內涵與過程,及其所導致的「故鄉喪失」,最終進步嘗試以林京子的上海系列作品及其「殖民者的傷痕」,重探殖民者真正脫殖民、被殖民者徹底去殖民的可能。
四、本書架構
本書共有七個部分。
導論主要概括本書的選題緣起、選題範圍、主要問題意識、研究方法,以及對先行研究進行述評。
第一章旨在梳理林京子上海書寫出現的脈絡與原因。雖然林京子在1969年即已發表描寫上海時代的散文,但著手寫以上海時代為主題的小說,乃至形成一個創作譜系的雛形,至少要等到20世紀70年代下半葉。林京子從70年代下半葉開始有意識地書寫上海的契機為何?70年代下半葉又是如何讓她產生出系統性書寫上海時代的想法的?
第二章擬以林京子上海系列作品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米歇爾的口紅》(1980)為中心,旨在討論林京子如何建構出其上海系列作品的地基——「我的上海」,以及這個「我的上海」在林京子上海系列作品中具有何種作用或機能;而透過描繪「我的上海」,林京子究竟想要表達什麼;她的應戰目標為何。
第三章擬以林京子上海系列作品的第二部長篇小說《上海》(1983)為中心,旨在討論林京子在1981年重新踏上暌違了36年的上海時的心路歷程。透過對新中國的觀察,並將此與她記憶中的「我的上海」互做比較後,林京子清楚地體認到新中國的上海已非她心目中的「我的上海」,就此「故鄉」變「他鄉」,林京子的上海「鄉愁」也隨之產生了變化。而透過這部新中國遊記,林京子更進一步要探問的現實關懷是:中日兩國之間大和解的可不可能,真正友好的可不可能。
第四章試圖梳理林京子上海系列作品中「另一隻眼」的生成軌跡,釐清從林京子慣常的創作路徑中乖離出來的《預定時間》出現的原因。在「另一隻眼」的生成過程中,在《控訴核戰爭危機的文學者聲明》連署運動、第三次原爆文學論爭、美國三年的生活、中日關係的再建與急轉直下、國際冷戰結構重組,以及20世紀80年代後殖民理論的流行、戰爭責任問責等外在事件的交互影響下,亟欲重新探問歷史的林京子最終連只存在於她的記憶與自然風士中的「我的上海」也無法保住,徹底陷入「故鄉喪失」之境。此後,林京子只能改以前夫林俊夫的上海經驗作為「另一隻眼」,重省上海進而勾勒出林京子不在場的「大人的上海」。
第五章擬以林京子上海系列作品的最後一部長篇小說《預定時間》(1998)為中心,旨在討論林京子為何又如何借用前夫林俊夫的上海經驗,描寫出她不在場的1938年至1948年的「大人的上海」。林京子以第二次上海之行(1996)中,又一次被上海拒絕之經驗作為內在的基底,在戰後中日關係最低潮之際,嘗試以此作叩問中日之間複雜曲折的歷史,思考自己兩次被上海拒絕的歷史成因。同時,透過對戰前歷史大敘事的追索,以及對在帝國日本的「偷換理論」下最終敗北的日本青年的個人小敘事的描繪,林京子嘗試思考當前中日關係所面臨的困境與突圍的可能。
結語部分旨在透過對林京子上海系列作品的分析與研究,以及林京子在「漫長的戰後」中以「上海」、以自身的「殖民者的傷痕」叩問歷史與自我的拼搏姿態,闡述筆者從中所得到的啟發、提醒與未來研究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