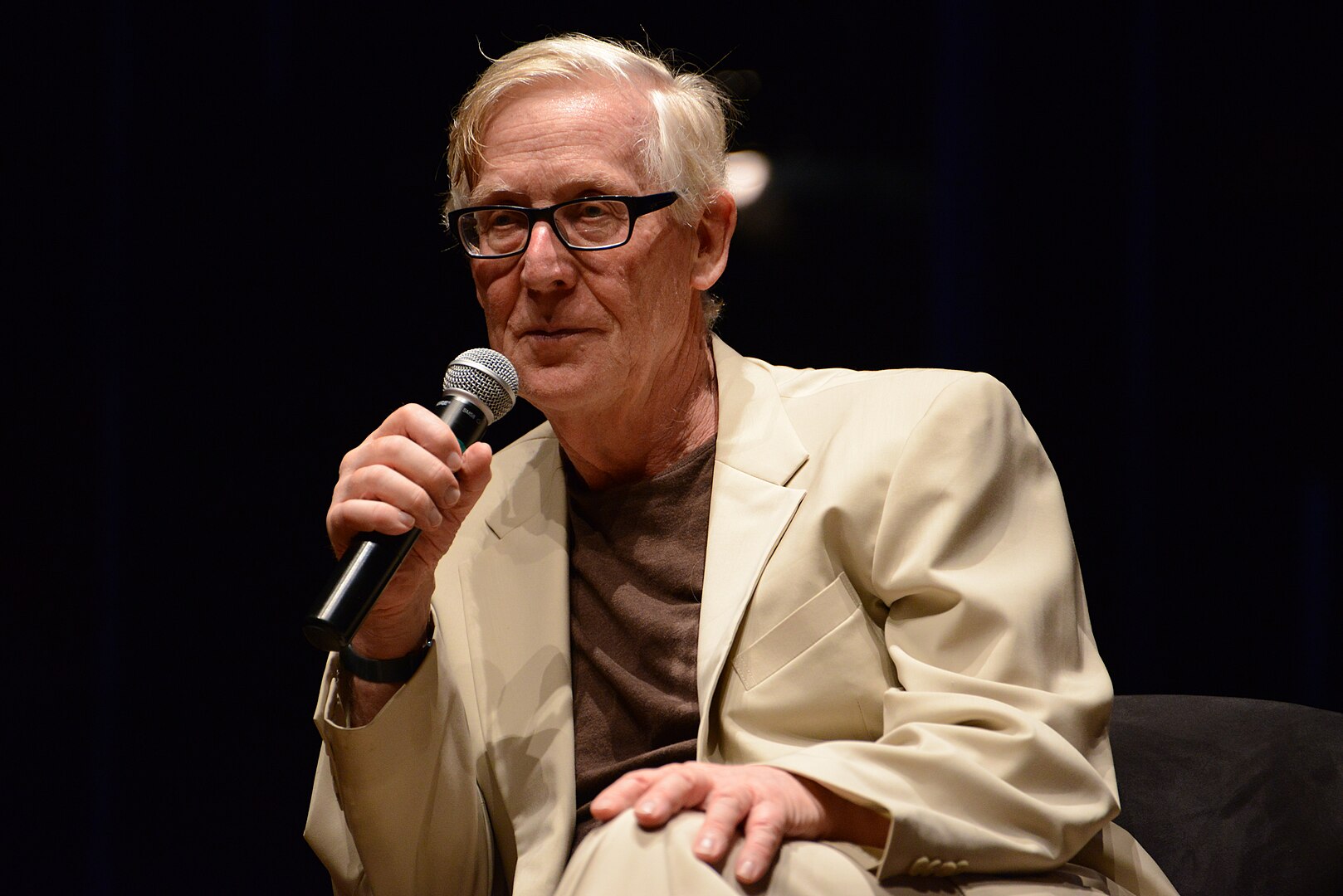本文原刊於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新國際獲作者授權轉載。
【摘要】佩里·安德森指出,所謂「國際法」乃是歐洲中心主義的產物,並常為帝國強權所用。認清這一事實後如何接著思考,以回應世界和中國當下的各種思想與問題顯得尤為重要。回顧歷史,中國第一批現代思想家如王韜、楊度、嚴復等在倡導向西方學習時,並未將西方視為文明最優代表,而是充滿困惑與矛盾。張君勱、梁啓超等則開始重新思考中西文化關係,思想焦點轉向 「是否有可能改變世界的野蠻規則」,魯迅、孫中山等則提出避免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變成 「獸性愛國者」 的方法。現在看來,現代早期中國思想的理想並未完全實現,當今世界仍然呈現 「野蠻化」 趨勢,但越是如此,越不能因他人 「野蠻」 而放棄追求 「文明」和全球正義。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教授演講的主要內容,令人信服地指出,目前通行的所謂「國際法」,從它誕生的時候起,就是歐洲中心主義的,因而並不具備體現國際正義的能力,反而常常成為各種類型的帝國主義強權的工具。
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認清了這個事實之後,怎麼繼續往下想?這個問題,對於我們中國人尤其顯得尖銳。一百多年來,我們一直主要是通過向「西方」學習來謀求中國自身的現代化的,無論是學習歐美,還是學習蘇聯,都是學習「西方」。① 可是,在持續向西方學習的同時,越來越多的中國人也逐漸清楚地意識到,在不少方面,「西方」其實是相當糟糕的。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思想會不會被搞亂,走到另一個極端?比方說,我們會不會覺得,向西方學習是搞錯了方向,今後應該返回「東方」,返回「中國」,我們自己的這一套才是最好的?②再比如,我們會不會覺得,什麼國際正義、世界和平,統統都是胡扯,叢林法則、弱肉強食,這才是世界從古到今的通則,我們完全應該理直氣壯地去爭當叢林霸主,即便因此對弱小的鄰居們呲出牙齒,大聲咆哮,又有什麼不可以?
還有,我們上述這樣的思想反應,會不會從國際事務的領域,擴展到國內事務的領域:既然國際關係上都是叢林法則、弱肉強食,那我們社會生活中的等級森嚴,贏家通吃,也就沒什麼奇怪,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還是如此的,就如同太陽每天從東方升起——這有什麼值得憤怒和批判的?
不要只是覺得這樣的思想反應太小器,它們其實表現了一種在今天仍然相當普遍的思想狀況:當我們選定一個社會理想的時候,總是本能地想為它找到一個現實的例證,如果找不到這樣的例證,我們就很難堅守那個理想。1930年代的蘇聯,1950—1970年代的中國,1980—2000年代的美國或「西方」,都曾經被世界上許多地方的人們看作這樣的例證,並因為它們最終都不同程度地被證偽了,而極大地打擊了這些人追求理想社會的信心。
幸運的是,至少在中國,並不是只有上面列出的這幾類反應。如果將中國的現代思想的起始時段,大致確定為19世紀晚期,那就可以很肯定地說,中國的第一批現代思想家③ ,在熱烈地稱讚歐美先進國家④ ,鼓吹中國全面向「西洋」學習的同時,卻並不認為,這幾個歐美國家所代表的現代「西洋」是體現了當時的人類文明的最優水準,他們更不認為,在這個「西洋」的推動下形成的新的世界秩序,是包括中國在內的非「西洋」國家都應當誠心皈依的。相反,這些思想家多半是帶著深深的困惑,在多種矛盾交雜的心態中,展開對現代中國的構想和實踐,包括鼓吹向「西洋」全面學習的思想家。⑤
第一個明顯表露出這種困惑和矛盾的是王韜(1828—1897)。作為中國現代思想的一個重要的開創者,在1880年代,他是最明確地鼓吹應該全面學習「西洋」的中國思想家,但他為自己這鼓吹列出的第一條理由,卻直指其時已經為中國的部分精英人士所知曉——甚至贊許——的「萬國公法」的野蠻性質:「彼之所謂萬國公法者,必先兵強國富,勢均力敵,而後可入乎此,否則束縛馳驟,亦為其所欲為而已。」⑥ 中國已經不可逃脫地被捲入了「西洋」主導的現代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只有勢均力敵者之間才有道理可講,因此,中國必須成為勢均力敵者中的一員,而要達到這一點,就必須全面學習「西洋」:在王韜的這一論述邏輯中,向「西洋」學習的必要性,是與一種「我們不得不適應野蠻規則」的無奈意識深度交織在一起的。
在更深廣的層次上重述了王韜的這一矛盾意識的,是十年之後的嚴復(1854—1921)。他與王韜一樣,也將學習「西洋」視為在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首要途徑,他甚至比王韜更激進,主張全國的新式學校的大部分課程都應該用「西文」來教。在某種程度上,他可以說是為中國的「全盤西化」擬定基本方案的第一人。
但正是這麼一個嚴復,他也有那種「我們不得不適應野蠻規則」的無奈。⑦ 因此,他每每在鼓吹那些意在適應新世界的「西化」主張的同時,又大聲地慨嘆那個造就新世界的「天演」的不可理喻:「世之變也,莫知其所由然」⑧ ;「大抵宇宙究竟,與其元始,同於不可思議。不可思議雲者,謂不可以名理論證也」⑨ 。顯然,他是要用這類「不可知論」式的說法,來化解自己和許多同道共有的那份「如此適應新世界是否正當」的道德焦慮,但也唯其如此,他對於「西洋」的認識的內在張力,是表現得非常清楚了。
再下來應該介紹的,是楊度(1875—1931)寫於1907年的《金鐵主義說》 。這也是一本宣講作者對中國如何現代化的方案的書,這方案的基本內容,也都是比照著歐美「強國」的經驗來展開的。但是,在具體說方案之前,他先概述當時的世界形勢,明確地說,所謂現代世界,就是一個在西方「文明國家」的主導下形成的「野蠻之世界」,一個通行叢林法則、弱肉強食的世界。⑩
值得注意的是,他仍然用「文明」一詞來稱呼那些主導和造就「野蠻世界」的西方國家——其中主要是英國、法國和美國。他之所以稱它們為「文明國家」,是因為這些國家內部的「政治上之組織」「教育上之周詳」「實業上之發達」,以及「舉國之人」的「和親康樂之風」,都已經達到了可被稱為「文明之國」的程度。⑩ 作為一個中國知識分子,楊度當然是憎惡西方列強的帝國主義行徑的,但他並沒有被這份憎惡衝昏頭腦,以至於看不見西方社會內的許多方面都遠遠「高於吾國」,值得中國人認真學習和仿效。
更重要的是,楊度進一步解釋了那些西方國家的內部「文明」與現代世界的整體「野蠻」之間的關係。在他看來,正是現代世界的「野蠻」——即各國不得不以國力競爭求勝,決定了這些國家(the states)必須團結自己的人民,以形成強大的國力,而團結人民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形成趨向於平等的法治,讓人民享有民權,因而認同自己所屬的國家(country)。也就是說,恰恰是整個現代世界的「野蠻」性質,倒逼這些國家形成了趨向於「文明」的內部形態。
站在今天來看,當然可以說楊度的這個解釋是過於簡單了,但在當時,它卻能將王韜、嚴復們對於現代「西洋」的兩種明顯矛盾的感受,相當有效地捏合到一起:覺得那些國家很先進、應該學習,當然對;覺得它們如此欺負我們、太霸道了,也對的。它們本來就是一體兩面,又文明又野蠻,而且這兩面還互相促進,形成了良性的循環……
不僅如此。楊度這樣的解釋,更凸顯了一個「為什麼在野蠻世界裡必須文明」的政治理由:越是看清楚只能加入現代世界的野蠻競爭,就越要在社會內部反其道而行之,創造文明的制度和法則,如果中國的內部生活跟在國際上一樣,也是按照叢林法則組織起來的,它就不可能形成穩固的強大國力,在國際競爭中一定會失敗,甚至「亡國亡種」。
這無疑是給鼓吹「西化」的變革主張墊下了一塊穩固的基石,它現在能夠將中國人面對西方帝國主義侵略的幾乎全部的屈辱感和憤慨心,都吸收為自己的一部分了。⑫ 從康有為開始,主張向「西洋」學習的中國思想家都不斷地拿越南、朝鮮、印度和土耳其當例子,既渲染「不改革一定亡國」的悲慘,又誇張「改革一定迅速強國」的樂觀,這樣的敘述策略所依據的,也正是楊度式的現代「西洋」觀。
當然,楊度的「金鐵主義」並不真正能化解嚴復的「天演不可知」論所蘊含的焦慮。即便1910年代中期興起的「新文化運動」,以一邊倒式的中西文化和社會比較論⑬ ,再度掀起了「全盤西化」的思想風氣,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慘烈狀況,還是嚴重衝擊了中國的現代思想,推動它正視現代「西洋」的複雜內涵,重新想象中西文化的關係。
這裡沒有篇幅介紹1918年以後中國思想界在這方面的大量討論,只簡單舉兩個例子。一個是張君勱(1887—1969),這位傾心於「西洋」政治制度與文化的哲學家在1922年初說,既然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慘劇和「歐洲文化的危機」,中國人就應該終止那種「西洋人如何,我便如何」的幼稚狀態,「由我民族精神上自行提出要求」,確定建設「吾國今後新文化之方針」。⑭ 另一個是梁啓超(1873—1929),他依據對「一戰」以後世界大勢的分析,提出了一個堪稱振聾發聵的判斷,「世界工業文明之禍殃,乃以我為最後之尾閭」,而隨著資本主義造就的全球社會矛盾持續地轉移和積聚到中國,「全世界資本主義之存滅,可以我國勞資階級最後之勝負決之」。⑮
倘說在嚴復那裡,「西化」所引發的道德焦慮,主要還是牽繫於「是否應該去適應新世界的野蠻規則」,上述兩個例子卻表明,在1920年代早期,問題的重心已經明顯偏向於「是否有可能改變世界的野蠻規則」了。
正是這個思想焦點的轉移,將楊度在闡發「金鐵主義」時有意回避的一個關鍵問題,再次凸顯了出來:為了在弱肉強食的叢林世界裡生存下去,中國不得不用「西化」的方式「發展」出足可抵擋「西洋」「列強」的蠻力和獠牙,那麼,隨著這一「野蠻化」過程的順利展開,中國會不會逐漸習慣於恃強凌弱、也去欺壓弱小的民族和國家?如果不願意中國變成那樣,我們如何一面被迫「野蠻化」,一面又努力不變成一頭新的大野獸呢?
就在楊度發表《金鐵主義說》 的第二年,正在日本求學、後來成為中國最重要的現代作家的魯迅(1881—1936),給出了他對上述問題的回答:面對帝國主義列強的「虎狼突來」,中國自然是要奮起反抗,將虎狼「斥去之」的,但是,這有個限度,就是僅止於「驅之適舊鄉,而不自反於獸性」,異化為「獸性愛國者」。可如何避免這個異化?他說,最重要的是保持自我省察的意識,恢復善良平和的初心:「反諸己也,獸性者之敵也。」⑯
1924年,國民黨領袖孫中山(1866—1925)在關於「民族主義」的系列演講中,不但重申16年前魯迅那樣的見解,說中國民族主義的任務,絕非以「強大」的國力去奪取叢林世界的「老大」的位置,還更進一步說,只有幫助和聯合世界上的其他弱小民族,一起來消滅現代世界的野蠻規則,創造一個真正文明的「大同」世界,中國民族主義才算完成了自己的「天職」。為了做到這一點,他也給出了一個類似「反諸己」的辦法:就是要牢記「今日身受列強政治、經濟壓迫的痛苦」。他深信,只要中國人不忘記這個痛苦,即便以後中國強大了,不會再受列強的壓迫了,中國也不會「學列強的帝國主義,走相同的路,蹈他們的覆轍」。⑰
到這一步,前述那個「為什麼在野蠻世界裡必須文明」的政治理由中的「文明」的全部涵義,也就完整地顯示出來了。中國現代思想所追求的「文明」,並非只有中國內部的社會形態這一個層面,它還有一個國際關係的、全球的層面,只是在社會內部終結叢林法則是遠遠不夠的,正如楊度所理解的,單個國家內部的文明形態,完全有可能成為全球性叢林法則的一個有機的部分,只有在全球層面基本達成了「大同」的局面,人類社會才真正進入「文明」的階段。顯然,這裡說的「文明」主要是一個形容詞,是對一種狀態的概括,它大致可以等同於「廣義的社會主義」。⑱
從1910年代到1930年代,中國的許多思想家和革命領袖,都對中國人在現代化的過程中變成「獸性愛國者」的可能,抱有不同程度的警惕,他們因此提出的對策,也絕非只如魯迅和孫中山這樣,偏重於民族的精神內省。從章太炎(1869—1936)一面竭力替中國構建現代國家(state),一面又大聲揭露這種國家的社會毒性,到章士釗(1881—1973)批判現代「工業國」的擴張本性,倡導以「農」的精神立國,再到1920年代中期開始的多種企圖從鄉村奠定國家現代化基礎的社會運動,都展現了相當開闊的精神和實踐的視野,打開了深入討論的層次。但限於篇幅,我只能簡單地介紹到這裡。
從上述極為粗略的介紹中,應該可以看出,至少在其早期階段,中國的現代思想是富於洞察力,並不狹隘和小器的。比如,它不是因為將「西方」看成一個完美的典範才大聲鼓吹向「西方」學習的,恰恰相反,幾乎從一開始,它就知道「西方」有深刻的弊病,但因為心中懷抱一個遠遠高於西式現代化的「世界大同」的理想,憎惡弱肉強食的現實,那就無論發現「西方」在國際事務上多麼「野蠻」,都不影響它肯定「西方」的「文明」之處,並以此為參照,正視中國自身的各種「野蠻」,全力用各種方法來自我批判和自我革命,而這些方法之中,就包括了堅決地向「西方」學習。
當然,現代早期的中國思想所表達的這些理想並沒有實現。有時候我甚至覺得,現實與這些理想是越來越遠了。看看今天的世界吧,大規模的戰爭居然可以在不止一個地方持續進行,以至於同時的那些規模較小的戰爭,都進不了媒體「熱搜」的範圍,在南蘇丹持續多年的內戰,巴基斯坦與阿富汗的邊境戰爭,就是最近的兩個突出的例子。越來越多的政府增加軍事預算,軍火工業開足馬力還供不應求,越來越多的非「軍迷」對兵器津津樂道,民眾之間的互相隔膜和嫌棄——甚至敵視——大面積蔓延,強勢者理直氣壯地鼓吹「大局」,弱勢者神情茫然地被迫「競爭」…… 社會內外的再次「野蠻化」,似乎真成了今天這個世界的一大趨勢了。
但另一方面,也正是今天這樣令人沮喪的現實,再次凸顯了一個在早期的中國現代思想中得到鮮明的表現、對於今天的中國人——當然也不只是中國人——尤為重要的精神和行動的方向:決不能因為「他們」的「野蠻」而泯滅了「我們」追求「文明」的志向。恰恰相反,越是看多了「他們」的「野蠻」是如何被揭露出來的,我們就越要在對自己做同樣的工作:在嚴酷現實的步步緊逼下,除了更堅決地拒絕叢林法則,我們其實並無選擇,只有世界各地的「野蠻」都被揭發出來了,大家都明白了,「只求此刻的自利自保」的掙扎,其實是通向死路的,人類社會才可能經由艱苦的努力,逐漸擺脫野蠻和愚昧,不斷接近社會正義和世界大同的目標。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非常讚賞佩里·安德森教授的演講,並且相信,如果大家都能努力去實踐上述那個精神和行動的方向,安德森教授在演講結束時提出的那個問題——如何利用現有的國際法來創造實現真正的全球正義的空間,就能很好地展開和實踐。
註釋
① 當然,為了說明這一現象,應該進一步解釋如下兩個問題:「中國社會是如何形成追求現代化的共識的」?「為什麼自二十世紀初以來,中國人會普遍認為‘向西方學習’是實現中國的現代化的最佳方式」?但限於篇幅,我無法在本文中展開這些解釋。
② 這裡說的「我們自己的這一套」主要包含兩方面的涵義,一是指中國的傳統,另一是指今天中國的體制。
③ 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王韜、康有為、譚嗣同、梁啓超、嚴復、楊度、章太炎、孫中山、劉師培、蔡元培和王國維等。
④ 主要指美國、英國、法國和德國。
⑤ 在某種意義上,這種困惑和矛盾正構成了中國現代思想的起點的一個最重要的特徵,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現代思想——以及在其引導下展開的中國革命(1880s—1980s)——的大致走向。限於篇幅,這裡無法展開介紹。
⑥ 王韜:《變法自強(上)》 ,參見王曉明、周展安編:《中國現代思想文選(上)》 ,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3年,第10頁。
⑦ 例如,他在《論世變之亟》 中那麼曲折地比較中西政教的差異,就相當明顯地表達了這種無奈。見《中國現代思想文選(上)》,第17頁。
⑧ 《論世變之亟》 ,見《中國現代思想文選(上)》,第16頁。
⑨ 嚴復:《天演論·導言十八》 ,《中國現代思想文選(上)》,第44頁。
⑩ 楊度:《金鐵主義說》 ,見王曉明、周展安編:《中國現代思想文選(上)》 ,第190—191頁。
⑪ 同上注。
⑫ 在整個19世紀後半葉,中國人對西方帝國主義侵略的屈辱和憤慨情緒,大部分都不同程度地被清政府內外的守舊勢力所引導,屢屢形成盲目仇外的風氣,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⑬ 這裡說的「一邊倒」的意思是,這些論述將「西方」的狀況一概視為先進,大加贊揚,對中國的狀況則一概視為落後,嚴加批判。
⑭ 張君勱:《歐洲文化之危機及中國新文化之方針》 ,見王曉明、周展安編:《中國現代思想文選(下)》 ,第406頁。
⑮ 梁啓超:《復張東蓀書論社會主義運動》 ,見《中國現代思想文選(下)》,第140、147頁。
⑯ 魯迅:《破惡聲論》 ,許廣平等編:《集外集拾遺》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第31—32頁。 要說明的是,魯迅如此主張「反諸己」,是有一個前提的,因為他此時認為,長期的農耕生活養成了中國人溫良平和、缺乏虎狼之心的集體習性。
⑰ 孫中山:《民族主義第六講》 ,見《中國現代思想文選(上)》 ,第228頁。
⑱ 在整個20世紀前半葉,包含各種思想派別的「廣義的社會主義」無疑是構成了中國現代思想的主流。限於篇幅,我無法在本文中展開這方面的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