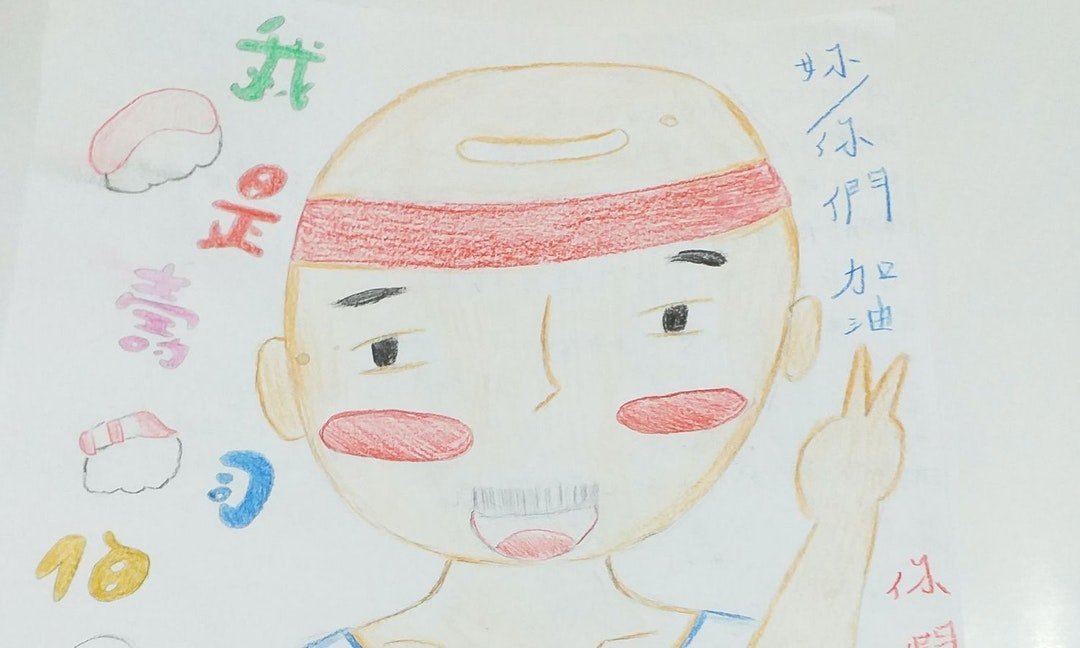(本文原刊於2020/10/30關鍵評論網,感謝鍾喬老師提供轉載)
戲演完時!整個原本空蕩蕩而顯得荒疏的大禮堂,突而被一種溫暖的氣息所籠罩著。孩子們臉上淌著淚水,和家人在舞台上相擁著,既是一種歡欣且存有某種說不上來的激動!劇場,是人與人相會的場合;是觀眾與舞台上的演員相會的場合。
久而久之,便也形成一種容納著時間與空間交匯的場域。場域,不僅僅是場合;更是事件激盪的所在。這裡,便有了人在一個特定空間中,經由故事所生產出來的情境,稱之為戲劇的文化行動!
如果,這行動本身發生在一處有實質牢牆的輔育院。舞台上的演員,即將或終在不遠的一日,會走出牢牆回返家庭或社會;而台下的觀眾,恰是常來或偶而前來探望的家長或親友們,她/他們在結束舞台與觀眾的分隔界線後,因著終而打破的疏遠或陌生而相擁而泣,不會是一件難以想像的事情!
很顯然,剛下了舞台的少女們,不願因散戲而離去。然而,曲終而人散,是一定要發生的情事!任誰都無法阻擋其發生的必然,那位剛剛在台上激越底舞蹈著,以表達內心掙扎的少女,剛剛擦拭完臉上的淚水,和離去的親人話別,臉上變得異常冷靜且似乎刻意不帶任何情緒,這是青春的身體話語,僅和無比深如海洋底層的內心,交換著喃喃的聲音或私語。就這樣,戲才在身體裡暫時畫下句號,卻又自心底浮起一層層飄向離岸的渦流,一層又一層,一直不曾散去。
我於是想起了青春時期,應該就是像這些逆風少女們一般的年歲時,多少次在禁制中閱讀,在埋著棉被的暗黑中打亮的手電筒,所照射出來的光中,映現的幾些字句,上面寫著:「我用指頭刮著淚。我不回家,我要走,要流浪。我要坐著一列長長的、豪華的列車,駛出這麼狹小、這麼悶人的小島….」
這是陳映真的短篇小說〈故鄉〉。描寫一個大學畢業後的青年,以第一人稱素描如版畫般的家族之沒落!榮光與繁盛隨著父親經商失敗欠人巨債,陷入無比的深淵。年少時,景仰的一如套著聖潔光環般的兄長,從礦坑裡救人的保健醫師,淪落為牌桌上沉淪地頭都不抬起來的賭徒!
曾經,俊美如太陽神的哥哥,「白天在焦炭廠工作得像個煉焦的工人;晚上洗掉煤煙又在教堂裡做事。」;如今,殞落如放縱邪淫的惡魔般,在家鄉的市井裡被流傳著。哥哥的落敗,從此導致小說中以「我」的身分現身的主角,隨著陷落到空虛、荒誕、衰敗的境地,深深感受「家是不得不回去了…」;但,家也是回不了的。因此說著—「我不要回家,我沒有家呀!」
這篇小說,對青春期的我還有相同年歲的伙伴,帶來深刻的影響,在那個禁制的年代中,我們如是閱讀陳映真被查禁的小說集《將軍族》。從時間的旅程而言,已經是上世紀1970年代中期的記憶,曲指稍數,也已有將近半個世紀的間隔。
然則,現在讀來,我總感覺,卻仍很能印證當下逆風少女們的處境,難道不是嗎!當然,真實的處境畢竟不同:時空不同,人物遭遇也不一定相同。畢竟,〈故鄉〉也是一篇虛構的小說。然而,某種象徵的況味,卻得以從小說的虛構,一路延伸到少女逆風的青春人生中。
在戲中,伊們以真實的告白,將自身的經歷與遭遇搬上舞台,其中都和逃家、離家或棄家脫離不了干係。家,是最初的生之泉源;然而,家也成了不得不回去的處所;進而,讓人感到「我不要回家,我沒有家呀!」這是青春的迷途,等在成長的道途中,一線之隔,隨即可能陷落到沉淪的浪跡生活中。
而我,恰也是在這樣的時刻裡,像是召喚回了自身的青春年少,在不知何處的時空交錯中,偶而回身,便看見伊們和我相同,對家懷抱著既矛盾且困頓的情愫,經常不知如何自處!於是,我寫下了以下的詩行,作為一個即將邁入年老歲月的男人,在回眸青春的視線中,與逆風少女們相遇的多重折射!詩行如下:
〈看著你們—寫給逆風少女〉
狂瀾中你依然燦爛且歌唱
儼然站在船頭的歌手 巴布羅.聶魯達(Pablo Neruda)看著妳們,我想起青春慘綠的年少
一個少年如我,站在風中的鐵軌
迎向逆風的旅程!歐!何等恐懼
傷感且無助的每一個午後
深懼下一刻倒塌的,便是身後的車站然而,不知何時吹來的風
還是帶來了準時現身的鐵道員
像是偶而嘴角露出微笑的父親
從時間那頭的軌道末梢走來
帶來幸福的耳語和刺臉的鬍渣
在狂風突然襲捲月台的片刻
畫下一幅鉛筆速描的家庭合照歐!看著妳們,提著孤單的行李
即將踏上陌生的一趟旅程
豪雨中依然不忘明朗歌唱
朝著生活的舞台狂歌
且允許青春的騷動
在黑暗中起舞看著妳們,在一處廢棄的碼頭
生鏽的鐵,拆得僅剩碎片的船
妳們逆風破浪,用身體
航向一趟旅程,相互攜手
共造一艘迎向破曉的船
你們在船頭歌唱
船尾,傳來層層的合頌那曾經是飢餓與糾纏
是困頓的破鏡與掙扎的愛
是冷冽的清晨與子夜的遺棄
現在,都逆風飛翔
朝向一趟未知的旅程且讓我,追回年少時
在鐵軌道上漫遊的少年如我
與妳們共同,逆風
飛向晴朗的高空遠方,仍有風暴在狂亂中席捲
這詩中,引用智利詩人巴布羅.聶魯達的詩行,其來有自,且訴說如後。先說,其緣由竟和自身一趟迷途緊密相關。事情是這樣的:驅車前往輔育院校,前後已有三年了!因為,劇團在此展開戲劇教育,今年針對的是19位逆風少女。是的,逆風。因為順風好行,偏偏伊們感覺逆風才是路的方向!這也是一種執著,我總這樣感受,伊們在牢房般的教室中渡過的青春。總之,結論是迷途而被送進這矯正學校的牢牆裡!

話說回頭,這天,我竟也因迷途而走反了方向。對於這迷途,最早感到迷惘,是從一條稱作山腳路這頭的一段,開到接近盡頭的五段,經過一條稱作「重生路」的小巷,很象徵性卻無比真實的,卻又回到山腳路一段!怎麼是一段又回一段呢?原來,開始的那頭是指員林鎮的「一段」,輔育院校這頭的「一段」,指的卻是位於田中鎮的「一段」!所以是山腳路「一段」輪迴到「一段」,才會抵達目的地!真是迷惘之途的寫實象徵!不知這些逆風少女,若知這路途指標的迷惘,會寫出怎樣的詩句來?會不會就是聶魯達的這兩行詩呢!耐人尋味,且充滿期待。
今年,演出的主題是「愛」。在稱作《那個她,那個我》的戲碼中,起始於一場逃家的旅程。文宣中寫著:「她們渴望被愛,離開了家,還是在愛情中跌跌撞撞;那麼,到底什麼是她們內心的歸屬呢?」寫這文宣邀請函的,也是同學本身。一位秀氣而曾經犯下大錯,卻被媒體喧染的標題所霸凌,導致長期患憂鬱症的女孩…。
很佩服她勇敢走出生命復甦的旅程,並隨著團隊的旋律走上舞台!伊們都共同擁有一位暱稱「媽咪」的導師;「媽咪」對這班逆風少女的愛,是少女們重新找到歸途的一盞燈,我心中一直很佩服有這樣奉獻精神的老師;因,我始終相信,這樣的燈將永遠不會在人間熄滅!
年青時,在《人間雜誌》學習編寫,發刊辭上,映真先生便寫著:「因為,我們相信,我們希望,我們愛…」我知道這話來自聖經,然更深的感受,卻出自對於「愛」的思索!便也是這「愛」的主題,讓我看完整排後,瘦削的老臉上,也紅著迷途後再次梭巡下去的眼神!心中迴旋著聶魯達在〈絕望之歌〉中,如何飛越挫敗的兩句詩行:
狂瀾之中你依然燦爛且歌唱
儼然站在船頭的水手
其實,更感人的是;這首詩,一直藏在切.格瓦拉(Che Guevara)最終經歷玻利維亞叢林革命歷程的背包裏;他慘遭槍決後,若耶穌般躺在泥沼的石床上,被魯莽的軍人與美國中情局「CIA」的特務蒐證般搜了出來,卻成了今世最鼓舞人的一本手抄筆記詩集。其中記載著,在愛的挫折中站起來的這兩句詩行。為了對革命者與詩更深的理解,並從這筆記中讀到1955年,切曾寫下的少數詩篇,抄寫於後:
大海以她友誼之友招喚我
溫柔且不朽的展開
彷彿薄暮中的 一只鐘
敲響一座浮沉的島嶼
(最後這句詩,是我加入的, 抱歉 切 我心目中的志士)
逆風少女的演出《那個她,那個我》,最令人動容之處,在於青春的生命之愛與跌落;涵蓋親情與愛情。青春,到底如何面對倉皇中若星辰殞落的愛呢?這裡,沒有以失落來形容伊們內心創傷;卻以跌落來形容,自有其更深的刻痕!因為,被法官判入矯正學校,面對的是身體的高牆;然則,愛的寄託卻是心理的高牆如何被翻越…。曾經於2019年,參與此項計畫的詩人葉子鳥,此次也以詩的工作坊,帶動逆風中的少女們,在舞台上,朗讀伊們自己書寫的愛的詩行。葉子鳥以詩行寫下了回應:
被監禁內的高牆
高不過我們每個人看不見的那座牆
你的牆,與他相仿嗎?
且用這首詩,來為即將陸續重返家庭,或在家門前躊躇難行的少女們,表達深切的祝福!是的。逆風中的伊們,將是一只鐘,敲響一座仍在價值判斷的異己排除間浮沉的島嶼。
發表日期:202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