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
反思「犧牲者」:韓江《少年來了》讀後
◎蔡依伶
【摘要】……我們總感嘆韓國影視可從計程車司機視角拍出光州事件,在我們這些歐巴桑愛看的韓劇裡置入全泰壹(但我相信青春奉獻給成衣業的南韓歐膩不會忘記),或時代劇女主角傾慕的男大生常因涉入讀書會而秘密失蹤數日,而由勇敢女主角伸出援手,成功躲避當局查緝。這種感嘆來自政治受難者在台灣的故事,著重挖掘菁英階層,從而萌發────外來政權透過二二八、白色恐怖是如何殲滅了台灣一代菁英階層?───這樣的敘事目的,而韓江《少年來了》則交錯不同階級的敘事聲線,呈現光州市民在歷史關鍵時刻的決心。甚至跟韓國其他影視作品不同的是,韓劇韓影裡,男女主角儘管眨著無辜淚眼,訴求政治無端阻礙他們的愛情及本該順遂的人生,這種對歷史與人生的解釋,也常見於台灣政治受難敘事。但《少年來了》則希望重新考慮政治受難者的定義,並顧及光州事件前後其他社會衝突的伏流……。
作者為南部「工人文學讀書會」成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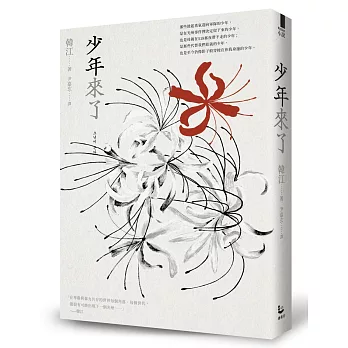
如眾多華文書評所稱頌,韓江《少年來了》確實厲害,文學技巧洗鍊出色,在讀書市場上更極大化了潛藏讀者,除爭取敏於政治的讀者,甚至防彈少年團金南俊一度直播推薦這部小說。
《少年來了》如何刷新該類寫作?我們總感嘆韓國影視可從計程車司機視角拍出光州事件,在我們這些歐巴桑愛看的韓劇裡置入全泰壹(但我相信青春奉獻給成衣業的南韓歐膩不會忘記),或時代劇女主角傾慕的男大生常因涉入讀書會而秘密失蹤數日,而由勇敢女主角伸出援手,成功躲避當局查緝。這種感嘆來自政治受難者在台灣的故事,著重挖掘菁英階層,從而萌發────外來政權透過二二八、白色恐怖是如何殲滅了台灣一代菁英階層?───這樣的敘事目的,而韓江《少年來了》則交錯不同階級的敘事聲線,呈現光州市民在歷史關鍵時刻的決心。甚至跟韓國其他影視作品不同的是,韓劇韓影裡,男女主角儘管眨著無辜淚眼,訴求政治無端阻礙他們的愛情及本該順遂的人生,這種對歷史與人生的解釋,也常見於台灣政治受難敘事。但《少年來了》則希望重新考慮政治受難者的定義,並顧及光州事件前後其他社會衝突的伏流:視他們為犧牲者是否恰當?稱他們為犧牲者是夠無辜的,卻也夠被動,從而弱化了他們的主動性(失敗是另一回事);但如果受難者並非無辜被動,是否能證成國家機器的威權暴力?另外還值得思考的是,目前對台灣解嚴的主要歷史解釋:台灣解嚴是反對國民黨威權統治的勝利,由本土菁英有效地組織反對運動,因此,有民主當思無民主之苦(而民主等同於人權、自由……)。這種對比所引發的政治效果,常在凸顯共時下台灣與中國的不同,卻很少啟發我們去回首歷史:那麼戒嚴三十八年究竟是什麼?
《少年來了》以少年之死為線索,渲染力十足。敘述者提供了不同角色的視角,再現且探索了少年為何而死?並非是刻板印象下的「被迫犧牲」,通過層層探問,每一次都發現少年東浩能自決轉身離開的空間:恩淑告知戒嚴軍晚上將至,要他離開別再回頭。善珠判斷朋友正載遺體肯定不會運來現場,不要東浩再等(也不要再等姊弟不在光州的親人來尋親,期望藉此告知真相)。振秀要求少年們離開,卻發現他們瞞著大人(?)留下,教他們主動投降以保性命,振秀等人意圖先犧牲自己來成全他人(包括少年們)。東浩的母親在最後時刻,喚不回為朋友之死而懷抱罪惡感的兒子。少年當場死了,其他人則意外倖存。很多小說或電影「操作」青少年角色來重新尋找人生答案,或可從初衷、本心的角度為小說提問,但作者不只想呈現這種效果,《少年來了》第一章「雛鳥」以「你」為人稱,帶有敘述者與少年東浩對話的企圖。除了敘事,韓江運用了類似推理小說「屍體會說話」的技巧,通過少年東浩及正載之眼「報導」事件中的遺體,精準刻劃當權者的心態。死狀恐怖,少年們無以名之(命名需要真相、脈絡與意義)。此外,此類型敘事的另一種危險(該說是陳腔濫調?)則是讓大學生來主導敘事,但作者並沒有這樣處理;相反地,形象陰柔的金振秀(因首爾大學停課而涉入事件)反而是採取獄友旁述來完成(振秀最終自殺)。
稱他們為犧牲者是否恰當?其中一個有力象徵是恩淑從檢閱科領回的查扣文稿,因當局在出版社翻箱倒櫃搜查時,將另一份劇作誤認為某政治通緝犯所作,因此領回的稿件大多數頁面直接以滾筒墨水輾壓漆黑,本該扁平的手稿被迫鼓成三角柱狀,而這些內容也陰錯陽差地成為不能搬上舞台、被禁演的內容,因此被查禁的台詞,最後以演員張口卻無聲的口形來表達,表現反覆輾壓、開口無言、噤聲等意義。然而其中過程並非只是機遇湊巧,而是恩淑借計施計,忍受拷問毒打,雙重保全了書籍與劇作。且小說家不只擅長處理情節,而是讓讀者跟緊恩淑的內心跌宕,於揭曉舞台劇該如何收場的懸念下,恫瘝一體,此理心同。
韓江接受傳媒訪問時指出,小說付梓前,仍不斷修改甚至重寫第五章,務求足以貼近人物為止。倘若原版與繁體中文版編排一致,第五章講的是善珠的故事,韓江的慎重,我猜無非是善珠的故事貫穿全書重要角色──善珠跟正載的姊姊正美的緣分,又在光州事件期間,在道廳結識了急尋正載遺體的少年東浩。但除寫作要素外,該書雖名之為「少年來了」,但善珠其實是最能回答作者提問的角色,部分地,甚至是作者置入自己的反身性詰問:
把那些沉默、乾咳、猶豫,以及生硬或軟弱的單字拼湊起來,最後會完成一段什麼樣的內容呢?
林善珠這個角色,相較於其他主角,是光州事件前已經比較有政治意識的角色。當然,其他角色除少年東浩與正載外,都不是政治白紙一張,比如此前恩淑曾在學校目睹便衣警察衝入學生餐廳任意毆打學生。而善珠有一段抗爭最終遭強力鎮壓而失敗的工會組織經驗,敘事用「妳」為人稱,來審視善珠從夜晚、深夜終至天光漸露的一夜心理轉折。
光州事件十多年後,餘生的善珠在一個反公害團體勉力工作,領按件計酬的微薄工資。這一晚,善珠掙扎是否該去見昔日工會組織者恩熙姊最後一面?(南韓70年代第一波自主工會的組織者如今也步入晚年?),同時,善珠遲遲無法開始對著尹教授提供的錄音機開口,前者幾度來信要求採集光州事件中女性市民軍的證言。如善珠這樣平凡市民為何會捲入政治事件?甚至以善珠為參照,去推測正載姐姐正美的枉死?一輛被年輕紡織廠女工佔領的市公車吸引了善珠的視線,車窗外布條掛著:「解除戒嚴,保障勞動三權」,女工們手拿樹枝拍打車體,一路唱戰歌,勾起善珠的回憶:清脆嗓音,很像小鳥或小獸同時發出的聲響。沿路清脆迴盪的戰歌向善珠展開以下的視野:
……老人、小學生、穿著工作制服的男女工人、打著領帶的年輕男子、穿著套裝腳踩高跟鞋的年輕女子,以及手拿長傘來充當武器、身穿新村外套的大叔。在這些群眾的隊伍前,還有一輛手推車,載著兩具在車站前被射死的男子遺體,一起往廣場走去。
善珠此時想起,透過工會選舉本可奪回資方掌控工會席次,但武裝鎮暴警察卻馬上進入工廠,強力鎮壓否決了選舉結果。資方背後站著國家,當資方再也不能掌握情況,國家立即上場,而國家對勞方保證的是:
薪水只有男性員工的一半……作業班長就會對妳咆哮謾罵或者一巴掌朝妳臉打過去……警衛深怕有東西被偷而搜查女工身體。那些手摸到內衣邊緣處就會刻意放慢速度。羞辱、咳嗽、經常性的流鼻血,頭痛。吐痰時還一併會吐出黑線頭。
萬萬沒想到那群人竟然將只穿著內衣褲的女子拖到了泥地上。她們的背部和腰部的肌膚被泥沙擦傷,流出了鮮血……他們用棍棒和角木毆打數十名勞團成員,並關進宛如鳥籠的鎮暴巴士裡。
南韓、台灣,乃至於香港的GDP、外匯存底不該有性別嗎?國家對美出口貿易的保證,靠大量廉價勞動力來兌現。如台灣楊青矗解嚴前所描寫的女工故事,許多中輟失學、先犧牲自己,成全年幼弟妹上學的姊姊們進到工廠,同時這也是《少年來了》正載姊弟分租東浩家、小說角色聚合的起點。而面對工人農民學生運動,所有的風吹草動,都遭當局與美國懷疑背後是否有個紅色政權?被捕的善珠,「只因過去是女工,從事過工會活動」而被羅織了個「赤婊子」的匪諜故事,遭凌虐到下體失血不止。
面對曾為同志,許久未見、病榻上的恩熙姊,善珠有許多想訴說的:
要是再次面臨與那年春天一樣的瞬間,妳可能還是會做出類似的抉擇。就如同國小在玩躲避球時,原本只要專心避開對方攻擊就好,最後只剩獨自一人時,妳反而要去接球。…….如同在那個夜晚,妳默默舉手表示願意留守到最後一樣。「我們不能成為犧牲者,」聖熙姊說過:「不能放任他們稱我們是犧牲者。」
但我還是覺得很可惜。相較於小說第二章「黑色氣息」寫正載魂魄徘迴棄屍處不知何從何去,充滿想像力。寫恩淑承擔受辱之恨而借計周全,抓緊角色內心情緒跌宕,扣人心弦;而善珠的故事讀來卻顯躓礙,善珠比起小說其他角色,較為複雜,不是更可說得更多、更深?如這段角色自白時說:「最後只剩獨自一人時」,讓我覺得作者最後還是將善珠孤例化(當然也表示時局艱難,團結更難),不知這是否受材料侷限?儘管如此,《少年來了》還是一部可深可廣的佳作,文學技巧洗鍊出色,當代書寫者(尤其是專職作家)該怎麼再現這些故事?大多數創作者無非得依靠歷史研究及口述歷史,當這些材料放進小說,語調、敘述方式、對話對象等「行文」、「文體」都會顯露出史料與小說敘述之間的扞格,而韓江對《少年來了》所選擇的敘事觀點、敘事方式,比如把這些材料透過「他敘」,或者把角色置放在受訪情境裡,透過獨白來發展,或者讓敘事者與角色「你」的對話,都成功地將真實相容於虛構之中。
※誌南部小小群組「工人文學讀書會」一周年。
發佈日期:2018/07/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