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20年專題】
離棄「人心」的「回歸」——政治化的污名與經濟化的困局
◎許寶強
本文轉載自:許寶強(2017),〈離棄「人心」的「回歸」–政治化的污名與經濟化的困局〉,羅金義編:《回歸20年:香港精神的變易》,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編案:香港文化研究學者馬國明曾這樣形容,「主權移交」指的是英國把香港的主權移交中國大陸,「收回主權」指的是中國大陸收回香港的主權,二者符合客觀的事實描述。相較之下,「回歸祖國」的說法帶著濃厚的感情,對於中共而言,代表結束了民族百年的屈辱,但是同時,對於一部分香港民眾而言,卻對「回歸」帶著恐懼、焦慮。1997年至今20年,官方一句「人心未回歸」,道盡了「回歸」下中港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矛盾,以及兩地歷史經驗與政治情感的斷裂,本系列搭配【重新思考社會主義】七月十五日【香港回歸20年,往何處去?】論壇,將轉載一系列文章,希望重新理解「回歸」的政治與問題。
隨著2014年831人大決定與雨傘運動爆發,1980年代以來的「民主回歸」論,被視為是失敗且過時的政治觀。推動香港民間教育、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許寶強,則重新論述「回歸」的意涵,並指出香港政治與社會的諸多矛盾,包括表現在地域或國族的民粹政治,係根源於去政治化的殖民主義接合了新自由主義,因而造成了「反政治化」、強調「經濟化」經濟發展的問題。在此意義下,「回歸」可以意味著抵抗「新自由主義」大計的「回歸」「人心」】
回首20年,一個最容易被觀察到的結論是:「人心未回歸」。所謂「未回歸」,指的是港人對中國缺乏認同,甚至抗拒;而所謂「人心」,大概就是「民眾的意願」。合在一起,表述的是香港的民眾迄今仍不願意認同中國。對此建基於國族認同的框架,並已逐漸成為公共論述中的常識的說法,我並沒有大太的興趣繼續分析討論其成因。然而,當中的兩個關鍵詞——「人心」與「回歸」,卻不妨拿來借題發揮,從一種更根本的視野盤點過去、思考未來。
換另一個角度看,「人心」相對的,是「獸性」。人跟其他動物最不同之處,是除了吃喝拉睡、勞動玩樂,還關注些物質生活以外的事情、超越本能的倫理價值。循此思路,「人心未回歸」可作兩種截然相反的解讀:一是人類的動物本能不斷膨脹,令「人性」無法回歸「宿主」;另一則是人類抗拒完全回歸「獸性」,守護「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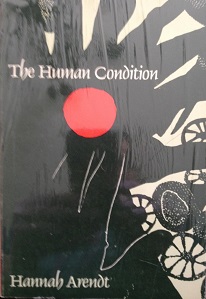 借用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在《人的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 中建立的概念,以及文化經濟學(cultural economy)中有關「經濟化」(economization) 的討論[1],本文嘗試分析香港過去20年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 —— 也就是意義的生產和流通所產生的政治效果 —— 的轉變,希望能同時捕捉當代香港精神的變易。儘管檢視的焦點在於過去20年,但本文希望探討的兩種相反意義下的「人心未回歸」,其實應同時置放於更長的歷史脈絡中考察,尤其是自上世紀70至80年代在英美興起,繼而擴散全球影響中港的「新自由主義」文化大計。
借用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在《人的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 中建立的概念,以及文化經濟學(cultural economy)中有關「經濟化」(economization) 的討論[1],本文嘗試分析香港過去20年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 —— 也就是意義的生產和流通所產生的政治效果 —— 的轉變,希望能同時捕捉當代香港精神的變易。儘管檢視的焦點在於過去20年,但本文希望探討的兩種相反意義下的「人心未回歸」,其實應同時置放於更長的歷史脈絡中考察,尤其是自上世紀70至80年代在英美興起,繼而擴散全球影響中港的「新自由主義」文化大計。
本文將以近年在香港公共論述中常見的污名 —— 「政治化」 —— 切入討論,期望指出反「政治化」與「經濟化」其實是一個銅幣的兩面,都是嘗試改造(或強化過去逐漸形成)港人的主流文化生活和價值觀念,也就是令只關注物質或狹隘經濟利益成為人生的唯一的目標,想完全以動物本能取代「人心」。然而,「經濟化」滲透及改造日常生活的文化大計,卻遭遇民間社會的自我保護力量抵制,而各式社會運動的興起擴大,包括保育自然生態、生活空間、歷史文物,追求平等公義、民主自由、尊重差異、獨立自主、人權大愛,恐怕正是「人心」不想「回歸」生物層次的明証。
「反政治化」的葫蘆賣「經濟化」的藥
當代的香港公共論述中,任何關乎民眾日常生活的領域,例如教育、醫療、飲食、文化藝術,只要扣上「政治化」這詞,都很容易變得「可疑」,甚或需要敬而遠之。這情況在過去的20年,變得愈來愈明顯。[2]
在公共討論中使用「政治化」批評或攻擊他人的,主要是親中港政權的建制力量。然而,在這些論述中,「政治化」具體是指甚麼,卻並不瞭然。在香港的當代語境中,「政治化」一般都帶負面的含意,經常與「搞亂香港」、「雞犬不寧」、「居心叵測」、「立心不良」、「不務正業」、「只求出位」等語詞連用,甚至有政治問責官員倡議「少談政治,只做實事」[3]、參選的政黨副主席把「搞政治」形容為「毒藥」[4],又或高級警務人員把「搞政治」與「做賊」並列[5]。
在這樣的論述之下,「政治化」成為了萬能的負面標簽,或Laclau意義下民粹政治攻擊對手、統合自己陣營的空洞能指(Laclau 2005)。這種港式民粹政治,主要由政權建制推動,嘗試把所有反對政府政策的不同聲音,以「政治化」這空洞能指統合,並召喚民眾把他們對(主要是物質)生活的各種紛雜焦慮及需求,投注於反對「政治化」這「邪惡的敵人」的戰鬥之中。「政治化」這空洞能指能夠裝載「不專業」、「不顧民生」、「忽略公眾利益」、「鬥爭為本」、「為反而反」等負面控訴,「政治化」亦可蘊含「不利學術、教育、貿易、民生、旅遊、社福、醫療等發展」,更有礙故宮博物館、機場第三跑道、落馬州河套「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新界東北發展計劃、港珠澳大橋等項目的上馬,也就是「阻人發達」、「礙人搵食」之意,甚至成為「影響社會的穩定」,引入「外國勢力顛覆國家」的「元兇」。
「政治化」這萬能的負面標簽之所以能夠在一定程度產生效果,與香港的社會脈絡有關。接合了長時期的殖民歷史,加上港英政權於戰後透過參與打造並利用冷戰的格局,令不少以難民身份移居香港的民眾,花大部分時間專注於追求温飽,讓「反政治化」這空洞能指獲得了良好的生長土壤。1980年代中期至1997年的政權轉移期間,港英政權逐漸開放了民眾參與政治的渠道,鼓勵一批新生中產階級投身政界、組織政黨。然而,在殖民體制和基本法的框架之下,讓1997年中共政權的逐漸介入干預很容易控制社會發展的方向,民眾參政的效果愈來愈有限。在最近十多二十年中,當民眾參政意願及對改進社會的期望提高,卻踫上功能團體及特首小圈子選舉的框限,再加上最近幾年在不忌憚挑起鬥爭的特區政府官治之下,社會撕裂擴大,立法和司法機關愈來愈難以正常講理的程序制約行政主導的「有權盡用」,只能用議會拉布或司法覆核等方式阻礙或拖延由上而下的政令。這種容易被認為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抗爭方式,在大眾傳媒陸續被政權建制力量收編、發展主義愈來愈成為統治共識的社會脈絡下,往往被描述為沒有建設性的「政治吵鬧」,再加上政權的「語言偽述」和建制政黨以同樣甚至更為沒有建設性的「政治吵鬧」方式回應,加深了不少民眾對「政治(化) 」的厭惡。
1997年後的特區政權,不僅沒有離棄及改造各層次的殖民管治制度,更愈來愈「充份利用」殖民體制賦予在位者的權力,尤以近五年為甚,令由上而下的殖民權力更直接赤裸地介入各個民間領域,導致大學委任校董、廉署人事變動、特首向報館發律師信、其女兒在機場的行李也涉嫌在特權介入下過關等風波,影響遍及教育學術、貪污腐敗、言論自由等領域,甚至出現被評為「官商鄉黑」的泥頭事件及發展模式;而在文化價值方面,則變本加厲,大力鼓吹「中環價值」,貶抑民主以至政治參與,比1997年前更沒有保留地推動香港的「經濟化」,或人的「動物化」。
從第一屆的特首開始,施政報告中主要的篇幅,全是有關於「經濟」。儘管報告中包括房屋、都市、環境、運輸、基建、教育、醫療、社福、人口、體育等議題,但這些議題基本上全是從「經濟」的角度審視,訂定政策建基的是成本-效益、物質需求、數量增長等狹義的經濟準則[6]。例如董建華時代提出的減少空氣污染,依據的是政府顧問的資料:「本港每年有多達8萬市民因為吸入過量微塵,導致心臟及血管性疾病,涉及的醫療費用多達350萬元」[7];又例如曾蔭權提出「進步發展觀」,其中一項主要的政策目標是為了「活化」古蹟文物,以打造「文化地標」,一方面可提升旅遊業的競爭力,另一方面則有助鄰近社區的土地增值。至於現任特首的施政報告,除了重覆各個領域的「經濟化」量性措辭,還加入了「一帶一路」等「中港融合」的「經濟發展戰略」。
一篇發表於一份親中港政權的網上刊物的文章,頗為直接地表述了「反政治化」其實就是「經濟化」。這篇由中評社記者撰寫,發表於2017年1月6日,題為〈香港繼續政治化 還是回歸本質?〉[8]的文章,這樣寫道:
「香港,這座國際金融中心,要如何迎來屬於自己“新”的一年,是要繼續政治化,還是回歸本質?…新的一年裡,香港何去何從,是要在政治泥沼中內鬥內耗,還是要在經濟賽道奮力向前,這不僅僅是反對派需要思考的,更是全香港市民需要思考的。…香港社會還是需要將重心轉移到經濟發展和民生建設上來。香港是工商社會,經濟發展才是香港的首要目標,過度沉迷於政治爭拗,只會讓香港流失絕佳的發展機會,這對香港而言,對香港市民而言,是百害而無一利的。…」(著重處為筆者所加)
把香港的「本質」定位於「國際金融中心」、「工商社會」,然後要求發展經濟、建設民生,並由此要求放棄「政治」、「爭拗」,自是順理成章。這樣的論述將「政治」與「經濟」截然對立,製造忠奸分明、只能二選其一的框框,隱含的前提,是把人還原為只剩下物質需求層次的動物。「政治化」之所以「對香港市民」「百害而無一利」,前提只能是除卻狹義的經濟物欲外,「香港市民」並不存在其他面向的需求。換句話說,「反政治化」與把民眾的社會生活、倫理價值「經濟化」,其實是一體兩面,是一項嘗試將「人心」回歸「獸性」的文化大計。
這項由上而下的文化大計,嘗試把人類生存的各個面向,包括政治生活、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生態保育,改造成全用「經濟」來表述和衡量。在此「經濟化」工程中,民主政治被轉化成行政管理,國家/政府、公共機構(大學、醫院、社福機關、文化演藝)均變成「公司」,資深教授、醫生、社工、文藝工作者化身為董事、行政總裁、高級經理,公帑支出被表述為等待合理「回報」的「投資」,以量化排名等指標衡功度值,用競爭文化作為唯一的遊戲規則;法律、自由、保育被貶低約化成推貿易、工商、旅遊的工具;人權、生態則被等同(或置於)人類的基本物質需要(之下),也就是「先(只)求温飽」,餘皆次要[9]。
近20年香港的「反政治化」/「經濟化」進程,是在1970至80年代英美新自由主義與中國的「改革開放」的社會脈絡下壯大成長的。戰後20年間香港的經濟快速增長(年均增幅約10%),但同期的貧富差距也不斷擴大。1970年代中期之後,香港的財富兩極化趨勢不僅沒有緩和,更愈來愈嚴重(表1),成為了「已發展地區」中貧窮最懸殊之地。值得注意的是,不論在每年平均超過10%增長經濟的1980至90年代,還是2000年之後相對低增長的時段,貧富兩極化趨勢都沒有中斷。
表1:香港的貧富差距
| 年份 | 1971 | 1976 | 1981 | 1986 | 1991 | 1996 | 2001 | 2006 | 2011 | 2016 |
| 堅尼系數 | 0.430 | 0.429 | 0.451 | 0.453 | 0.476 | 0.518 | 0.525 | 0.533 | 0.537 | 0.537 |
資料出處:劉祖雲,2009:頁10;〈近30年貧富差距漸大〉,2016年 06月 09日,《香港商報》,http://www.hkcd.com.hk/content/2016-06/09/content_3563943.htm。
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再加上消費主義的壓力,令物質資源相對匱乏的低收入人口的數量在上升之餘[10],其生活質量(包括居住環境、食物安全、工作條件、精神壓力等)也改善不大,而在過去十年更每況愈下[11]。相較戰前以至上世紀50-60年代,當代香港的物質發展無可置疑是遠為充裕的,但分配的嚴重不均卻容易讓民眾不滿。為了轉移在不平等愈來愈明顯的社會環境下,民眾為追求公義而指向政經特權的矛頭,中港政權和商界企業等建制力量,自然願意以「反政治化」/「經濟化」的論述,嘗試把問題鎖定於物質或生物所需層面,以消解公共政治的集體行動,並貶抑民主、自由、平等、多元等價值為「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這也是為甚麼近幾年「反政治化」的論述在公共領域大行其道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從「經濟化」手中拯救政治
漢娜.阿倫特的《人的境況》,區分了人類的三種活動,包括勞動(labor)、工作(work)和行動(action),並探討了這些活動的條件。勞動意指透過與自然界的互動,例如獵食或採集,獲取延續生命所需,食物和安全保障,是所有動物共有的本能;工作是與人造世界的互動,例如各種工藝、技術活動,涉及的條件是建立及置身於可居的塵世(worldiness) ;行動的條件則是人的多樣性,人類不可能完全離群獨處,因此必然與其他不同的人互動,行動包括討論、說服、決定、執行,當中充滿難以控制、無法制止、不可預料的性質,人在行動中「不知道自己正在做甚麼」,會產生甚麼後果,行動就是冒險。把阿倫特關於人類活動的分類,與上述的「反政治化」的文化大計對照,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從「經濟化」手中拯救「政治」的思考角度。
阿倫特所稱的「勞動」,對應的是「經濟化」指向的動物性需求;而在當代的社會脈絡下,「工作」可以理解為接近科技理性與管理主義的活動形式;至於「行動」,對應的則是公共政治的參與,這種活動既非為了追求温飽,也不是透過訂定按步就班的規劃,希望達致確定的成果,而是願意冒不確定的風險,走到人群中去對話、溝通,參與集體的生活。阿倫特心目中的公共政治「行動」,並不是由形式(如遊行佔領或示威集會) 介定,而是「意味去創新、去開始……發動某件 事」(《人的境況》,頁139)[12]。
「行動」,或參與公共政治,並沒有類似「勞動」和「工作」的顯然易見的「用處」。它的特殊之處,正在於其超越了人作為動物的日常必需領域,因而也有可能擺脫律常伴隨追逐温飽而至的暴力和專制手段[13]。阿倫特從回顧古希臘的城邦歷史中,領會到人只能在脱離追逐物質生活的羈絆下,走進「行動」的不可預知的公共領域,才能獲得自由,或回歸人不同於其他動物的特性。當公共政治的空間被壓縮,「行動」難以開展,人便會容易退回私人的領域,變為一群孤立的個體,只埋首勞動或工作,消費生活所需,不再關心人類集體的前途,為極權統治提供了生長的土壤[14]。循阿倫特的視角回看香港,「反政治化」劍指的,恐怕正是我們的公共政治空間,嘗試取消「行動」,把港人推回只求温飽這必需性的動物層次,強調「搵食大哂」的「中環價值」;或跟循科技理性/管理主義的軌道,僅提供「勞動」或「工作」的選項,也就是只剩下「經濟化」的目標。
循此思路,我們可以理解,自1997年迄今的中港「深層次」矛盾,根源於私領域中「經濟動物」的「獸性」與在公領域中「政治行動」之「人心」之間的分歧與衝突,尤其是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中國的「改革開放」 —— 也就是逐漸採納新自由主義的文化大計 —— 之後。「改革開放」其實是社會全面「經濟化」的發展工程,亦是透過「反政治化」 —— 對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徹底否定 —— 來加以推進,嘗試把整個社會的發展目標框限於物質豐盛、民眾的温飽,先讓「一部分人富裕起來」,再達至「全民小康」。在「改革開放」的大旗下,過去的公共政治語言,包括人民當家作主、革命、階級等逐漸讓位於經濟發展、貿易增長、繁榮穩定等詞彙,也就是從阿倫特意義下的不可預知的「行動」場域,轉向當代由技術官僚、管理主義宰制的「勞動」、「工作」等領域。1989年中國的民主運動,可理解為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化」的第一波社會自我保護,然而「六四」的鎮壓中斷了中國民眾(包括上百萬香港支持者)回歸公共政治或「人心」的努力,埋下了1997年後中港兩地「深層次」矛盾的種子。
儘管阿倫特批判馬克思主義對「勞動」的高度重視和推崇,助長了對「行動」的漠視,但仍未放棄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的前期「社會主義中國」(也就是所謂的「前三十年」) ,除了強調温飽以外,對平等、參與等動物必需領域以外的關注,至少在公共論述中,恐怕仍然比「新自由主義」時代(或「後三十年」) 為高。被中共官方「徹底否定」的「文革」,逐漸成為了反「政治化」的最重要「歷史記憶」,加上1989年的「六四」鎮壓及隨之而來對公共政治的全面控制,客觀上為「改革開放」的「經濟化」進程掃除了主要的障礙,令社會平等、民主參與等訴求與價值被貶抑為「破壞安定」、「打擊繁榮」的「政治化」「浩劫」,也為1997年後香港的「資本主義」「五十年不變」塗上底色,把社會生活和文化價值約化為動物温飽的必需層次的「經濟化」進程,由於只剩下對物質富裕的追求,滋生了片面追求經濟不斷増長的發展主義意識形態,以及由此而至的社會危機–貧富兩極分化、生態危機–全球暖化各式污染、道德與人性危機–以狹窄的物質/經濟價值取消(或替代) 對 真與善的追求。與「經濟化」進程共生的「反政治化」,傾向排拒壓抑難以控制和不可預料的「行動」,令依據討論、說服作出集決定的公共政治逐漸消失,使民眾分解成單獨的個體,在缺乏認真的論辯的情況下,容易孕育輕率盲信,又或鼓勵順從,為極權社會創造生長的條件。當1980年代中國啓動的經濟化/反政治化「改革開放走資大計」,在1997年與缺學無思[15]的香港殖民體制及執行者遇上,滙流合力強化(或全面啓動)港英殖民時代的極權因子,同時淡化甚至嘗試抹去英式自由主義與中式社會主義理想中蘊含的平等、民主和自由等動物必需層次以外的價值與生活訴求。
雨傘運動的再思

2014年的雨傘運動,正是一場嘗試中斷甚至扭轉「經濟化」進程、回歸公共政治的大型集體演練[16]。一種流行的看法認為,2014年末的雨傘運動是徹底失敗了,甚至有論者認為必須要承認失敗,才有可能汲取教訓,走出困局[17]。這種把焦點置放於短期現實政治得失的看法,忽略了雨傘運動過程中,透過重新激活公共政治的場域,不僅於79天內在一定程度上干擾了「經濟化」的過程,同時讓數以十萬計的港人親身見証及經歷了阿倫特意義下的公共政治參與,這些經歷在為數不少的民眾心中埋下了「經濟化」以外的社會發展的想象和願景,催生出不少傘後政治素人的組織或社群,積極參與社區或全港範圍的公共事務,部份更投入隨後的兩次選舉,並成功進入議會。從拯救公共政治的角度回看,雨傘運動不僅沒有「失敗」,而是成功地從變得例行化的議會議政及遊行示威,以至把命運交托他人的「訴求政治」 —— 也就是希望向代議士或政府提出(主要是物質必需的) 訴求後,等待在位者的體恤恩賜,轉到各種難以預知結果與具創造性及冒險性的社區參與、環保動保、獨立文化、另類媒體等「行動」,在「經濟化」的洪流中開拓了不少公共政治參與的空間。
故此,我們不必要接受「雨傘運動失敗」的結論,但可以承認當中確實犯了一些錯誤。從知識生產和論述反思的角度回看,一個重要的錯誤是未能有效清理傘運中一些流行的論點和關鍵概念,例如「本土」,以至在佔領結束之後,針對「經濟化」、嘗試重建公共政治的社會/民主運動方向,逐漸被以地域矛盾或國族視野的論述框架所置換。
當代香港的「本土」的論述,其實早於2006-07的天星皇后抗爭前後出台,但逐漸被地域及國族的視野窄化或收編[18],於雨傘時代成功與民眾的「抗中」意識接合,發展出「民族自決」這「港獨」的選項,並弔詭地在中港政權近年的高調批評下不斷壯大。產生的客觀效果,是以「中港矛盾」置換了反「經濟化」的抗爭。
然而,把「抗中」意識與國族框架扣連,無法準確閱讀出民眾,尤其是經歷雨傘運動洗禮的青年的情感政治。借用哈維爾對「後極權社會」(post-totalitarianism)的分析,我與同事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參閱Hui and Lau 2015),雨傘運動所呈現的香港當代的文化政治,是追求活得磊落真誠(living in truth) 與馬基維利式的現實政治(realpolitik) 的根本矛盾,前者重視的是抗拒與由上而下的權力合作的犬儒認命,後者則把政治理解為利益爭奪的場域,可以甚至應該為求目的而不擇手段。傘運參與者當中,確有一些十分重視現實政治的效果,甚至以此來批評他人「離地」[19];然而,為數更多的年輕政治素人,他們的出發點,是對朋友的義氣、對平等公正的執著、對語言偽術的厭惡,也就是希望能活得較自主自在、磊落真誠(許寶強2015)。
追求「命運自主」的傘運一代,之所以「抗中」,主要是基於「代表」中國的中共政權及其在香港的代理者–特首和政府高官、建制政黨以至各路「愛國愛黨」力量,在香港近年的作為,從高鐵、新界東北發展的毁人家園式的「中港融合」「經濟化」大計,到「一國兩制白皮書」、人大「831」決議等封殺公共政治參與的舉措,以及推行這些計劃的過程中的指鹿為馬、弄虛作假,或完全離棄一些基本的政治倫理和程序公義,所呈現的,正是一套建基於赤裸利益、不擇手段的現實政治。換句話說,所謂「抗中」,突顯的除了表面上的中港地緣政治矛盾外,還有更為根本的是兩種生活方式、價值觀念、文化政治–也就是語言偽術/現實政治vs磊落真誠/公共政治– 的衝突,在這意義下,「抗中」其實是拒絕將人還原為只求温飽的動物,反抗「經濟化」,追求回歸「人心」。
循此角度,我們可以理解,為甚麼反傘運的社會力量,其論述的重點往往置放於批評佔領、集會、示威、遊行會嚴重影響「經濟民生」,「阻人搵食」變得「罪大惡極」;而這種側重「經濟化」的論述,往往配合其他「反政治化」的策略,包括以由上而下框定的「諮詢」表演取代開放的民主討論,或以警察暴力鎮壓不可預期的公共政治「行動」,又或用「依法辦事」的措詞,把強調程序公義、人人平等的rule of law置換成政權借法治民的rule by law。換句話說,就是嘗試以動物的必需性取代人的公共政治性,用「獸性」替換「人心」。然而,「人心」卻不願完全回歸「獸性」,於是我們可以看到過去(包括港英殖民時代和政權轉移之後) 此起彼伏的民眾抗爭。由於近年的「經濟化」/「反政治化」進程,主要由「代表」中國的中港政權、建制政黨和「愛國愛港」力量推動,因此反映「人心」不願「回歸」的各種社會/民主運動,以「抗中」與「自決」的面貌出現,也就不難理解。
循上述的分析角度,「抗中」和「自決」除了依循國族框架、現實政治原則的「港獨」(或民族自決) 一支之外,還有另一重含意,也就是反映了抗拒「經濟化」的進程,追求公共政治「行動」,或「人心」不願回歸「獸性」的掙扎,這也許正是「民主自決」的真正意思。之所以以「抗中」的面貌出現,主要是1997年政權轉移後,中共的管治方式比英殖時代的「經濟化」更赤裸和徹底,愈來愈離棄了英殖時代和中國「前三十年」的公共論述,也就是忘掉「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理想中的非動物性必需的價值。
從此思路出發,我們大概也可以理解,面對近年香港青年一代的「抗中」情緒和「自決」訴求,「代表」中共政權的特首並不忌憚透過高調批評仍不成氣候的「港獨」力量,客觀上其實為「港獨」推波助瀾[20]。這樣做能夠置換了民間對「經濟化」過程所造成的社會、生態和道德危機的反彈,嘗試引導民間的不滿進入「國族矛盾」的框架,而在此框框內,仍然能夠保留「經濟化」的論述及文化大計,包括把中港矛盾吸納理解為經濟利益的爭奪,或物質資源的匱乏。而對「現實政治」與「民族自決」的倡議,也在客觀上配合了這種論述的轉移,其針對「離地」「左膠」的指控,嘗試否定哈維爾的「活出磊落真誠」的政治,或阿倫特意義下的強調討論、溝通、說服的公共政治行動的「現實性」,客觀地支持了「反政治化」的工程,以至強化「經濟化」的進程。用一句話歸納,就是嘗試以「人心未回歸」的國族/政權訴求,取代「回歸人心」的民眾訴求。
結語
於政權移交廿周年之際,無論是政權建制的「人心未回歸」論述,又或「民族自治」的港獨訴求,都未能捕捉一個更根本的問題,也就是「經濟化」/「反政治化」所蘊含的另一種意義下的「人心」與「回歸」。缺乏這層次的回顧反思,很難有助我們理解當代香港精神的變易,無法校正民主運動的方向。而要有效達致這長遠目標,前提必須是直面及處理最根本的問題,也就是如何讓社會的發展從追逐「獸性」的需求回歸「人心」的多樣性,或從「經濟化」手中拯救公共政治。
註解:
[1] 有關「經濟化」的討論,可參閱Brown (2015) 、Calıskan and Collon (2009; 2010) 、Masumi (2014) 。
[2] 在Wisenews輸入「政治化」這關鍵詞,搜尋香港報章,90年代末每年大概有幾百到千多項,到了最近幾年,則有二千多到三千多項。於1997年,已有本地論者批判反「政治化」的論述,見蔡建誠:〈香港:太政治化,還是不夠政治化?〉,http://www.franklenchoi.org/commentary/toopolitical.htm(瀏覽日期:2017年1月24日)。
[3] https://forum.hkej.com/node/127217(瀏覽日期:2017年1月23日)。
[4] 〈田北辰:只做實事唔玩政治?〉,http://www.takungpao.com.hk/hongkong/text/2016/0811/15667.html(瀏覽日期:2017年1月23日)。
[5] 一位最近退休的高級警務人員引述前輩說:「警察退咗休,有兩件事唔可以做,第一係唔可以做賊,第二係唔可以搞政治」(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61012/19798093,瀏覽日期:2017年1月23日)。
[6] 例如「終身學習」其實是指持續不斷地作「人力資本」的投資。「這反映在施政報告的教育政策建議中,除了全港性的英語推廣活動外,都是擴展或改革正規學校,而不見提及具體的措施以方便市民終身自學:如公共圖書館增購高質量的書籍、開放大學圖書館給公眾人士使用、減少法定工作時間以使在職人士有更多餘閑和精力學習等等」 (許寶強2003: 80-81)。
[7] 《蘋果日報》,1999年10月7日。
[8] http://hk.crntt.com/doc/1045/3/2/5/104532539.html?coluid=176&kindid=11723&docid=104532539&mdate=0106161545(瀏覽日期:2017年1月23日)。
[9] 可參閱Brown (2015) 第一章對美國的相關分析,Brown認為,「經濟化」已逐漸從內部破壞了民主 —— 人民當家作主 —— 的實質內涵。
[10] 劉祖雲2009:頁18-20;譚兵2009:頁46-49, 51-52。
[11] http://www.cuhk.edu.hk/hkiaps/qol/ch/index.html。
[12] 阿倫特補充,「政治是人們在公共領域中的行動、思考、學習和判斷,需要與公眾討論,進行相互說服,才有可能作出並執行決定。政治是公共的,不為政府、政黨壟斷,要求的是開放的對話與承諾。…阿倫特進一步指出,極權主義的興起意味着政治的消失。隨着開放的公共對話的萎縮,政權以至民間社會愈來愈無法明白多元紛雜的不同立場,很容易作出與 現實相距甚遠的判斷,做出違背良心傷害社會的事情」(Parekh 2008與Young-Bruehl 2009;引自 許寶強2014)。阿倫特同時指出,「很多行動其實都是透過言 說的方式進行的。不過,倘若我們僅以目的來肯定任何手段,那麼言說很可能會變成為政治化妝的空話」(《人的境況》,142;引自許寶強 2012: 169) 。
[13] 最極端的是成為完全失去自由的奴隸,以至現代社會超長工時、被老板呼來喝去的勞工。
[14] 儘管阿倫特強調「行動」於人類的重要性,但她並沒有完全否定「勞動」(與「工作」),只是從歐洲的歷史發展中看到了「勞動」的逐漸獨大的趨勢,從而提出回歸「行動」的必要(《人的境況》)。本文亦非想把「行動」與「勞動」作二元對立的分割,更無意眨抑「勞動」,而是想借用阿倫特這些有洞見的理論概念,分析在香港的當代社會脈絡下「勞動」不斷排拒「行動」的過程及影響。
[15] 缺學無思是筆者對海德格和阿倫特有關學習(learning) 及無思(thoughtless) 等觀念的概括翻譯,可參閱許寶強 (2015a) 。
[16] 這次公共政治的演練之所以能大規模爆發,除了人大8.31框架及9.28的催淚蛋直接激化外,過去幾年的也可被理解為反「經濟化」的社會運動,包括天星皇后抗爭、反高鐵
[17] 李達寧(2016年9月28日),〈後知後覺的傘運檢討──承認失敗是第一步〉,《端媒體》,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928-opinion-daniellee-unmbrellamovement/。李達寧所針對的其實是雨傘運動過程中出現的一些機會的錯失,以致未能更大程度地爭取民運的當下目標。而循此引伸出傘運的「失敗」,則窄化了判斷民主運動成敗的準則,也糢糊了接受「失敗」與承認「錯誤」於反思學習過程中細微但重要的分別–前者容易陷入「失敗主義」而打擊繼續前行的意志,後者則在不徹底否定運動(以至當中的主體)的前提下鼓勵從「錯誤」中學習。
[18] 有關香港「本土運動」的發展和演變的較詳細討論,可參閱了許寶強(2015b) 。
[19] 當中最有代表性的,也許是一些被介定為右翼「土本派」的核心,例如《城邦論》的陳雲,以至「熱血公民」和「普羅政治學苑」。傘運後他們合組成「熱普城」聯盟參與立法會五區直選,但只獲-席,「熱普城」的三位領袖均敗選。
[20] 有關香港政權與「本土力量」興起的共謀關係,可參閱許寶強(2016) 。
參考書目
Altshuler, Roman (2009): “Political Realism and Political Idealism: The Difference that Evil Makes”, Public Reason 1 (2) , pp.73-87.
Arendt, Hannah (1958).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中譯:《人的境况》,王寅麗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Brown, Wendy (2015): Undoing the Demons – Neoliberalism’s Stealth Revolution, NY: Zone Books, pp.17-45.
Calıskan, Koray and Michell Collon (2009): “Economization, part 1: shifting attention from the economy towards processes of economization”, Economy and Society, Vol.38, No. 3, pp.369-398.
Havel, Vaclav. [1978] 2010.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In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Routledge Revivals): Citizens Against the State in Central Eastern Europe, by Vaclav Havel et al, 1–59. New York: Routledge.
Hui, Po Keung and Lau Kin Chi (2015): “‘Living in truth’ versus realpolitik: limitations and potentials of the Umbrella Movement”,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Vol. 16, Issue 3, pp. 348 -366.
Laclau, Ernesto (2005): On Populist Reason.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Masumi, Brian (2014): The Power at the End of the Economy, Duke University Press.
Parekh, Serena (2008): Hannah Arendt and the Challenge of Modern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中譯,《阿倫特與現代性的挑戰》,張雲龍譯,江蘇人民出版社)
Young-Bruehl, Elisabeth(2009):Why Arendt Matters, Yale University Press. (中譯,揚-布魯爾,《阿倫特為什麼重要》,劉北成、劉小鷗譯,江蘇:譯林出版社,2008)
譚兵(2009) :《香港、澳門、內地社會援助比較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劉祖雲(2009) :《香港社會的弱勢群體及其社會支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許寶強(2003) :《富裕中的貧乏 — 香港文化經濟評論》,香港:進一步出版社。
許寶強(2009) :《告別犬儒:香港自由主義的危機》,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許寶強(2012) :《告別犬儒續篇》,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許寶強(2010) :《限富扶貧–富裕中的貧乏(新編) 》,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許寶強(2015a) :《缺學無思–香港教育的文化研究》,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許寶強(2015b) :〈社會運動作為方法–香港雨傘運動的啟示〉, 《台灣文學研究》,第9期,pp.37-51。
發佈日期:2017/07/09
延伸閱讀:許寶強,〈千萬不要忘記階級分析—本土主義的政治經濟根源〉
【活動訊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