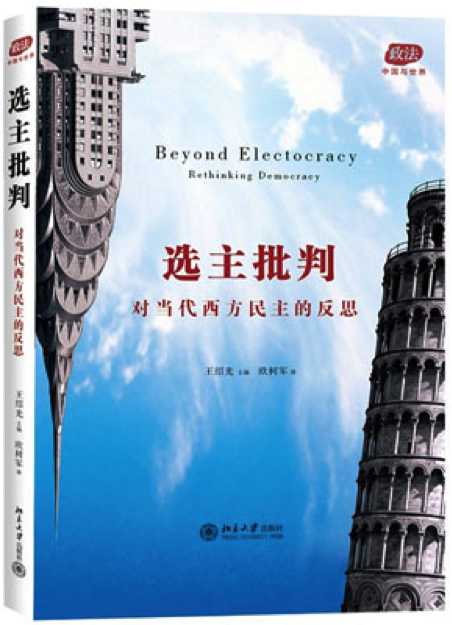反思民主,探尋民主
◎歐樹軍
【摘要:民主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一覽眾山小,以致當今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聲稱自己是民主國家。正是同時,西式民主在實踐和理論上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難和質疑。對於民主危機的性質的判斷越來越悲觀,民主理論家們開始反思代議制民主的內在缺陷,反思選舉式民主,並探尋通過各種容納普羅大眾參與的制度機制,回歸真正的民主。】
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選主體制”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危機。即使像法蘭西斯·福山,湯姆斯·弗裡德曼這樣的堅定辯護者也不時顯得憂心忡忡。更嚴肅的思考則開始跳出選主框框,重新審視一些在他人看來不是問題的問題,比如民主到底是什麼?選主究竟是不是一種實現民主的恰當方式?實現民主還有哪些更有效、更可行的方式?
—王紹光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講座教授
過去十年間,29位西方知名學者,對20世紀70年代以來民主在理論與實踐上所遭遇的雙重危機憂心忡忡,對”選主體制”做出了深刻的學理反思,彙集成12篇文章,收錄在王紹光和歐樹軍編譯的《選主批判:對當代西方民主的反思》(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一書中,集中展現了對”真民主”(real democracy)的嚴肅思考。
一、西式民主步入泥沼
當真民主的意義被認識到的時候,人們已經準備好迎接21世紀了,1989-1992年因此成為新舊兩個時代的分水嶺。在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終結論”裡,意識形態的衝突已經結束,西方自由民主製成為最好且唯一的選擇,反思民主當然還不是個問題;僅僅十年之後,在民主推手湯瑪斯·卡羅瑟斯(Thomas Carothers)的《轉型範式的終結》一文中,反思民主就已經變成了一個重要的問題,[2]而且至今仍然支配著政治理論家的思想。
十年之後,卡羅瑟斯的文章宣告了”轉型範式的終結”。背景是大約100個第三波民主化國家和地區:拉美20個、東歐和前蘇聯25個、次撒哈拉非洲30個、亞洲10個、中東5個。轉型範式假設這些國家的政治轉型設定為一條從獨裁威權走向民主之路,先是街頭抗爭運動,再是蘇聯黨報式的非理性的自我批評,最後才是以多黨制定期競爭性選舉為標誌的成熟而穩定的民主制,整個過程無需先決條件,只要政治精英有意願有能力,政治歷史、經濟狀況、制度遺產、民族性格、社會文化傳統或者其他結構因素都不重要,民主化優先於政府品質和國家建設。
但是,卡羅瑟斯尖銳地指出,”轉型範式”的這些核心假設無一成立,結果也很是不堪。只有不到20個政治體建立了較好的民主制,包括歐洲的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愛沙尼亞、斯洛維尼亞、羅馬尼亞、保加利亞,亞非拉的巴西、墨西哥、智利、烏拉圭、迦納、韓國、中國臺灣和菲律賓。其餘七八十個國家和地區都被迫接受了西方國家的苛刻條件,皆以失敗告終,走向了不負責任又沒有效率的多元政治和政黨國家化,其政府形式變成了介於民主與威權之間的混合物,又因治理失靈而變成了”失敗國家”(failing state) [3]這些國家的政治轉型如此失敗,以至於很快又爆發了”顏色革命”,形成了內外聯動的政治拉鋸戰。
短短五六年之後,所謂”阿拉伯之春”加劇了”歷史終結論”與”文明衝突論”的衝突。緊隨其後,2009年,菲律賓發生選舉屠殺慘案。2013年以來,埃及總統莫爾西、泰國總理英拉、烏克蘭總統亞努科維奇,這些民選的國家或政府領導人,相繼被街頭運動拉下馬,結果卻是軍人政府或者寡頭政府得以重建。2014年9月,印尼國會立法廢除了地方首長直選。新世紀以來,選舉民主陷入了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為嚴重的正當性危機。不僅如此,2011年美國爆發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也宣告了老牌民主國家的變質,不再是林肯說的”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而是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說的”of the 1%,by the 1%,for the 1%”。1%的富人劫持了民主,把美國從民主制變成了金融寡頭專制(financial despotism),從民主政治變成了金權政治(Plutocracy)。
除了政治體制的悲劇性倒退,最近五十年以來,西方世界的內部治理也先後遭遇多重困境。其一是工業、產業等經濟政策的失靈,自由放任主義和凱恩斯主義都面臨動力不足而難以落地的巨大困境;其二是以”福利國家”為核心的社會政策的可持續性危機;其三是在墨西哥裔等非白人族群和穆斯林等異教族群的衝擊下,歐美的多元文化政策正在終結;最後,在全球化、國際化、私有化、自由化、民主化、公民社會、現代化等各種理論和力量競相發揮主導和支配作用的時代,很多國家處在運轉失靈的邊緣,”民族國家”概念失效了。這些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進程,都在加劇而非緩解西式民主的危機。
“轉型範式的終結”宣告了”歷史終結論的終結”,同為美國”華盛頓首都環線圈”(inside the beltway)的重要外事智囊,從福山到卡羅瑟斯的思想反轉,發人深思。福山歡呼的是”選舉寡頭制”的徹底勝利,這個體系的奠基人是法蘭西斯科·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西耶斯(Emmanuel Abbe Si-eyes)、潘恩(Thomas Paine)、羅伯斯庇爾、托克維爾、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和羅伯特·達爾(Robert Dahl)等。卡羅瑟斯身為美國”輸出民主”戰略的重要推手,他的思想反轉從實踐中來,秉承的是更為久遠的思想譜系:指責代議制民主以防止”多數的暴政”為名,建立起”精英的專制”,而人類社會的未來走向是回歸真民主。這些代議制民主的反思者包括馬基雅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奧賽亞·奧伯(Josiah Ober)、約翰·麥考米克(John P. McCormick)、詹姆斯·費希金(Jams Fishkin)、漢娜·皮特金(Hanna Fenichel Pitkin)、拉尼·吉尼爾(Lani Guinier)、謝爾登·沃林(Sheldon Wolin)、莫恩斯·漢森(Mogens Herman Hansen)、理查·斯奈德(Richard Snyder)、博·羅斯坦(Bo Rothstein)、伯納德·曼寧(Bernard Manin)和納迪亞·烏賓第(Nadia Urbinati)等人。他們發現,民主並沒有因為代議制而變得更好,相反,毋寧說代議制敗壞了民主,因此,有必要從”弱民主”回歸”強民主”,從間接民主回到直接民主,從”代表的統治”回到”人民的統治”,從”虛民主”回到”實民主”,從”假民主”回歸”真民主”。
二、對“選舉式民主“的反思
如果民主有真義,那它究竟是什麼?反思民主者認為,只有返本溯源,回到政體流變論中去,才能找到真民主。柏拉圖認為,城邦公民的習慣傾向和靈魂類型決定政體類型及其變動方向。他根據統治者的數量,把政體類型分為一人之治、少數之治和多數之治,一人之治的好形式是君主制、壞形式是僭主制,少數之治的好形式是貴族制、壞形式是寡頭制,多數之治的好形式是公民憲制、壞形式是民主制。這些政體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迴圈流變的,每種政體都源於之前的制度,政治制度的變動源于領導層的不團結。這就是說,民主不是唯一的可能,另一種體制是完全可能的。在民主制下,因為平民沒有財富、沒有權力、沒有智慧,他們那不受任何約束的靈魂,追求主奴平等、男女平等、人畜平等、暢所欲言,很容易走極端,進而因為追求極端的自由,走向極端的奴役。因此,儘管民主制包含最多樣的習慣傾向、制度模式、生活模式,但它是一種不可取的壞政體,是多數平民的直接統治,古典民主與代表無關。
古往今來,代表從來都是從屬於主權的。主權在教,教皇委派代表;主權在王,國王委派代表;主權在民,人民委派代表。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代表與民主無關,恰恰相反,曼甯指出,代表的起源也即代表概念的精髓就在於,”代表的言行,對委派自己的人有約束力”。
在從古典共和制轉向現代共和制的過程中,民主變成了好政體,但直接民主制無法支撐現代共和制,代議制才被發明出來。克里斯多夫·霍布森(Christopher Hobson)由此認為,民主與代表的結合是法國大革命和美國獨立革命的重要一環,這一轉變不僅僅是潘恩的功勞,也是羅伯斯庇爾的功勞,甚至後者的形象也與民主的作用相似,他的行動就是”多數的暴政”的化身,但卻正是他在西方歷史上破天荒地第一次斷言”民主必須借助代議制”,”主權人民受自己制定的法律領導,自己去做所能做的一切事情,借助代表去做自己所不能做的一切事情”。同時,代議制也是防止、限制、制約人民變成暴民的篩檢程式,人民直接參與權力行使只是一種”粗糙的民主”,必將導致巨大災難。換言之,現代民主制之所以是可行的好政體,正是因為它是代議制的[4]。由此說來,作為現代共和制理論締造者的聯邦黨人,以及民主時代預言家的托克維爾,都是潘恩和羅伯斯庇爾的傳人,都主張用共和來約束民主,用代表來改造民主,用精英來約束人民,他們的代表觀、民主觀與人民觀是協調一致的。
在這一點上,代表概念的精髓並沒有什麼古今之變。代議制民主從一開始就被”寡頭統治鐵律”的萬有引力捕獲,成了”精英統治”的俘虜,”多元民主”、”憲政民主”、”否決政體”這些變體的實質也就不再難以理解。民主這個偶像似乎正在步入黃昏,不再能夠開枝散葉、桃李芬芳,反而在枯萎乾涸、收縮反轉。那麼,當代民主所面臨的危機究竟是什麼意義上的危機?究竟是民主沒有用好?還是民主本身有缺陷?越來越多的學者傾向于後者。
首先,民主的危機是內生的還是外生的?約翰·麥考米克同意圭恰迪尼的判斷,城邦共和制下的選舉必將走向貴族化,大眾政府必然是混合憲制,這種政制的長治久安,取決於其貴族成分能否獲得相對于君主成分和大眾成分的優勢,這就是現代代議制政府的理論雛形。麥考米克因此把圭恰迪尼視為”現代民主之父”,也就是”選舉寡頭制之父”。既然選舉意味著貴族統治,那麼共和還有希望嗎?麥考米克從馬基雅維利的思想中看到了希望。馬基雅維利在《李維史論》中構想了大眾政府的共和之道,不是排斥階級界別機制,而是把它作為政治規則,建立讓平民對抗富人的保民官、監察官制度,讓大眾成分也有可能獲得相對于貴族成分和君主成分的優勢,從而抑制達官貴人的傲慢,因為後者總是尋求對其他階層的永恆壓迫[5]。這也就是說,民主的危機是內生的,用容納而非拒絕階級因素的大眾共和來制約危險的民主,就是共和的希望所在。
其次,代表究竟是成全了民主,還是異化了民主?代議制研究權威漢娜·皮特金更傾向於後者。她主張從理論而不只是技術上反思民主,現代代議制政府成了新的寡頭制,普通人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病入膏肓的代議制民主能否獲得拯救,取決於能否克服私人權力的擴張,能否擺脫金錢干預,能否消除選舉政治對普通人的觀念、資訊和選擇的操控[6]。在皮特金看來,民主被以代表制、選舉制、金權政治為核心的政治操控術異化成了寡頭制,把普通人帶回到政治中,才能真正約束”金錢民主”,才能拯救民主。
再次,選舉這種產生代表的方式出了什麼問題?以選舉為核心的西方民主在實踐中遭遇了種種困境,諸如投票率下降,政黨身份減少,政治家不被信任,平民主義政黨風起雲湧,代議制民主的核心機制因此受到重重質疑,選舉(voting)不再被視為解決之道,而越來越被視為問題所在,有人甚至高呼”選舉已死”。克勞迪婭·齊奧利斯(Claudia Chwalisz)說:我們每個人都需要反躬自問:自己是不是選舉原旨主義者(electoral fundamentalists)。[7]艾迪安·蘇瓦德(Ètienne Chouard)質疑選舉:民主的核心在於政治平等,選舉是反民主的,選舉設計者從沒說過選舉是為了民主,歷史表明,選舉讓富人掌握了權力,權貴支持選舉是因為選舉不會威脅他們,他們還給選舉建構了選舉可以選出好人的神話,但選舉實際上是壞人的統治,選舉只適合人民彼此熟悉、能對自身行為負責的小群體,並不適用於選民不瞭解候選人、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的大群體。
越來越多的人認為,選舉變成了富人或者權貴支配政治的遊戲,而普通公民沒有政治影響力。[8]民主變得固步自封,[9]疲憊不堪,軟弱無力,西方政府對於經濟不平等並未做出有效的回應。沒有超越選舉的手段,尤其是保民官和監察官之類手段,普通公民就無法迫使政治精英負責[10]。拉尼·吉尼爾[11]認為,”通過選舉的統治”或者說”選主制”已經不能充分滿足民主的價值需求,選舉把人民的選擇權限定在選舉日,選舉讓代表自視為金錢的代理人,選區重劃等選舉操控術讓政客可以選擇選民,代表最後成了其權位的獨佔者、所有者,官職成為”代表的財產”(representational property),代表越來越像”陌生的權貴”,代議制民主的問責機制出了大問題。
在經濟與社會不平等加劇的時代,民主更是危機重重。2004年12月,美國政治學會”不平等與美國民主”課題組,發佈了由15名美國政治學頂尖學者合作、歷時18個月完成的研究報告。[12][13]他們的研究發現,美國一直大力向國外推銷民主,但其國內民主狀況卻很不令人樂觀。雖然美國社會逐漸打破了種族、民族、性別藩籬及其他長期存在的社會隔離,但卻深受收入和財富差距拉大之困,不平等在持續加劇。不僅社會貧富差距在擴大,享有特權的專業人士、經理、企業主與通常由白領、藍領雇員所組成的中間階層之間的差距也在擴大。許多中產家庭勉強度日,哪怕父母雙方都在工作;很多作為家庭頂樑柱的黑人、拉丁裔和女性處境不妙;公立學校按收入與種族進行隔離的跡象不斷增加。同時,富人和巨富卻越來越多,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更是如此,最富的1%的美國人已將窮人和中產階層統統拋在身後。白人家庭的中位收入比黑人多62%,白人家庭的中位財富是黑人的12倍;接近三分之二的黑人家庭(61%)和一半的西班牙裔家庭沒有淨資產,但只有四分之一的美國白人陷入這種窘境。在公民發言權、政府決策和公共政策這三個領域,美國都在放大極少數人的影響力,促使政府不回應多數人的價值觀和需要,這加劇了政治發言權的不平等。結果,美國的平等公民身份和回應性政府理念正在遭遇越來越大的威脅。而美國財富與收入差距的擴大速度已經超過加拿大、法國、德國、義大利以及幾乎所有其他發達工業民主國家。在實現民主理想方面,美國已裹足不前,在一些重要領域甚至走了回頭路。湯瑪斯·皮克提(Thomas Piketty)的《21世紀資本論》用更多的事實和資料證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已經重新回到了一百多年前的”鍍金時代”。
現代民主的多數決原則也有天生的社會選擇困境。喬賽亞·奧伯認為,唐斯的”理性的無知”和阿羅的”不可能定理”所導致的社會選擇困境,是民主體制無法擺脫的遺傳病灶,民主的價值因此大大削弱。而民主的古典定義不是人民壟斷官職,因為人民是集體意義上的整體,無法成為”官職擁有者”。民主制並不是指人民對現存憲法權威的獨佔,它不僅僅是人民的權力,不僅僅是人民在國家內部相對於其他潛在的權利掌控者的優勢權力或獨佔權力。為了讓人民以常規化、可持續的方式擁有政治能力,現代社會必須處理一些麻煩的集體行動和合作困境,投票從來都不是唯一的處理方式。民主制是人民在革命時刻對自身的歷史性自我肯定的結果,是人民在公共領域做事、做成事的集體能力[14]。奧伯同樣主張告別簡單化的以選舉為唯一標準的民主模式,啟動人民的集體力量,從而改造政治。
民主與憲政是一對孿生兄弟還是冤家對頭?與樂觀的民主憲政論者不同,謝爾登·沃林對”憲政民主”或者”發達工業民主制”深懷憂慮。他認為,所謂憲政民主是沒有人民作為行動者的民主,憲法既是在限定政治,也是在約束民主,”其設定的界限一定與社會中占支配地位的權力群體合拍,並使之正當化”,公司法人權利的自然人化就是最典型的表現。而民主的自由特徵也遮蔽了反民主的權力形式,也消解了”人民”的同質性。“發達工業民主制”的民主化,最終變成”勞動、財富和公民心靈,同時得到防禦與剝削、保護與壓榨、養育與榨取、獎勵與控制、奉承與威脅”[15]。沃林一陣見血地指出了”憲政民主”通過消解”人民”、保障少數人權力的反民主實質。
三、探尋真正的民主
看起來民主痼疾已發,”人累了,選舉累了,錢卻不累”,甚至”選舉已死”,”政黨已死”,鈔票卻逍遙無忌。那麼,民主還有沒有未來?新的政治科學還有沒有可能出現?很多學者對此持樂觀的探索態度,設想了不同的未來。
斯奈德希望儘早終結轉型范式,”超越選舉威權主義”,從四個方面做恰當的政體分析[16]。一是誰統治,是政黨精英、領袖個人、軍隊,還是神職人員;二是統治者如何統治,通過庇護網路、種族紐帶還是大眾政黨;三是統治者為什麼統治,出於貪婪、種族仇恨還是宗教或意識形態使命;四是”國家管控度”,是否有人在統治?統治者又在多大程度上在統治?這四個方面不僅僅是政體思維,也融入了政道或者治道思維。
博·羅斯坦的”政府品質論”同樣將目光投注到治理對民主的影響[17]。他認為,政治正當性是所有政府體系的終極目標,很少有證據表明”選舉式民主”是創造正當性的首要工具。公民通常更頻繁、集中地接觸政治體系的輸出端即政府而非輸入端,他們在輸出端所遭遇的,常常對其福祉有至關重要的影響。作為在政治體系的輸出端產生正當性的基本規範,公正(不偏不倚)與輸入端的基本規範,即政治平等,同樣重要。政治正當性的主要來源處於政治體系的輸出端,與政府的品質相關。只有在權力行使中消除腐敗、歧視以及對公平原則的違背,才能創造出政治正當性。因此,羅斯坦敏銳地指出,只是把選舉式民主送給一個國家,不可能給它創造政治正當性。
莫里斯·漢森則推進至政體分析的源頭,自由民主源于孟德斯鳩的分權理論,但充滿了例外,漏洞百出,早已過時,而現代自由代議民主制不是純粹的民主,最好稱之為”混合憲制”,它所混合的政治制度只有一部分是民主的,其他部分則是貴族制或者君主制的,各種不同成分不會以每個機構壟斷一項特定職能的方式分立,不存在什麼三權分立,各司其職[18]。漢森的”混合憲制論”超越了選舉式民主的單向思考,為改造現代政治的運作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元理論視角。
另一位代議制研究專家伯納德·曼寧也認同漢森的混合憲制論,他把現代代議制政府分成了三個階段:議會民主、政黨民主、”受眾民主”(audience democracy),所謂受眾民主,就是觀眾即時寫劇本,政治家像舞臺演員那樣直接訴諸公眾,政黨在這個過程中是多餘的。[19]當然,受眾民主更多是正在進行時,民主的未來在於民主與非民主成分的混合,恢復現代政體的混合體制本色[20]。
麥考米克同意馬基雅維利的看法,即,富人而非人民才是共和制的最大政治困境,而選舉式民主已經陷入了結構性的問責困境,更多是金錢、資源而不是選票、權利決定政策,選舉也不再能夠有力地確保官員負責,選舉具有天生的貴族效應,只是一種有利於富人的選拔機制,威脅共和政體的首要根源是富人的資源和官員的巨大自由裁量權,而不是人民大眾的無知、嫉妒、冷漠和反復無常,在富人的腐化、顛覆和篡奪企圖面前,當代民主制與古代民主制同樣脆弱,需要用”馬基雅維利式的民主”(Machiavellian Democracy)[21],即人民大眾制約富裕公民和官員的非選舉方式,包括混合抽籤與選舉的平民主義官員任命程式,為特定官職設定排斥富人的階級資格限制,以及支持全體公民參與處理政治犯罪的控訴程式,來拯救當代民主。
詹姆斯·費希金、布魯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和卡斯·桑斯坦(Cass Suntain)把希望寄託在復興”協商民主”上。費希金版的協商民主機制,核心是通過抽籤隨機抽樣,建立臨時協商群體,討論重要議題,通過投票決定結果。協商民主論把協商視為民主的實質,主張在現代條件下,通過各種協商式制度實驗,來復興民主的協商本性。
勞倫斯·萊西格(Lawrence Lessig)提出了”民主券”(democracy vouchers)和抽選產生的憲法大會(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selected by sortition)方案。萊西格方案的困境在於,三個臭皮匠真的抵得上一個諸葛亮嗎?相信群眾還是相信精英?三分之二的美國人甚至不知道權利法案是啥!這種情況下如何讓普通公民提出憲法修正案?[22]這個困境集中體現了現代代議制民主的危機與生機,代議制民主是因為不相信群眾眼睛雪亮而生,也因此走上了太過倚重精英的道路。
尤拉姆·蓋特(Yoram Gat)等人認為,未來的希望在於用”抽選民主”、抽選之治(Lottocracy)[23]或隨機民主(Randomocracy)矯正選舉民主。他們認為,普通人能夠對影響自身長遠福祉和生活品質的事務做出決策,才是人類社會最好的治理,而抽選(sortition or selection by lot)更有助於實現這種治理,抽選是民主的,選舉是貴族制的。抽選有很多好處,它可以讓我們放棄選舉、競選、競選捐款,切斷金錢與影響力的關聯;可以隔離兩極化、意識形態和忠誠困境,讓議會更準確地代表人民,讓政客不再完全操控政治,讓大眾有制度化的政治參與管道,還可以緩解根深蒂固的權勢和政治階級所帶來的腐敗。[24]它是對選舉民主的極佳替代,不僅僅適用于古希臘和當代的陪審員遴選,也適用于地方議員和國家政治。民主的希望在於抽選民主,即在基層社區,通過抽籤遴選公民組成政策陪審團[25],決定立法結果,而政黨的作用只限于立法與政策的倡議和辯護。抽選民主與選舉民主混合運用,並與集權的、等級制的政黨體系相結合,這更可能與21世紀頻繁互動、高度關聯的社會自身的水準權力關係相適應。此外,抽選論者還主張不再以左右劃分政治,而是通過區分人民與權貴,重新構想政治的未來。
斯蒂芬·沙羅姆(Stephen R. Shalom)提出了”參與式政治體”(ParPolity),具體落實為一種嵌模式的議會(nested councils)。[26]與典型的直接選舉相比,每一級議會選舉一個代表到上一級議會,從而建立一種有機聯繫,有效監控代表的表現,並在必要時彈劾之。因此,每一級議會都不能太大,不能離其支持者太遠,以免無法監控或者成本太高。與典型的間接選舉相比,這可以確保人民意志不因選舉層級變化而減弱。
拉尼·吉尼爾構想了”集體效能論”[27]。集體效能論基於”相同的命運而不只是相同的長相”,相信民主與自治相關,而不僅僅是代議。要者有三:第一,民主的結果應該體現集體智慧:普通人是重要的決策者,而不僅僅是個統計資料點;第二,參與過程增強了民主的正當性:人民更信任自己做出貢獻、付出心血的結果;第三,民主要回應的是基於公平的各式各樣的表達,而不僅僅是選票:參與不能被縮減成一個單一的選擇時刻。吉尼爾認為,這些假設都建立在更普遍的參與價值之上,參與讓公民有能力承擔風險,挑戰不公,對公共辯論有所貢獻,也是在回應讓”選主體制”感染瘟疫的各種因素,比如公民不參與、不信任政客、不尊重政策結果等等。蒙哥馬利罷乘公車運動中的群眾大會、巴西的社區劇場、帕圖阿雷格里港的參與式預算、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有關選舉體制改革的公民會議,都是這種集體效能論的一種實驗。吉尼爾把發揮”集體效能”作為更重視參與、更有活力、更注重交往的民主問責方式,它至少在地方層面是可能的,是對選舉的昇華。
沃林認為民主能否復興,取決於共同體能否復興[28]。這種共同體,讓普通個體有能力在任何時刻創造具有共同性的新文化模式,讓大家可以齊心協力建立工廠工人所有制,為低收入者建造住房,提供更好的學校、更好的醫保服務、更安全的飲用水,以及處理日常生活中人們共同關切的其他事務。這些共同行動,通過挑戰”民主的自由和平等”所帶來的各種形式的權力不平等,來實現民主的復興。
上述種種方案都相信現代代議制民主或者說選舉式民主已經陷入困境,民主要想獲得拯救,需要回到混合憲制的整體思維,用民主製成分平衡寡頭製成分、君主製成分,用地方直接民主拯救全國代議制民主。而選舉、代表、代議制,都是需要反思、對抗、制約的寡頭制機制。
四、結語
如果把過去四分之一世紀的政治理論史看做一篇文章,這篇文章的起承轉合可以說只有一個關鍵字:民主,再沒有什麼比它更提綱挈領,更萬眾矚目,更動人心魄。民主在這四分之一世紀達到了其自身的巔峰,當今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聲稱自己是民主國家,然而,登上巔峰的輝煌轉瞬即逝,也正是在這四分之一世紀,民主在實踐上陷入難以擺脫的泥沼,在理論上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質疑,對於民主危機的性質的判斷越來越悲觀。
作為反思民主的一部分,人們對真民主的探尋從未停止,但這註定是一條充滿荊棘之路。民主的正當性來自哪裡,也正受到更多質疑。究竟是經濟增長,還是某種政治價值的實現在支撐民主?這提醒我們,民主絕不僅僅是政治思想、觀念、理想的民主化,也是工業化的民主、現實的民主,尤其是有政治主體的民主。民主不僅僅是說說而已,更應該是有效的民主、廣泛的民主。
人們也許會問,對於不民主、不那麼民主或者非西式民主的國家,討論真民主是否必要,是否缺乏正當性?這就像是在問,一個瘦子看到了肥胖的危險,可不可以自主選擇不做一個胖子?答案不言自明。能否回歸真民主,能否找到新的政治、好的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能否超越遮蔽心智的”民主原旨主義”,能否將代表觀、民主觀與人民觀協調一致,能否提升反思民主、追問真民主的智識能力,進而敢於構想新的未來。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1] See http://www.stickergiant.com/, click “social-political,” “progressive,” and “anti-Bush.” 轉引自博·羅斯坦:”建構政治正當性:選舉民主還是政府品質”,載于王紹光主編、歐樹軍譯:《選主批判:對當代西方民主的反思》,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第1版,第195-218頁。
[2] Thomas Carothers, “The End of the Transition Paradigm,” Journal of Democracy 13, No. 1(January 2002).
[3] Florent Guénard, “Promoting Democracy : A Theoretical Impasse ? ” Books and Ideas, 28 November 2007, http://www.booksandideas.net/Promotin … ocracy-a-theoretical.html.
[4] 克里斯多夫·霍布森,”革命、代表與現代民主制的根基”,載于王紹光主編、歐樹軍譯:《選主批判:對當代西方民主的反思》,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第1版,第49-77頁。
[5] 約翰·麥考米克,”抑富督官:讓精英重新對大眾政府負責”,載于王紹光主編、歐樹軍譯:《選主批判:對當代西方民主的反思》,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第1版,第11-48頁。
[6] 漢娜·皮特金,”代表與民主:不穩定的聯姻”,載于王紹光主編、歐樹軍譯:《選主批判:對當代西方民主的反思》,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第1版,第78-86頁。
[7] Claudia Chwalisz, “Are We Electoral Fundamentalists?”
https://equalitybylot.wordpress.com/20 … ectoral-fundamentalists/.
[8] Martin Gilens and Benjamin I. Page, “Testing Theories of American Politics: Elites, Interest Groups, and Average Citizen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ume 12, Issue 03, September 2014, pp. 564-581.
[10] 約翰·麥考米克,”抑富督官:讓精英重新對大眾政府負責”,載于王紹光主編、歐樹軍譯:《選主批判:對當代西方民主的反思》,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第1版,第35頁。
[11] 拉尼·吉尼爾,”超越選主:反思作為陌生權貴的政治代表”,載于王紹光主編、歐樹軍譯:《選主批判:對當代西方民主的反思》,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第1版,第87-134頁。
[12] 他們是明尼蘇達大學的勞倫斯·雅各斯(Lawrence Jacobs)、馬里蘭大學的本·巴伯(Ben Barber)、普林斯頓大學的拉裡·巴特爾斯(Larry Bartels)、哈佛大學的、斯坦福大學的莫里斯·菲奧裡納(Morris Fiorina)、耶魯大學的雅各·哈克(Jacob Hacker)、聖母大學的羅德尼·郝羅(Rodney Hero)、喬治梅森大學的休·郝克羅(Hugh Heclo)、加利福尼亞大學爾灣分校的克雷爾·瓊·金(Claire Jean Kim)、雪城大學的蘇珊娜·梅特勒(Suzanne Mettler)、西北大學的本傑明·佩奇(Benjamin Page)、伊利諾斯大學香檳分校的戴安娜·平德修斯(Dianne Pinderhughes)、波斯頓學院的凱·萊曼·施洛茨曼(Kay Lehman Schlozman),以及哈佛大學的西達·史考樸(Theda Skocpol)、悉尼·維巴(Sidney Verba)和邁克爾·唐森(Michael Dawson)。
[13] 美國政治學會特別報告,”不平等加劇時代的美國民主”,載于王紹光主編、歐樹軍譯:《選主批判:對當代西方民主的反思》,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第1版,第243-275頁。
[14] 喬賽亞·奧伯,”民主的原初含義:做事能力,而非多數決”,載于王紹光主編、歐樹軍譯:《選主批判:對當代西方民主的反思》,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第1版,第1-10頁。
[15] 謝爾登·沃林,”難以抓住的民主”,載于王紹光主編、歐樹軍譯:《選主批判:對當代西方民主的反思》,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第1版,第135-151頁。
[16] 理查·斯奈德,”超越選舉威權主義:非民主體制的譜系”,載于王紹光主編、歐樹軍譯:《選主批判:對當代西方民主的反思》,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第1版,第179-194頁。
[17] 博·羅斯坦:”建構政治正當性:選舉民主還是政府品質”,載于王紹光主編、歐樹軍譯:《選主批判:對當代西方民主的反思》,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第1版,第195-218頁。
[18] 莫恩斯·赫爾曼·漢森,”混合憲制vs.現代民主的君主制與貴族制特徵”,載于王紹光主編、歐樹軍譯:《選主批判:對當代西方民主的反思》,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第1版,第152-178頁。
[19] Bernard Manin, The Principles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20] 伯納德·曼甯,”代議制民主真的民主嗎”,載于王紹光主編、歐樹軍譯:《選主批判:對當代西方民主的反思》,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第1版,第276-293頁。
[21] 約翰·麥考米克,”抑富督官:讓精英重新對大眾政府負責”,載于王紹光主編、歐樹軍譯:《選主批判:對當代西方民主的反思》,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第1版,第11-48頁。
[22] Lawrence Lessig, Republic, Lost: How Money Corrupts Congress-and a Plan to Stop It, New York: Twelve, 2011.
[23] Alexander Guerrero,”The Lottocracy,” http://aeon.co/magazine/society/forge … ts-pick-reps-by-lottery/.
[24] Brandon Joyce, http://equalitybylot.wordpress.com/20 … andon-joyce-on-sortition/ ; David Grant,http://equalitybylot.wordpress.com/20 … t-talks-about-sortition/.
[25] 政策陪審團由獨立機構而非議會隨機遴選,代表整個社區。政策陪審團不會取代議員,但會完善其工作:讓每個公民有時間和管道掌握他們所需要的所有資訊,從而在獨立論壇上做出能夠贏得社區信任的明智決策。參見http://www.noosa.qld.gov.au/-/democracy-the-noosa-way。
[26] Stephen R. Shalom, ParPolity: Political vision for a good society [J]. Z Magazine/ZNet, (November), 2005.
[27] 拉尼·吉尼爾,”超越選主:反思作為陌生權貴的政治代表”,載于王紹光主編、歐樹軍譯:《選主批判:對當代西方民主的反思》,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第1版,第87-134頁。
[28] 謝爾登·沃林,”難以抓住的民主”,載于王紹光主編、歐樹軍譯:《選主批判:對當代西方民主的反思》,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第1版,第135-151頁。
本文原發表於《開放時代》2015年第5期,轉載於《人文與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