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文由中山大學嶺南學院政治經濟學教授、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經濟學教授盧荻撰寫,原刊於2025年7月4日《明報》,經作者授權由「新國際」轉載。文章回顧近年國際左翼思想界圍繞中國與世界格局的爭論,以Losurdo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為切入點,揭示其長期以來的知識盲點:對蘇聯、中國及全球南方反帝實踐的漠視甚至敵視,沉溺於「純粹主義」理論框架,卻忽略資本主義本質上的世界性。作者並結合個人經驗,指出西方左翼在論述中國時,往往陷於國別視角與西方中心主義,甚至在政治立場上與右翼殊途同歸。盧荻強調,在美國霸權衰退、民粹與新法西斯抬頭之際,中國與全球南方的角色尤為重要。文章提醒讀者,若要理解並參與新世界的可能誕生,必須超越西方內部視角,直面殖民主義的延續與全球權力的重組。
「舊世界已經瀕死,新世界尚在難產,於此明暗交錯之際,怪物湧現。」這是上世紀意大利革命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名言。然後近百年過去了,輪廻再現,來到特朗普2.0年代,民粹主義、新法西斯主義浪潮洶湧澎湃。西方左翼知識分子焦慮不安,即使不敢奢望改變世界,至少也得理解世界。
而理解世界的關鍵之一在於理解中國,是否堪以寄望作為創造新世界的重要力量;由此進而要求自我審視,檢討他們長期以來藉以理解西方本身的知識,以及他們應對西方與世界的實踐。
來到新舊交替加速階段,爭論升級
筆者此前在本欄介紹了圍繞Giovanni Arrighi著作《亞當.斯密在北京》的爭論,那已經是十多年前的爭論了,而隨後世界果然是照着書中的預言演變:美國霸權衰落加速,中國在世界崛起加速。於是爭論兩端的分歧更嚴重,對立更尖銳,表現為對另一部新近著作的熱議:意大利學者Domenico Losurdo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誕生、死亡、重生》(意大利文版2017年,英文版2024年,中文版2022年,作者於2018年去世)。

本書的主要篇幅用於哲學批判,但是核心信息是政治批判,後者透過英文版兩位編輯和譯者的導論更加凸顯出來。
哲學批判,指的是書中第3-5部分,對近百年來歐美一系列多多少少屬於左翼陣營的思想家的批判。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回應Perry Anderson——英國《新左派評論》雜誌創辦主編和美國加州洛杉磯大學歷史系教授——近50年前的名著《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後者以不無認同的態度討論這些思想家的思想演化,着重強調,西方馬克思主義從物質批判轉向精神批判,即是從政治經濟學轉向哲學、美學、心理學、文化研究等領域,歸根究底是因為「歷史與階級意識」問題:自1920年代革命浪潮被鎮壓之後,西方的革命不再,縱使是在危機時代也就是革命的客觀條件成熟時候也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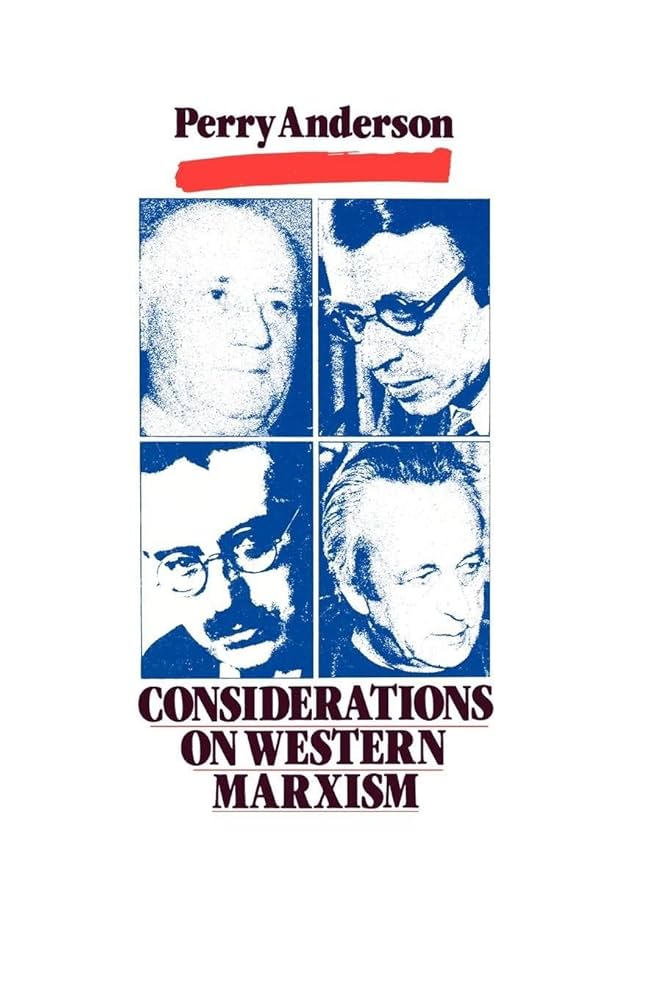
政治批判,主要是書中第1-2和結尾也即第6部分,正是要揭示Anderson及其所討論的思想家群體的共同知識盲點,即,對蘇聯、中國、全球南方的輕視、漠視、敵視。在知識上,這一方面是源自以先驗信條對照和要求現實,所謂「純粹主義拜物教」,另一方面,更根本是無視歷史存在的資本主義必然是一個世界性體系,勞動與資本的鬥爭必然是表現於世界範圍,而西方社會之外的社會主義導向的反帝反殖運動,正是勞動反抗資本的體現。Anderson以冷淡的態度,說俄國革命波瀾壯闊而中國革命更是人類歷史上規模空前絕後的社會動員,但是皆受制於客觀環境也即資本主義發展程度有限,因此世界意義有限,這正反映了上述的「無視」。
而今日回應Losurdo的反批判者,倒是從精神批判回歸到物質批判,然而同時是從無視走向敵視。其特性猶如筆者在評介圍繞Arrighi著作的爭論的上一篇文章(以及之前好些評論各路「自封左派」的文章)所述,在知識上以國別模式理解資本主義,在政治上以左翼話語包裝着對中國的滿滿的敵意,總之是宣稱中國政治經濟的惡劣程度堪比甚至遠超美國霸權,總之是西方中心主義甚至種族主義地罔顧霸權的存在。
錯位「看待中國」:一點個人體驗
行文至此,或者可以借題發揮,談談筆者與西方左翼的一度邂逅和一點感悟。
新世紀初,筆者突然心血來潮,寫了一篇文章投寄《新左派評論》,就是那篇令很多人感到新奇的發表在《讀書》雜誌的以「中國模式」為標題的文章的英文版。然後Anderson直接上門來亞非學院在辦公室詳談,很表贊賞,並將我介紹給Robert Brenner(美國加州洛杉磯大學歷史系教授),邀請我去洛杉磯做個講座。
然後那篇文章命運多舛。Brenner作為評審極力推薦,同時提出諸多修改和補充要求;我尊重這些要求,將文章從5000字左右擴展至15000字以上,回應質疑、強化論斷。然後等着等着過了兩三年始終不見刊,評審繼續推薦,是作為執行主編的Susan Watkins死活不同意。期間跟她多番面談和郵件交流。她強調,文章沒有突出階級鬥爭和危機趨向,這在政治上和知識上都不對。我引經據典解釋說現階段中國政治經濟現實的主要矛盾不是這樣,理解中國與資本主義的關係必須有世界範圍的系統觀,不能限於國別模式觀之內。
然而知識的論辯始終不敵政治的成見,最終他們放棄了,我也放棄了。在隨後的年頭,出現在《新左派評論》的中國論述,經濟上是孔誥烽那類調調,政治上是區龍宇甚至黃之鋒的專訪,完全出乎我的想象。卻原來,西方左翼與右翼,在面對西方之外的世界時是同一種認識、同一種立場、同一種行動。
在洛杉磯的大學講堂會議室、餐廳酒吧、Anderson家裡,一群來自世界各地但是用英語交流的左翼知識分子高談闊論,其樂融融也自以為睿智看透世界。後來覺得是虛幻,當時卻覺得好像是憧憬的實現。大概是2008年左右,Watkins在汪暉座談會上主持致辭,就熱情洋溢地歡迎中國同志、祝賀世界各地左翼共聚一堂,那個時候我也感動了。然而真實世界終歸是另一回事。
黎明前,「他們本來應該是中鋒」
言歸正傳,2024年年底,Anderson在北京大學演講談世界資本主義前景迷茫,替代的前景更是迷茫,其基調正是「舊世界已經瀕死,新世界尚在難產」。

這個基調主要是來自視野的限制,就是只着眼於西方內部:危機重重下,一方面是統治階級統治不下去,另一方面是被統治階級不是朝向創造新世界,而是朝向野蠻的民粹主義、法西斯主義,終歸還是百年來西方左翼苦苦掙扎的「歷史與階級意識」問題。至於會場上一眾中國學者的提問,提醒是否需要重視來自中國、來自全球南方的國際主義進步力量,得到的回應依然是漠視。
然而漠視總比敵視好。Losurdo著作的英文版編譯者在其導論和其他相關推介文章中,特別強調,西方左翼之所以被西方中心主義俘虜了,其實是有其物質基礎的,這就是「工人貴族」問題:西方對全球南方的盤剝所得,部分用於收買工人階級的上層集團,各式各樣社會民主黨、工黨、民主黨以及相關聯的群眾團體和意識形態建制就是其代表,誘導工人階級支持這種盤剝。今日西方左翼及其影響下的群眾對中國的敵視正是來源於此。
筆者在小時候見識過阿根廷文藝作品《中鋒在黎明前死去》,年代久遠,忘記是電影、連環圖、抑或是初中課文,總之不是原初形態的話劇,這些形態都出現於中國,影響了整整兩代人。作品以拉丁美洲文學的魔幻現實主義刻畫邊陲地區資本主義社會的壓迫性,作為中鋒足球員的主角在經受壓迫中覺醒,挺身反抗而最終犧牲。這里就借用作品的意象,說:現階段是新舊世界交替的黎明前,左翼本來應該是猶如中鋒,但是西方左翼卻要自取毀滅,奈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