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時間政治——評瓦克曼《時間緊迫》
◎王行坤
【編按】中秋佳節,《新國際》特別推送一篇關於「休閒」與工作感到「時間緊迫」的文章。科技日新月異,無人駕駛汽車的出現也預告了未來越來越多領域都將由機器取代。然而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下,科技的發展與帶來的效率,並不意味著人類從工作中得到解放並得到更多的空閒與自由的時間。雖然當今社會可能比上兩個世紀有著更多的空閒,但是主觀上人類似乎過得更加地「忙」,客觀上青年貧窮、彈性僱傭下的工作不穩定狀態嚴重,「小確幸」、「厭世」等情感表述以及「全民基本收入」的提出,某個程度上也是回應這樣的勞動處境。透過評論朱迪•瓦克曼(Judy Wajcman)《時間緊迫》一書,本文論述了數位科技時代下「後工作」的工作性質,以及「時間緊迫」意味著什麼。作者王行坤任教於天津工業大學外國語學院,關注「後工作」議題與有關懶漢權、拒絕工作的批判理論,曾翻譯與編譯一套有關「後工作」、「不工作」的期刊專題。本文轉載自2018/09/22《中國圖書評論》2018年第8期/讀家有方,感謝作者授權轉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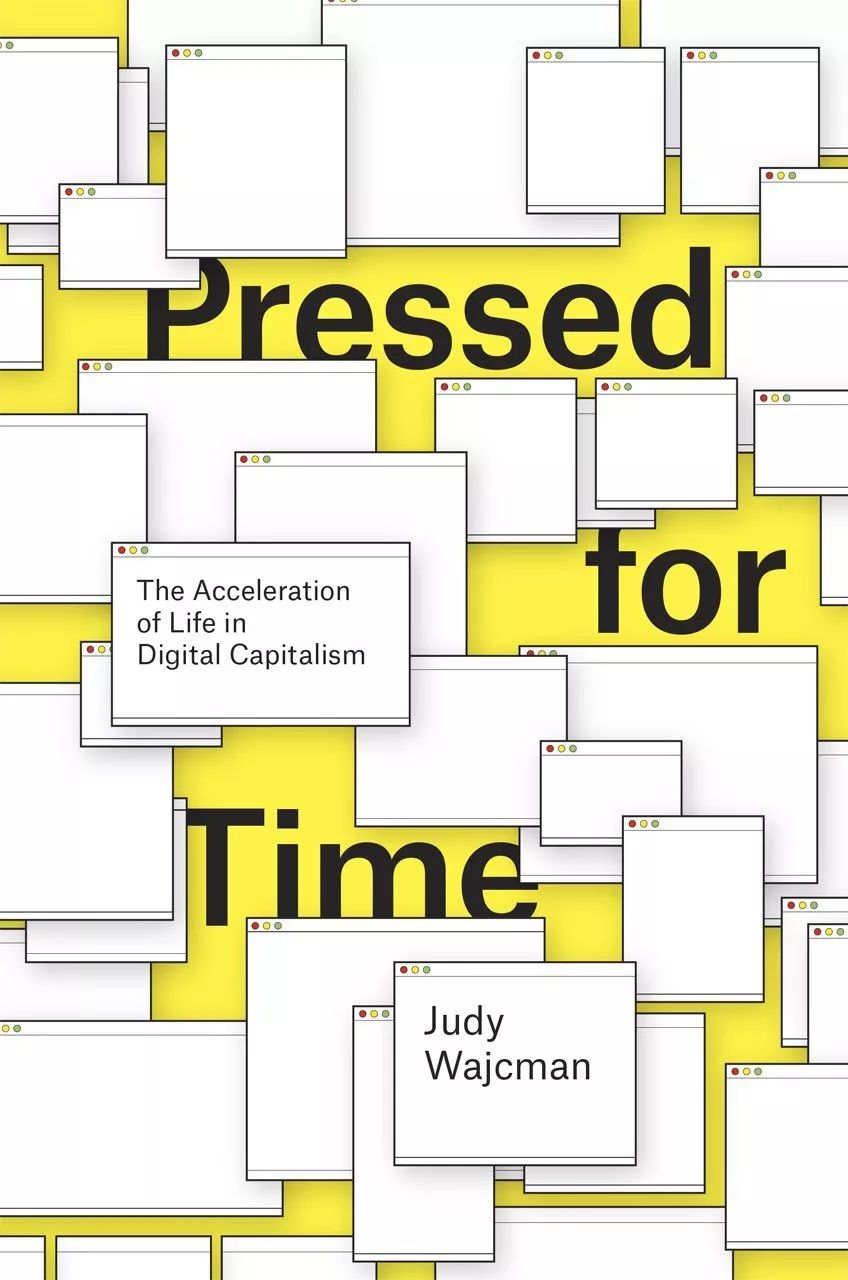
隨著「後工作」(post-work)思想的方興未艾[1],對工作時間、工作與閒暇、工作與生活等問題的反思越來越多,凱恩斯於1930年所發表的具有預言性質的《我們後代在經濟上的可能前景》也得到了很多人的關注。在這篇文章中,凱恩斯樂觀地預測,隨著技術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滿足人類需求所需要的工作時間將越來越短,人們有望從生計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那時(100年以後即2030年),人類「應該怎樣來利用他的自由?科學和復利的力量將為他贏得閒暇,而他又該如何來消磨這段光陰,生活得更明智而愜意呢?」在凱恩斯看來,那時人類可以廣泛分配所剩不多的工作,每周工作15小時就足以同時滿足人類的物質需求和工作願望——凱恩斯將這種工作願望稱為劣根性。[2]
時間已來到2018年,我們迎來的是一個物質和閒暇都極大豐富的時代嗎?就物質來說,全世界某些地區的匱乏依然觸目驚心,但大部分地區的大部分人口已經享受到了豐富的湧現;就閒暇來說,反而是大部分地區的人口都行色匆匆,深感時間緊迫。這不能不說是歷史進步的巨大悖論。
作為研究時間利用、工作變遷與技術進步的專著,朱迪•瓦克曼(Judy Wajcman)的《時間緊迫:數字資本主義下生活的加速》(Pressed for Time: the Acceleration of Life in Digital Capitali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5)[3]自然也提到了凱恩斯的預測,並且其主要目的就是解釋,為何先進的數字技術沒有能減少人類的工作時間,而是讓我們更加感到時間緊迫。但時間緊迫真的是技術進步——尤其是信息與通信技術(ICT)——造成的嗎?所有人都同等程度地感到時間上的緊迫感嗎?如何看待技術對人們的時間感所產生的影響?我們如何才能慢下來,享受高品質的閒暇,從而享受真正的自由?瓦克曼的這本書將工作社會學、科學與技術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以及女性主義熔於一爐,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切入點。

一、時間緊迫是一種怎樣的體驗?
現代都市中的居民最為常見的抱怨之一就是「忙忙忙!」。現代技術如各種自動化機械以及信息與通信技術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節省了我們的勞動,為何我們還辛勞不已,無法擺脫亞當的詛咒(the curse of Adam)?前文所引凱恩斯所說的劣根性原文即是「the old Adam」[4],指的是人類不得不勞作並忍受勞苦的命運。尤其是伴隨著信息與通信技術的發展,我們似乎進入全面加速的時代,原本線性的鐘錶時間趨向於消失。保羅•維利里奧(Paul Virilio)甚至發明瞭速度學(dromology)來解釋人類所面對的加速化世界,其他類似的概念還有瞬時的時間(instantaneous time)和無時間的時間(timeless time)等。[5]
這些概念都非常形象地描述了我們所經歷的加速社會。的確,伴隨著信息通信技術的發展,交易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完成;伴隨自動化和人工智能的發展,生產的速度也大大加快;而伴隨著交通網絡的發展,人和物的移動更是超越了日千里。因此我們的生活節奏在不斷變快,因而就感覺繁忙不堪。但是難道技術不是會節約時間的嗎?因此伴隨著技術的進步我們不應該有更多的閒暇嗎,為何會感到更加的匆忙?這就是作者所提出的「時間緊迫悖論」(time pressure paradox)。
但我們的閒暇真的變少了嗎?瓦克曼通過數據指出,自「二戰」以後,西方國家的閒暇時間並沒有減少,其實還有所增加。但為何人們還是感覺時間緊迫?當然,對時間的感受本就很主觀,人們可能在量上擁有更多的閒暇時間,但如果在享受閒暇的同時還要擔心工作內容或者家庭事務,這也會造成時間緊迫的感受。因此,作為一名女性主義學者,瓦克曼解構了太過概括性的時間緊迫話語:男性在家庭內的勞動時間要少於女性,對家務在精力和情感上的投入也弱於女性,這當然造就已婚已育女性在時間上更加緊迫的後果。
當然,我們不禁要問,現在家庭空間不也自動化了嗎?洗衣機,微波爐,烤箱等家用電器不是大大節省了我們花在家務上的時間嗎?的確,隨著社會分工的發展,很多原本屬於家務勞動的活動都被社會化和商品化,如製作衣服、養殖家禽家畜、釀酒、醃菜、甚至於做飯,以至於很多社會學家認為家庭只存在消費功能。[6]但是家用電器依然需要有人操控,這就產生了很多額外的活動。另外,像準備飯菜,照料老人與孩子的活動依然屬於勞動和時間密集型的活動,無法被機械化,也無法加速,大多時候都是落在了婦女的肩上。另外,當下文化對於衛生、對於與孩子相處的「品質時間」(quality time)的重視都讓家庭活動的內容有增無減。尤其是對單身母親來說,她們可以說是時間緊迫感最為強烈的群體。
因此當我們說時間緊迫的時候,我們要分清不同群體——如男性與女性,城市居民與農村居民,精英與大眾——所面對的不同時間體制。換言之,時間緊迫感是一種多維度的現象。[7]
時間或者說鐘錶時間與資本主義的崛起有著緊密關聯。正如芒福德(Lewis Munford)所說,現代工業時代的關鍵機器不是蒸汽機,而是時鐘。[8]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前資本主義的農業社會都是根據自然節奏以及上帝或者神的時間來安排自己的作息。關於這一點不得不提E.P.湯普森的經典研究《時間、工作紀律與工業資本主義》中,這也是瓦克曼在非常重視文本。[9]農民會根據自然節氣來安排農時,歡度比現在多得多的宗教節日,而教士則會根據教堂的鐘錶來安排每天的活動。因此有論者認為聖本尼迪克特的信徒們及其嚴格的工作秩序,也許是現代資本主義的最初奠基人。[10]
湯普森所指出,在農業社會,時間標誌法曾被描述為任務導向(task-orientation)。完成這種任務不需要計時,農民有活就乾,無活就歇,因此也就沒有「生活」與「工作」的區分問題,因為工作完全是自主的(前提是不至於土地荒蕪而顆粒無收)。最後,與需要計時的(工廠內的雇傭)勞動相比,這種勞動不慌不忙,毫無緊迫感,甚至顯得浪費時間。[11]因此前工業社會並不需要精確的計時工具,不需要那樣分秒必爭。
在韋伯看來,作為入世禁慾的新教滋長了現代工作倫理,從而也確立了現代的工作社會和工作意識形態。新教徒不再通過神跡或巫術來確認自己是否被上帝所揀選,他們的標準更為客觀,那就是在禁慾的前提下勤勞致富。因為所有禁慾的新教教徒為了確認自己的「恩寵狀態」,無法再借助任何巫術—聖禮手段、懺悔赦罪或個別的虔敬善功而獲得保障,最終只能訴諸自己的行為舉止。最終就是「著眼於彼世而在現世內進行生活樣式的理性化」。[12]所謂理性化就是通過勞動積累財富,於是勞動或者做工(如《約翰福音》9:4所說,趁著白日,做那差我來者的工)就成了絕對命令。任何對於時間的浪費,如社交、閒聊、享樂甚至超過健康所需的睡眠絕對是應該加以道德譴責的。正如韋伯所指出的,富蘭克林「時間就是金錢」的說法雖然未曾聽聞,但其背後的精神卻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13]教徒的懶惰有損於上帝的榮光,現代工人的懶惰則有損於資本家的利潤。對此湯普森寫道:「在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所有的時間必須有所利用,必須銷售掉,使用掉;勞動力白白地『消磨時間』(pass the time),這是一種錯誤。」[14]
於是我們看到,到了19世紀下半葉,這種工作倫理越來越成為一種虛假意識,因為絕大多數工人無法從工作中得到財富,更不要說拯救了。工人會通過怠工與造反等方式反抗這種工業生產方式,於是作為馴服工人機制的工作意識形態就應運而生了。這種意識形態之所以會佔據主導地位,當然有賴於各種意識形態機器的作用。[15]在高茲(Andre Gorz)看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可以稱之為工作社會(work-based society)。在工作社會中,作為絕大多數的雇傭勞動者的時間當然要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即創造財富和剩餘價值。因此所謂的時間緊迫悖論也就很好理解:一天二十四小時要在(「我的」)自由時間和(由老闆所支配的)工作時間進行分配,前者必然不斷為後者所侵佔或者殖民。
無論技術如何進步,生產力如何發達,資本總是要剝奪越來越多的勞動,而不可能主動削減勞動時間,滿足於已經極大豐富的生產。在《資本論》和《機器。自然力和科學的應用》中,馬克思對機器的論述均是從穆勒的一句話開始的:「值得懷疑的是,一切已有的機械發明,是否減輕了任何人每天的辛勞。」[16]這個懷疑當然是有道理的,因為資本主義使用機器的目的並非是為了縮短工作日,而是為了縮短必要勞動時間,從而抽取更多的相對剩餘價值。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非但沒有縮短勞動時間和減小勞動強度,反而最終把工人的勞動強度增加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因此馬克思在《大綱》中寫道:最發達的機器體系現在迫使工人比野蠻人勞動的時間還要長,或者比他自己過去用最簡單、最粗笨的工具時勞動的時間還要長。[17]瓦克曼沒有注意到資本與勞動的對立關係所造成的勞動時間的不減反增,這無疑是巨大的盲點。
《時間緊迫》指出,在過去50年中,美國和歐洲的工作時間並沒有明顯的增加。事實上,在1965—2010年,當三分之一的美國人感覺匆忙的時候,他們的自由時間其實在增多(第64—65頁)。那問題就來了,時間緊迫僅僅是我們的主觀感受,而且主要是工作女性尤其是工作的單身母親的問題?
二、都是數字技術的錯?
在瓦克曼看來,這種時間緊迫感更多由現代的「忙文化」所造成的。在20世紀上半葉以前,精英階層的重要標誌是大量的閒暇,這樣他們就可以從事政治與藝術等高貴的活動,而普通民眾只能從商或者從事生產性勞動——後者被認為是「鄙事」,屬於小人所為。但是在今天,這種價值秩序似乎顛倒了。今天的英雄是那些創業型企業家,他們在媒體中的形象是勤勞且智慧的成功者,是有著多方面追求的生活家,最典型的就是馬雲,他不僅在商界呼風喚雨,而且也想在藝術界留下自己的印記。即便是富二代,他們也要表現出勤勞聰慧,如此才能得到大眾的接受。「今天衡量社會地位的標準不是對閒暇的炫耀性消費,而是投入時間密集型工作的程度。」[18]換言之,是繁忙,而非閒暇成了「榮譽勳章」[19]。這可以說是工作意識形態的一個具體體現,那些失業或者找不到工作的人在這樣的文化中必然要受到歧視。有研究表明,失業所造成的傷害比失去親人還要嚴重。這是工作意識形態對人的內在心理所造成的壓迫。
當然,忙也分為窮忙和富忙。兩者除了收入上的差別之外,心態上也有著天壤之別。前者主要是從事低端行業的臨時工或者合同工,他們沒有穩定的工作,可能從事好幾份兼職,每天疲於奔命,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從這些工作中除了收穫微薄的工資之外,無法獲得任何成長的經驗或者生活的意義;後者雖然繁忙,但是他們能夠掌控自己的工作節奏,並且能從自己的工作中獲得成就感和意義感。而大多數人介於這兩者之間,將「忙文化」內化進自己的心理。因此當一般人抱怨「忙忙忙」的時候,他們既是抱怨,同時也不無炫耀。加班也就成了家常便飯。瓦克曼也注意到了工作的極化問題——她給出的說法是好的MacJob(以蘋果公司中的高科技高收入的工作為代表)和壞的McJob(以麥當勞中的低技能低收入的工作為代表)。[20]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時代,很多重復性和程序化的白領和藍領工作逐漸被消滅,中產階級萎縮,壞的McJob大肆泛濫。但瓦克曼並沒有沿著這條線索論述下去,來解釋當下的時間緊迫感。作為科學與技術研究出身的學者,她選擇了對技術與時間緊迫感之間的關聯進行闡釋。
一般對待技術存在樂觀論和悲觀論兩種態度,前者認為技術進步必然帶來社會進步,如更豐富的物質產品,更短的工作時間,更便捷的生活服務;後者則認為技術總是走向樂觀期待的反面,不是帶來解放,而是帶來更深的奴役。在瓦克曼看來,無論是技術樂觀論還是悲觀論,本質上都是技術決定論,即認為技術必然會帶來某種社會結果,而她則屬於技術的社會塑造論(a social shaping approach to technology):技術並非外在於社會的抽象理性的必然後果,而是一系列社會、經濟和政治力量互動的結果。換言之,技術設備與時間的關係取決於這些設備如何進入並融入我們的制度以及日常生活的模式中去。[21]技術設備並不直接決定我們的時間感,而是受到社會制度、日常生活文化等要素的中介。也就是說,可以將技術視為某種編碼,而如何對其進行解碼取決於我們所處的社會制度以及日常生活實踐。
瓦克曼正是在這種思路的指導下來破除如下流俗之見:電子郵件以及手機等信息通信技術是讓我們感到時間緊迫的罪魁禍首。作者基於自己的實證研究否定了二者之間的因果關係。[22]電子郵件並不一定會加快工作節奏,因為員工即便在工作場所之外收到工作郵件,他們也可以決定何時回復。手機也並沒有讓工作時間侵佔「我的」時間,相反,它可以讓我們有更加靈活地安排時間,與親人朋友進行更多的互動,從而建構更為緊密的社會關係——手機並沒有「偷走」我們的時間,只是改變了我們安排時間的方式。
但果真如此的話,我們似乎的確沒有感到時間緊迫的理由,似乎時間緊迫更多是工作女性尤其是單身母親的感受。瓦克曼給出了一定的解釋,那就是很多人對信息通信技術所帶來的隨時隨地的互聯的擔憂——工作時間侵佔「我的」時間,整個社會成為生產的場所即社會—工廠(social factory)——必須在如下語境中進行考慮:嚴酷的經濟氣候以及相伴隨的不穩定狀態。[23]也就是說,當經濟氣候不好並且造成工作不穩的情況下,很多人就會感到時間不受自己掌控,疲於奔命卻無濟於事,那種時間緊迫感才是最為迫切真實的。
三、新的工作形式造就了越來越強烈的時間緊迫感
但瓦克曼並沒有對經濟氣候和不穩定狀態展開論述,當然也沒有論述工作形式變化所造成的時間感的轉變。瓦克曼用「在過去50年中,美國和歐洲的工作時間並沒有明顯的增加」來反駁朱麗葉•肖爾(Juliet Schor)的《過度工作的美國人》(The Overworked American)所提出的美國人過度工作的問題,這實際上是站不住腳的,因為美國和歐洲的勞動時間差別甚大[24]。這背後的原因當然是因為歐洲的國家政策,因為歐洲比美國更為平等,更是因為相較於美國,歐洲勞工的力量要更為強大,因此歐洲勞工所爭取的「我的」時間要多於美國勞工。正如肖爾所說,「資本主義的發展會導致我所稱之為的『長工作時間』。最終之所以能奪回閒暇,是因為工會和社會改良家們展開了漫長的爭取更短工時的鬥爭。」[25]事實上因為德國工會的強大,他們正在爭取將周工作時間從35小時縮減至28小時,其訴求之一是這樣可以更好地照顧家庭。[26]而美國則顯然因為工會力量的衰落,以及消費主義的盛行,勞動者則明顯過度工作,缺少閒暇。
瓦克曼寫道:「工作性質、家庭構成、關於撫育子女的觀念以及消費模式的轉變,所有這些與技術變革的共同作用讓我們感到世界在加速」。[27]如今,隨著離婚率的提高,單親媽媽越來越多。另外,隨著國家的退出和社會福利的緊縮,再生產的任務完全落到核心家庭或單親家庭頭上,而家庭內的無償勞動則主要落在婦女頭上,這就造成女性相較於男性的時間緊迫感。另外,現在對孩子的(過度)關注的確造成了父母將大部分時間投入「品質時間」的後果,這也造成人們閒暇時間的縮水。再者消費主義的浪潮將大部分勞動者都裹挾其中,人們通過消費去製造幸福的幻象,然後再拼命工作以維持收支平衡。正如肖爾所指出的,長時間地工作,長時間地看電視,大肆購物,擁抱物質主義的價值觀,這些不會增進幸福感,反而會讓人變得抑鬱、焦慮。[28]這些要素在瓦克曼的書中都有詳細論述,但作為工作社會學家,瓦克曼對於當下工作性質的轉變卻著墨甚少。而在我看來,工作性質的轉變是造成勞動者時間緊迫的最關鍵要素。
瓦克曼的確通過引用理查德•桑內特(Richard Sennett)來指出長期穩定雇傭關係的終結及其對人格所造成的影響[29],但是並沒有詳細分析具體是什麼樣的終結。這裡最為關鍵的就是20世紀80年代伴隨新自由主義確立所產生的雇傭的不穩定化,即不穩定階級(precariat)[30]的產生。他們沒有穩定安全的工作,沒有或者只有很少的社會保障和福利,有的只是少得可憐的工資和自己難以認同的工作身份。麥克•戴維斯(Mike Davis)指出:「全球的非正規工人階級(與貧民窟居民有交叉,但兩者並不完全相同)大約有十億強,這讓其成為地球上增長最為迅速、史無前例的社會階級。」[31]這樣的群體不可能掌握自己的時間,也就是說他們不可能擁有瓦克曼所說的時間主權(temporal sovereignty)——自由不僅意味著免於貧困的自由,而且意味著掌握時間的自由,在朝不保夕的工作的驅使下,他們不能不感到時間上的緊迫。
另外,隨著智能手機的普及以及各種各樣網絡平台的出現,企業拋棄了傳統的雇傭方式,通過在全球範圍內分派任務(如亞馬遜的土耳其機器人、優步、Facebook等)。這樣企業不需要與勞動者締結任何勞動關係,它們只需要發佈任務,然後等待合適的人來競爭獲取並完成任務。這種新時代的計件工資形式一般被稱為零工經濟(gig economy)。這種工作形式看起來很美好,好像勞動者可以靈活地安排自己的時間,像個企業家那樣經營自己的事業。但是從事零工經濟的主要是中下層勞動者,他們的生活岌岌可危,每天只能戰戰兢兢地等待並且競爭企業平台所派發的任務,而不可能掌握自己的時間。而因為他們不是企業的員工,因此也不能享受醫療保險和失業保險等福利。有組織預測,到2020年美國全職就業將會變得稀缺,超過40%的勞動力將是自由職業者、合同工或臨時工。[32]
在不穩定雇傭的背景下,勞動者很難分清工作時間與「我的」時間,甚至不知道下一個工作任務的內容,因為他們總是在焦急地等待任務,這對他們的身心健康和社會關係造成了很大的負面影響。[33]而作為具有女性主義立場的科學與技術研究學者,瓦克曼在最後的部分強調了如何正確對待家務勞動以及數字技術。但瓦克曼只是提及了數字技術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但是卻沒有注意到更為關鍵的問題,那就是數字技術如何被資本主義企業所利用,形成所謂的平台資本主義,從而對勞動者進行更為精細刻薄的剝削——零工經濟就是當下新興的剝削形式。如果我們想要奪回更多的閒暇,那就必須直面這個問題,從而提出更為激進的時間政治。
瓦克曼似乎接受了每周40小時的工作時間,只想保衛這40小時之外的「我的」時間不受侵犯。但作者忘記了在美國30年代曾經出現的爭取30小時周工作時間的運動。事實上,工人運動從最開始就在爭取更短的工時,從而讓他們有更多的時間投入家庭和社區以及自我的發展中。從根本來說,爭取更短工時意味著解放,無論是對個人還是對集體來說。[34]馬克思也將「工作日的縮短」看作是「自由王國」的「根本條件」。[35]歷史學家亨尼卡特(Benjamin Kline Hunnicutt)考證了另一個被遺忘的「美國夢」:逐步削減勞動時間。[36]在美國的歷史上,這曾經是比我們一般所知道的美國夢更高的夢想。
瓦克曼的結論沒錯,數字技術的確不是造成現代人時間緊迫的元兇,真正的罪魁禍首是技術所處的社會與經濟制度以及文化和意識形態等。但如果想要爭取更多的閒暇時間,獲得時間主權,那就必須削減工作時間。在數字資本主義和平台資本主義的歷史背景下,工作時間不斷滲入「我的」時間,獲得時間主權似乎變得前所未有的艱難,不穩定勞工時刻都要擔心或者操心工作。
但這根本還取決於勞資雙方的力量對比。作者在書中提到,德國大眾公司規定在工作時間之外不能向員工發送電子郵件。[37]另外,法國在2017年元旦通過法律,工人享有「斷網權」(right to disconnect)[38],即在工作時間之外可以無視工作電話或者郵件。但是對於那些從事零工經濟的勞動者來說,斷網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必須隨時處於在線狀態以接收任務。他們無法控制工作的日程和內容。這種工作形式本身就存在問題,因此有學者和活動家主張用平台合作主義(platform cooperativism)來代替平台資本主義。平台合作主義的根本在於這個平台必須由依賴或參與平台經濟活動的成員集體所有,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在公平分配的基礎上讓所有利益相關者都能掌握自己的工作日程和時間。
當然,在人工智能時代,很多職業都要消失,其中也包括傳統意義上的白領崗位,如記者,律師,醫生等,剩下的工作將寥寥無幾,而且的確呈現出極化的趨勢:高收入且能帶來成就感和意義感的工作越來越少,低收入且只能帶來挫敗感的工作越來越多,如我們前面所說的各種零工。一個健康理性的社會應該盡可能消滅後一種工作形式,同時對前一種工作進行更為普遍的分配,這樣每個人就可以像凱恩斯所預期的那樣,每天只需工作很短時間,但又不必擔心失業的前景。這是諸多「後工作」理論所提倡的解決方案,荷蘭等國家也在實踐這種分享工作(work-sharing)的形式:每人都有工作,每人都少工作。[39]
因此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時間政治不僅僅意味著奪回時間主權,削減工作時間,同時也意味著更民主的工作場所、更合理的工作日程、更人道的工作形式以及更公正的勞動分配。這是當下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微觀政治,也是當下的大政治。
註解:
[1] 關於後工作,見孫大剩,〈工人的消失與後工作的未來〉,《藝術世界》2017年9月刊;王行坤,董牧孜,〈勞動的解放是爭取懶惰的權利〉(上)、〈只戀愛不工作,廢青的未來不是夢?〉(下),《01哲學》。英文世界關於後工作的較為全面深入的介紹,見Andy Beckett, Post work: the radical idea of a world without jobs,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news/2018/jan/19/post-work-the-radical-idea-of-a-world-without-jobs?CMP=Share_iOSApp_Other。較為通俗的英語專著,見Rutger Bregman, Utopia for Realists: The Case for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Open Borders, and a 15-hour Workweek, trans. Elizabeth Manton, The Correspondent, 2016。
[2] 凱恩斯。《預言與勸說》,趙波,包曉聞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358-359。
[3] 台灣將這本書翻譯為《縮時社會:奪回科技控制的快轉人生》,王寶翔譯,台灣:新樂園,2017年。
[4] John Maynard Keynes, Essays in Persuasion, New York and London: W.W.Norton & Company, 1963, pp.368—369.
[5] Pressed for Time: the Acceleration of Life in Digital Capitali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 p.14.
[6] 見烏蘇拉•胡斯。《高科技無產階級的形成》,任海龍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1-9。
[7] 同註5,頁5。
[8] 芒福德。《技術與文明》,陳允明等譯。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9:15。
[9] 同註5,頁37。
[10] 同註8,頁14。
[11] E.P. Thompson, 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ast and Present, No.38, 1967, p.60.
[12] 見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康樂、簡惠美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146。
[13] 同註12,頁151。
[14] 同註11,頁90-91.
[15] 關於工作的意識形態在美國取得霸權地位的過程,見Daniel T.Rodgers, The Work Ethic in Industrial America 1850—1920,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16]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27;馬克思。《機器、自然力和科學的應用》。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1。
[1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04。
[18] 同註5,頁71。
[19] 同樣的論斷見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愛德華•斯基德爾斯基。《金錢與美好生活》。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13。
[20] 同註5,頁92。
[21] 這與馬克思對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的批判異曲同工,相關研究見夏永紅、王行坤。〈機器中的勞動與資本〉。《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2(4)。
[22] 同註5,頁143。
[23] 同註5,頁159。
[24] 關於歐美各國工作時間的差別,見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愛德華•斯基德爾斯基。《金錢與美好生活》。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11—12。另見,Rutger Bregman, Utopia for Realists: The Case for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Open Borders, and a 15-hour Workweek, trans. Elizabeth Manton, The Correspondent, 2016, p.31。
[25] Juliet Schor, The Overworked America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3, p.7.
[26]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germany-election-work/german-wage-talks-to-include-new-focus-reduced-working-hours-idUSKCN1BP0KF。中文報道見http://www.baisuu.net/guojixinwen/20180111/51088.html。
[27] 同註5,頁164。
[28] Kate Holbrook et al eds., Global Values 101: A Short Course, Boston: Beacon Press, 2006, p.85.
[29] 同註5,頁108。
[30] 關於這個群體的分析,見Guy Standing, Precariat, London: Bloomsbury, 2011。
[31] Mike Davis, Planet of Slums, London: Verso, 2006, p.178.
[32] Wayne Lewchuk, Precarious Jobs: Where are They, and How Do They Affect Well-Being?, The Economic and Labour Relations Review. 28 (3): 402-419, 2017.
[33] 關於這種狀況的深入報道和分析,見Natasha Singer, In the Sharing Economy, Workers Find Both Freedom and Uncertainty, https://www.nytimes.com/2014/08/17/technology/in-the-sharing-economy-workers-find-both-freedom-and-uncertainty.html。關於零工經濟讓人工作至死的報道和分析,見Jia Tolentino, The Gig Economy Celebrates Working Yourself to Death, https://www.newyorker.com/culture/jia-tolentino/the-gig-economy-celebrates-working-yourself-to-death。
[34] Miya Tokumitsu, The Fight for Free Time,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7/10/shorter-workweek-vacation-free-time-labor.
[35] 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929。
[36] Benjamin Kline Hunnicutt, Free Time: The Forgotten American Dream,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13.
[37] 同註5,頁137。
[38] 相關報道見https://www.theguardian.com/money/2016/dec/31/french-workers-win-legal-right-to-avoid-checking-work-email-out-of-hours。
[39] 關於分享工作所帶來的各種積極後果,見Stephanie Luce, Time is Political,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5/07/luce-eight-hour-day-obama-overtime。對此安德烈•高茲有更為系統的論述,見Andre Goze, Paths to Paradise: On the Liberation from Work, trans. Malcolm Imrie, London: Pluto Press, 1985。
發佈日期:2018/09/24

